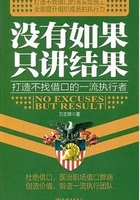秦凤舞吃得眼睛不禁微微地眯了起来,露出心满意足的表情。
这倒是令坐在一旁的宫染夜颇有些意外,若是薛氏早囔着要吐,她倒吃得津津有味起。
见宫染夜碗筷未曾动过,夹了块臭豆腐,眯起眼眸,将臭豆腐凑近他嘴边,“啊……”
他略略挑眉,眉宇间夹杂着深深疑惑,却含羞带怯张嘴将臭豆腐含在嘴里。
边上老板娘拿着茶壶,膝跪在软垫上,沏了两杯茶放在桌子上,羡慕的目光看着这两口子甜蜜,笑道:“姑娘可真体贴,懂得疼自家相公。”
嬉囔的街道上,薛氏躲在小巷内偷窥着这一幕,气得咬牙切齿,暗自怒火,这个小贱人三番四次勾引她家相公,这笔账早晚会跟她算清。
眼底一闪而逝阴毒,等着瞧吧!一气之下将手上刚买来的首饰丢在地上,往小巷走去。
正月初三,屋外麻雀叽叽喳喳,鸡鸣啼叫,梅花随风飘落在窗台上。
秦凤舞昨儿染上了风寒,今日一整天未曾下过地,只觉得浑身欲冷玉热,干呕不止,头晕脑胀,浑身几乎出不上力来,高烧不退。
这令喜鹊甚是担忧,二奶奶今个也不知吹了哪阵西北风,听说秦凤舞感染上风寒,就差人派请了位大夫,领着大夫进了屋,不巧宫染夜正拿着药喂她,心中暗暗嫉妒起。
还是强忍着不悦,屋内俩丫鬟给薛氏行礼,薛氏的眼睛却紧紧盯着宫染夜:“这里没你们什么事,退下吧!”
喜鹊、桃子互望各自一眼,又瞥了眼二奶奶身后大夫,心存疑惑,二奶奶何时变得这么友善?平时不是待她们姑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吗?又怎会好心找大夫替她们家姑娘看病?想来此事必有蹊跷,便撤退在一旁。
宫染夜将碗放在边上椅子上,看了眼薛氏,又不解的打量着站在薛氏身后大夫,挑眉凝问道:“你来做什么?”声音依旧那样冷淡。
薛氏听得暗自生起闷气,面露友善,讪讪然地笑道:“相公这话可真是的,自当是来看望妹妹病情。听府里丫鬟说起四妹病情,便想起跟随家父多年的吴大夫,他经验老道,想来四妹这病来得突然,就让吴大夫诊断诊断。”
闻听这话,宫染夜脸色愈加凝重,平时怎不见薛氏如此好心肠?若有所思,眉头微蹙,又瞧见薛氏一脸诚意,“难得你有这份心。”便也不反对,站在一旁若有吴大夫诊断。
不知道为什么,薛氏的笑容让喜鹊想起之前处处针对她家姑娘心存戒备的神色来。
秦凤舞呼吸难受,脸蛋愈加灼热,红润的嘴唇不时吐出轻烟,眉心紧皱,只觉得身心疲乏,时冷时热,好似处在水深火热般煎熬。
吴大夫撩开帐帘,坐在凳子上,卷开她那长长袖子,将食指按在她经脉上,挑眉侧着脸看了眼薛氏,若有所思的点着头,起身将被子给她盖上,这才道:“二公子,可否借一步说话?”
宫染夜却有些狐惑,只得随吴大夫出了屋。
薛氏眼波流转至躺在炕上满脸倦容的秦凤舞,嘴角勾勒出一抹不易察觉笑意。
喜鹊无意间见二奶奶脸上那若有若现的笑容,目光一掠,心存疑惑,只好朝屋外望去。
院外格外寂静,吴大夫摇着头,一声叹息道:“夫人不过是感染上风寒,只需按时服药即可,但是……”很是紧张,嘴角翕了半天,硬是没有说出一句话来。
宫染夜眉心紧皱,声音调高质问道:“但是什么?吴大夫为何吞吞吐吐?但说无妨。”
“想必二公子还不知道夫人有先天性不孕不育之症,再加上不足之症,怕是难得子嗣。”吴大夫心一提,只得将话说白了,额头隐约冒着汗。
闻听这话,宫染夜表情越发凝重,隔着窗户深深望了眼秦凤舞,对这个吴大夫诊断却丝毫未怀疑过,因为吴大夫行医数十年,曾也是宫廷御医,所以心中没有一丝疑惑。
见他沉默不语,吴大夫又道:“以夫人现在病情,不易同房,不难只会伤身。”
一时间,屋里的气氛有些沉闷。
一阵刺骨寒冷的风吹入屋内,宫染夜就微微蹙了蹙眉,淡启薄唇:“我自有分寸。”
薛氏像是变了个人似的,向昏昏欲睡的秦凤舞嘘寒问暖后,出了屋子,眼角瞥了眼吴大夫,稍稍点头,作势愁眉不展,满口担忧道:“吴大夫,不知四妹得了什么重病,为何非得让二爷出来说不可?”
吴大夫敛起视线,心中暗明,神色凝重地望着薛氏,深深叹了口气道:“不满二奶奶,四夫人病只需按时服药便可。”
薛氏今日作风令人有些意外,宫染夜看在眼里,疑在心中,转身迈步进了屋,稍喜鹊好生照料好秦凤舞,便忙自个的事儿。
待宫染夜离去后,她心里冷冷一哼,似笑非笑地道:“吴大夫,这药你可得细细的抓好,少了一两良药,四妹这病情怕好不了。”薛氏锦里藏针的话锋,在旁人听来并没什么,也只有吴大夫心知肚明。
“难得二奶奶有这份仁慈的心,小人自当尽力医好四夫人的病。”吴大夫眼波流转,若有所思的说着。
薛氏送吴大夫到后门,左顾右盼的望着四周,这才从长袖中取出装了金子的荷包遮遮掩掩递给吴大夫,出了后门小巷内,低声道:“这些钱你先拿着,待会你在上薛府拿你应得的钱。”
吴大夫拿起荷包在鼻子里深深的嗅着,露出那深深笑意:“多谢二奶奶赏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