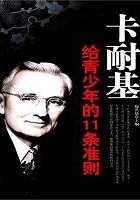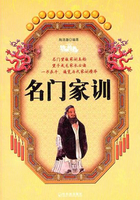董玉低着头,薄唇紧抿着默不作声,只觉得无脸面对年迈的父母。
秦凤舞挪起步伐走至他面前,将那份罪证书递给他,询问道:“可认清这份罪证书是你所画的押?”
董玉闻言,掀起消沉的目光愣愣的看向秦凤舞,怎么会是她?接过状纸,他便慎重的点头道:“是。”
站在一旁的吴家老爷气得直捶胸,指着董玉破口大骂道:“你这个畜生,我女儿跟你无冤无仇,你为什么要杀害她,为什么啊!”
“吴老爷,令千金并非是我所杀,我是被冤枉的。”董玉连忙解释,状纸上明明写着他是无辜的,为什么吴家老爷这么激动?
“你这个杀人犯,自己都承认杀死我女儿,还想狡辩人不是你杀的?”吴老爷闷哼一声,一口咬定他是杀人犯,面对着县官老爷道:“知府大人,你要为小女做主啊!”
董玉头脑一片空白,他何时承认吴家三小姐是他杀的?
秦凤舞嘴边笑纹深了几分,不难看出他现在是一头雾水,果不出她所料,“你把这份认罪证念一遍,而且要大声的念。”
董玉点了点头,拿起状纸道:“本人董玉否认歼杀吴家三小姐,否认有罪。”
站在大堂外的众人纷纷惊讶不已,这哪里是认罪状,分明是申述无罪状,大伙开始议论纷纷。
“肃静!”县官老爷拍响惊堂木,堂下一片寂静,正色厉声道:“荒唐!本官早已过目,这份明明就是认罪状,怎在你口中倒成了申述状?”
大伙听得不由赞叹,外界传闻秦家六小姐痴痴颠颠,如今却分析得头头是道,浑然不像是个弱智儿,倒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气质。
董家老爷子闻言,经她提及,念头忽闪,直道:“秦小姐所言甚是,老父患有色盲,犬子也遗传老父的色盲,因此对于我们来说所见的事物只能分辨出黑白颜色。”
秦凤舞冷然暗忖,到底是谁想出这法子陷害董玉?
站在堂外的百姓开始交头接耳,堂内也颇有些骚动。
肃静坐在一旁的宇文侯开始有些不安,深深望了眼秦凤舞,没想到这丫头倒是有两下子,倘若董玉无罪释放,他岂不是白忙一场?这口气无论如何都咽不下去,冷言道:“那又如何?董玉杀人那是事实,就冲这点赐他一死也不为过。”
董夫人眼底闪过一丝慌张,抱住儿子哭诉道:“冤枉啊!我儿生性善良,连一只蚂蚁都不忍心踩死,又怎会做出这等伤天害理的事来,定是有人想陷害我儿,妄县官老爷为我儿做主啊!”
县官老爷一声喝止,硬生生举起惊堂木啪响桌面,“放肆!公堂之上岂容你这刁妇妖言惑众?谁是谁非本官自有判断,当日吴家三小姐是三更在家遇害,有人亲眼目睹董玉在五更回府,浑身沾有血迹。一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明,二在董府搜到刺杀吴家三小姐的凶器,三有董家余管家作证,铁证如山,容不得你狡辩。”
董玉抬起眼皮,瞳孔深深一紧,双手紧捏着被扣住的铁链,李管家……
“不知可否请人证李管家上堂当面对质?”秦凤舞眼波流转向县官老爷,目光一闪而逝的慧芒,邪不胜正,她相信总会找出一丝破绽。
县官老爷余光偷偷瞅了眼宇文侯,见他紧抿着薄唇默许,举起惊堂木沉吟道:“带证人李管家上堂。”
很快李管家身穿淡黄色锦袍,大拇指上带着玉扳指,像是一夜间暴富,低着头撩起膝盖上长袍怯怯走了进来,跪在地上恭敬卑微道:“草民李权叩见知府大人。”
县官老爷目光炯炯有神的看向李管家,询问道:“讲述一下那夜的来龙去脉。”
“是。”李管家同样把目光怯怯的瞥了眼宇文侯,又看了眼秦凤舞,不由抬起右手长袖擦了擦汗水,这才道:“那晚夫人说肚子不舒服,小人便连夜去请大夫,回府途中瞧见少爷一身醉醺醺的躺在大门石阶上,身上还沾有斑斑血迹。那时小人并是很在意,以为是少爷喝多了酒撞伤了,便扶少爷回屋休息。第二天一早就听说吴家三小姐被歼杀,小人不忍少爷一错再错,就主动来报案。”
“你浑说!那晚我去大伯家是喝了点酒,回来途中被人击晕,而后醒来人已在家中。那份认罪证也是你交给我,说是只要我画了押就有十成把握还我清白,没想到权叔你竟然如此卑鄙,你到底是何居心?”董玉长袖中的拳头咯吱作响,毫不掩饰他此刻的愤怒。
李权连忙拍着膝盖喊冤道:“冤枉啊大人,少爷自小就是小人看着长大,不忍他一错再错,无奈就想出这法子让少爷认了罪,以免日后受苦,我这是做了什么孽,好心倒成了牛肝肺。”
县官老爷面色一冷,喝道:“肃静!”
秦凤舞淡然转身坐在一旁的椅子上,冲随从暗暗递了个眼色,一个打更的老伯被领了进来,只听县官老爷惊堂木一啪响,吓得老伯双腿一软跪在地上。
“堂下何人?”县官老爷眉宇瞬间紧皱起,这秦家六小姐葫芦里买了什么药?
“小人何三儿,是打更者,小人能证明董少爷所言句句属实。”打更老伯说着,不由回想起那夜的事,询说道:“那时是四更天,小人去了趟茅房解手后出来,碰巧看到董少爷被人从后脑勺击晕,被人拖进小巷深处。当小人追上去,人已不知所踪。”
李权脸色当即铁青了下来,把头低得很沉,深怕被他给认出来。
秦凤舞薄唇紧抿起,手指轻轻滑过隆起的小腹,眼波淡淡流转向老伯,询问道:“你可看清那夜击晕董少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