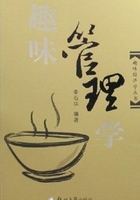下午上课,不到一刻钟。
我的大腿突然被一棵针刺了一下,但没叫出声来。
鲜于洞洞怒目瞪着我,却又什么也不说。
这时,我才发现他的脸上肿了一块肉。
想笑,又假装不明白地惊慌失措,也听不见老师讲课。
还没来得及多想,鲜于洞洞的针又刺了我一下。
这回痛得我难受,好像已经有血流出来。
刚想大声叫老师,又被重重地刺了一下。
同时,鲜于洞洞推过来一张纸。
上书:恶哈,丑哈,造谣不是哈,敢喊人哈,看你还想考大学不哈。
这哈文化是鲜于洞洞的独创,他的口头禅是:不!文字禅是:哈!
妈的,在预告他对我的处理方式。
想那仗义执言的任杨杨,今天就不执言了,搞什么背后锤人肉的事出来。
见鲜于洞洞翻脸,我的心跳得不是滋味。
他可是最调皮的学生,没有之一。
说得出干得到,何时不顺,立马翻脸的那种。
就这样,我再也没有勇气叫老师,忍住气,考学才是第一。
至于是谁打了鲜于洞洞,八九不离十是任杨杨。
因为她是这种女人,如果长成成年女人,通常你在街看见撑着腰骂城管的,必定是她这类女人。
平常她反对打架,但每次有打架的场所。
一定有她的风采,身材高大,外班人都叫她东方之猪。
我们班嘛,还是规规矩矩地叫她——江山美人,不好说,主要内容在江山二字。
她是惟一有胆量直接收拾李洞的人,收拾了还装二。
打就打了,干脆不去想,想这类事多余。
谁知,第二天一上课,我又挨了鲜于洞洞几针。
见他脸上多了几个紫青印,这事儿就不得不要去弄个清楚。
任杨杨出手好像只喜欢一次,这出现了二次,就不应该是她所为。
第一个就是夏侯村里,只有他才压时常老子曰孙子夫子曰。
不是打架用砖呼,就是呼不死再呼。
他到是与鲜于洞洞交手过两次,不过,大家懂的。
修眼镜的,通常是夏侯村里。
可是,柳里听了我的话,也感到奇怪,说居然有人敢欺负鲜于洞洞!
居然一出,说明不是他。
还说鲜于洞洞有没有错,值得怀疑。
我又找了几个男生打听,都说不知道。
为了不让事情闹大,晚上我主动走到鲜于洞床边。
小声问是谁在打他,表明自己的确不知道事情的因果。
然而,鲜于洞洞躺着一言不发。
样子是受了莫大的委屈,那张大嘴不停地打开、关闭。
同寝室的同学,都装模作样地看书。
耳朵却一直关注着我和鲜于洞洞,让我下不了台。
我说,我不愿干些有伤同学信任的事,还说吃亏的终究是自己。
到最后,竟请求鲜于洞洞不要再用针刺我。
他听了这话,像压倦了几千年的弹簧,在地震摇开了石板之后。
“呼”地一下直起身来,吼我说谁刺了你?嗯!谁?要不要我打他一顿?
我无奈之极,慢慢转身走回自己的床边。
又回头扫了鲜于洞洞一眼,是有敌意的象征。
怕你了还不行么,我高佳——索。
我没有说出来,内心还是怕得慌。
一时间,就像自己掉入了深井,无力支撑身体。
鲜于洞洞并未睡下,一直盯着我,可我不想盯,倒下去昏睡。
是网状般的昏睡,千百万根丝线,在大脑里来回打结。
直到结子装满了整个脑筋,才步入梦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