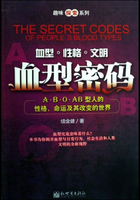远处的天空一整面的压过来,楼下静悄悄,一个人也没有,那么大的一片天,象是全部压在了方非的肩膀上似的。
人不会在瞬间发生改变的,若不见到叶永义,方非还是原来的方非,没有那么多刺,也不是那么强硬。
陈正东再也不肯走太近,但也没有离开,他无须使用语言,或者他使用的是一种负载情感的行动。
他定期过来看妈妈,送来价格不菲的药物,或者帮忙打吊瓶,毕竟曾经学过一点医学,可以照料母亲的种种细节,在妈妈形容枯槁的时刻,与方非合力推动最艰难的生之齿轮,兄妹一样。换作从前,方非一定会深深的感觉到被爱。
昨天傍晚陈正东来过,帮妈妈挂了点滴,走到客厅,有意无意的对方非说:“刘飞燕来电话说,因为缺课太多,没有拿到毕业证。”
“哦。”方非看着窗外,天色已经由黄昏转至全黑,过度的恩怨分明,使她显得冷漠。
“你不觉得惊讶或者可惜?”陈正东问,“我还以为,她不会输的太多,补上时间,从头来过,没想到损失惨重,白白浪费了青春。”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讲话,方非缩在沙发上,嘴唇闭合,不知不觉精神恍惚起来。陈正东说:“哎,在想什么?”
她看着他,不远不近坐着的陈正东,令人产生幸福的想象,方非低下头,愈发恍如隔世,什么也想不清楚。
面对一个重症病人,保持平稳和泰然的情绪很不容易,方非尽量做到最好,每次进妈妈的卧室,都会在门口稍稍站站,然后,提口气敲门进去。
妈妈的病情继续恶化,一个月里,妈妈分秒计数似的瘦下去,整个人变了形。很少很少说话,张开嘴,很容易呕吐,胃都空了,吐无可吐。
她依然在用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自己,她不甘心就这样闭了眼睛,看到小菲这样落魄而离开,她一定无法瞑目。
躺在床上,会想很多很多,有时候,痛恨自己无力给予孩子一个幸福的保证。或许该让方非尝试原谅,起码活的轻松。
方非进了家门,妈妈正趴在床上,伤口发痛,刚刚吃过止痛药,仍痛的辗转,扯起了床单。她头发落的干干净净,但依然是个美丽的妈妈,方非想要走进去,里面的姨妈从屋里冲出来,趴在墙上,双肩不停的抽动。
她哭的那么迫切,仿佛身体里有着刀割一样的痛苦。
家里的气氛真的很沉,连呼吸都透不过气,方非心中恻然,转头安慰姨妈,轻轻拍打姨妈的背,小小声说:“姨妈,不要哭,有我在。”
姨妈沙哑着声音说道:“我没想到,你妈妈这么能忍,疼起来,汗把床单都湿透了,也不肯哼一声。
到了晚上十点,妈妈平静下来。方非跪在床头,把妈妈的手贴在脸旁。每一天晚饭后,方非都会在妈妈床前说说话,临睡前跟妈妈说晚安,都象是一次生离死别,从没有习惯、麻木过。
妈妈今日看起来精神不错,对着方非笑盈盈的,忽然开口说话,叫:“小菲。”
方非抬起脸,听妈妈轻轻说:“小菲,我想见见叶永义。”
“为什么?”方非问。
“想见见他,有话对他说。”
方非不情愿,把脸伏在妈妈的被子上,妈妈轻轻抚着她的头发,坚持道,“妈妈的日子不多了……如果叶永义来了,把一切说清楚,向你道歉,你是否可以原谅他?”
“不原谅。妈妈,他不值得原谅,也不能原谅。”
妈妈是个病患,却比谁都清明,比谁都冷静,她解释道:“是,他罪不可赦,罪有应得,但是……小菲,人的一生很短暂,临到最后才想明白,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或者朋友,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原谅的。他虽有错,却也不是杀人放火……他自有难处,他从小没有家,如果让你孤零零一个人长大,敢想象吗?”
妈妈一口气说了那么多,握着方非的手,眼睛幽幽的看她,方非坐直了身子,抿了抿嘴,深深的吸了几口气,不敢再有违抗。她懂得妈妈的心理,劝女儿罢手,因为恨他太不值得,弄不好把自己后半生的幸福都搭进去,知女莫如母,没有谁比妈妈更了解方非。
方非走到阳台,外面黑黑沉沉,脸上浮起一个奇怪的微笑,只好给叶永义拨打了电话,刚刚剑拔弩张,现在不知道该用何种口气,方非等待那边接起来,才问道:“如果我妈妈想要见你,你会不会来?”
叶永义正在气头上,又喝了酒,怒吼道:“如果她快死了,我可以考虑。”便挂了电话。
方非身子一震,就此沉默下来。
方非真的很想保持气度或者风度,但叶永义的回答实在未经考虑,如同子弹打入她的胸膛。为了妈妈,方非本来已经有所动摇,如果妈妈执意让方非放手,叶永义态度诚恳,她会仔细考虑。
方非深深呼吸,仿佛身上转移了母亲的癌细胞,心一阵阵的揪痛,痛的满头大汗,方非知道这是错觉,她的痛并非肉体的痛苦。方非站在黑色的冰凉的阳台上,眼神是透彻的,苍凉的,死亡一般无边无际。
叶永义回过神来,立刻回拨了方非的电话:“如果我去见了你妈妈,你可否放过我?让我跟陶然顺利结婚并出国?”
方非的声音并不激动,只是深深的疲惫与无可奈何,她拒绝道:“对不起,机会稍纵即逝,刚才你没有抓住,现在回头,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