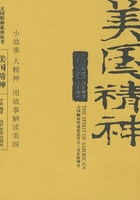你缓步走上高冈。高冈上更加空旷,放眼望去,牧人晚归的牛羊哞哞咩咩地叫唤着,一条无声的河蜿蜒曲折,流向远方的群山。你童年牧羊的景象恍然如在眼前。你还似乎看到老去的祖父佝偻着身子喂马的样子。恍惚之间,你像浪子归来。你仿佛看见,小妹妹推开了木栅门。多少年了,你在异乡的城市里无家可归,像一个被抛弃的人游来荡去。多少年了,再也没有听到阿妈在旷野里呼唤你的名字。夜晚的凉风吹动额前的头发,你才发觉眼泪已经冰凉。星光照亮了大草原。你踅身回到路边,摇醒了扎西尼玛。
“茨仁!茨仁!”你们向这一家朝圣者祝福并告别。
扎西尼玛猛踩油门,汽车冲上了公路。你回过头去,看见朝圣者一家在夜色中伫立,凝重,一如铜像。畋猎之鹰,拾取了我内心的火焰。那朝圣者,前额叩击长途。而那瞎眼歌王,破碎的喉咙弹拨命运的谣唱。三个月,或半年,或一年,饥餐粗粮,渴饮河流,冷燃篝火,当夜晚来临,朝圣者就在公路边,裹覆着破旧的羊皮袍子,席地而眠。大月驰入的青藏高原,精神空虚的观光客们在汽车和旅馆中声色犬马,谈论着一路见闻,讥笑着贫穷而肮脏的朝圣者,但谁能体会一个抱风而眠的朝圣者内心的纯粹与幸福?正如西藏奇僧更敦群培①所说:他们或许度过黑暗的一生,也不会知道,解除一个哀伤的心灵惟有依靠神圣的宗教。
长途班车在公路上疾驶。走亲戚的牧民骑着马。马蹄橐橐,蹄铁闪亮。她头靠着车窗,心中泛动着思念和回忆的感伤。目力所及,是晨曦中泛着幽蓝之光的川西大草原。一匹白马徐徐穿过潺潺流淌的小河,一个早起的牧人摇晃着背影正向山顶上的寺院走去,一个女人从泉边起身,木桶里溅出的水恰好打湿了她的裙裾……
她一再醒来又睡去,半梦半醒之间,往事如烟,一切似真似幻,却又在睁开眼睛望着车窗外那一掠而过的树木、村落、草原、溪流、朝圣者、牧人的毡帐和一两个埋头赶路的骑手时,陷入不知身在何处的虚无中。梦里不知身是客。在路上,哦,在路上,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她看见漫长的公路线一直向远方延伸,穿过草原、河流、森林和高山,像永无止境的慈航,或者流放。自从进入大草原,她的心情逐渐变得灿烂起来。一直积压在心头的阴霾不知不觉消散得无影无踪。
那年秋天,你在西部流浪,经历着命运中惨淡的时光——举目无亲,身无分文。那时候,玛曲县城的第一场雪下得遮天盖地。从兰州捎
①更敦群培(1903—1951)是现代西藏史上的佛门奇僧、学术大师、启蒙思想家和藏传佛教世俗化的先驱,一生坎坷而极富传奇彩色,曾在印度游历十二年,返藏后,遭噶厦政府诬陷,身陷囹圄达三年之久。
你到玛曲的大胖子司机把卡车往路中央一扔,独自跑进汽车旅馆找他的姘头去了。你冻得瑟瑟发抖,蜷缩在驾驶室里,透过挡风玻璃望着茫茫大雪。半夜里,你饥寒交迫。“要是我一直躲在这里,明天准会变成一坨冻肉。”你心想。你爬出驾驶室。风雪呼啸,几乎要把你的那张脸刮走。所有的人家和旅店都关门闭户。从汽车旅店的二楼窗户里传来女人尖利的叫床声。“哎,老板娘,你在卧室里杀猪哩嘛,干啥哩!”郁闷的房客在一楼叫骂着,“吵死人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看来,该死的大胖子司机已经彻底将你忘记。你跌跌撞撞地寻觅着栖身之所。拐过一家商铺,你看见一个狗熊般的黑影摇摇晃晃地走了过来。大老远,你就闻见他一身的酒气。
醉鬼难惹,你还是赶紧躲开。“嗨,别跑兄弟!”他大喊一声,冲到你身边,一把揽住你的肩头。“兄弟,是不是你拐走了我的拉姆措?觉仁波①,哦嚯,胆儿不小啊,敢抢我边巴茨仁的女人。嗳,你不要以为我醉了!觉仁波……兄弟,我就是醉了你也不能抢我的女人嘛!喏呗?”“大哥,你弄错了吧,我根本就不知道拉姆措是谁。”你说。“觉仁波,你不要以为我醉了唦。”他揽着你的肩头边走边说,“啊,你们这些汉人骗不了我,喏呗?我就是喝上三瓶青稞酒,你们汉人都别想骗我,何况我今天才喝了两瓶,喏呗?”“喏……喏……喏……”你慌不迭地应承着。巷子愈走愈窄。他的身体愈来愈沉。最后,你几乎是扛着他在走。你想,在巷子尽头,他会杀了你。
①觉仁波,意即:对着释迦牟尼佛发誓。
在巷子尽头……他用马靴踢响了一个木门。过了一会儿,门洞里的灯亮了,一个大眼睛的藏族女人打开了门。“这是两兄弟旅店,进来吧。”他对你说,“这个女人嘛,就是拉姆措,我的尕妹妹……”藏族女人用一种司空见惯的表情瞟了一眼边巴茨仁,扭身向院子里走去。跟着她,你扶着边巴茨仁走过宽阔的院子。一只藏狗冲你汪汪狂吠。藏族女人打开一个房间。“扶他进去吧。”她说。哎哟哟……红嘴绿毛的(个就)尕(呀)鹦哥(呀),(牡丹月里来呀),要吃的(个就)红颗子(金晶花儿开)米哩。
哎哟哟……尕妹是(个就)牡丹者(呀)谁不爱(呀),(牡丹月里来呀),阿哥(你就)要采一个(金晶花儿开)你来。哎哟哟……阿哥的(个就)心里(呀)头窝着(呀)火哩,今晚(你就)要在尕妹的(金晶花儿开)奶卡卡上睡哩。边巴茨仁哼哼唧唧地唱着一首花儿。“兄弟,这是205房间,喏呗?”他突然问道。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藏族女人冲你使了个眼色。于是,你说:“大哥,是的,这是205房间。”扑通一声,边巴茨仁一头栽到房间地毯上,立刻发出了呼噜声和连连呓语。女人从床上扯下一床棉被,丢在边巴茨仁的身上,连盖都懒得盖。“你睡床上。”藏族女人看了你一眼说,“你好像没喝酒。”你点了点头。她没再说什么,拉上门,去了隔壁的房间。第二天,你才知道,那藏族女人名叫卓玛,是边巴茨仁的妻子。
整个冬天,你一直住在边巴茨仁的家里。卓玛打的酥油茶让你唇齿生香。在每个酩酊大醉的晚上,你都要扶着边巴茨仁回到他一路嘀咕的
“两兄弟”旅店。那其实是他的家。真正的“两兄弟”旅店坐落在靠近温泉的公路边,那是他和情人拉姆措幽会的地方。边巴茨仁只有在清醒的时候才去“两兄弟”旅店。他从不带你,因为他担心你会把拉姆措拐跑。不过,实话实说,如果不是担心他腰间的刀子有朝一日会架上你的脖子,你真想拐走拉姆措。边巴茨仁把你当兄弟看待。那些美好的日子一想起来就让人心碎。你跟着他天天喝酒,在酒场上见识了玛曲县城里的各等角色。
恶棍兼弹唱歌手扎巴多吉是边巴茨仁少年时代的拜把子兄弟。他对你很好。每次喝酒,他都会找个姑娘陪你,可你对那些姑娘要么就认作干姐姐要么就认作干妹妹,从来不会把她们带到床上。扎巴多吉为此很生气,总说你不够义气,但你知道,他因此更加敬重你。那时候,他做生意欠了一屁股债。从兰州来的黑帮老大来催债,把扎巴多吉堵在“两兄弟”旅店里。胖得像头大象一样的老板娘跑来给你和边巴茨仁通风报信。你和边巴茨仁赶去解围。
“这是我的地盘子,”扎巴多吉对黑帮老大说,“你强龙压不住地头蛇。”“我日!”黑帮老大用枪管指着他的鼻子说,“你个尕狗娃子趴在粪
堆堆上,还想充大狗哩,我看你就是个四脚蛇。”“这位大哥,宽限两天唦!”边巴茨仁说。“我日!钱嘛,多大的个事唦!这么价着来,你们兄弟三个唦,把
这块煤炭子放在大腿面面上,能捱上一分钟,我那十万块钱咱就一笔勾销。”
045你们兄弟三个果然把三块烧红的煤炭放在了大腿上。扎巴多吉弹起了曼陀铃,唱起一首忧伤的歌。草原上的格桑梅朵,你静静地开放静静地摇晃。草原上流浪的人儿,你爬上山冈然后独自歌唱。那在春天到来的姑娘,她给你带来一罐马奶子很香。那在秋天开走的班车,它把你心爱的人儿带去远方。没有人告诉你,你的姑娘她是否幸福。没有人告诉你,你的姑娘她是否靠在别人的肩膀。阿妈说,女人是牛栏那边的河流,她走了就不再回头。阿妈说,男人是一匹善跑的骏马,他流浪是为了寻找。趁着天黑,阿妈还没醒来,你就走了。你走的时候,草原上的格桑梅朵正在开放。你爬上山冈,帐篷前的阿妈她向山冈张望。趁着天黑,看不清阿妈的眼泪,你就走了。结果,你们竟然挨了三分钟。满屋子飘荡着肉的焦煳味。“我日!”那黑帮老大说,“三条真正的好汉子。来来来,喝酒。”那夜,你们喝了一夜的酒,唱了一夜的歌。可扎巴多吉还欠着更多人的债。八月的赛马节上,他跳上主席台,夺过主持人的麦克风,对满场的骑手和观众说:“觉仁波,尕海子里埋着金矿哩,你们信不信?”你和边巴茨仁觉得那家伙疯了。“不信——”满场的骑手和观众齐声喊道。
“不信是不是?”他从主席台上跳下来,一边走向水波荡漾的尕海子,一边说,“白哈尔神①作证,我要双手捧着金子,从尕海子里出来,让你们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相信你们愚蠢的眼睛。”
当着众人的面,他一头扎进了尕海子。人们在岸上静静地等待,直到太阳落了山,也没见他从海子里钻出来。你和边巴茨仁在尕海岸边把一迭迭隆达②撒向湖面。拉姆措和卓玛在一棵树下哭红了眼睛。可是后来,你到拉萨流浪的时候,听人说他在拉萨做着珠宝生意,发了大财。有一天,你在八廓街上转悠,看见一个头戴毡帽的大胡子男人,长得极像扎巴多吉。你和他擦肩而过,但你没敢确认。过了两天,你和卓玛在八廓街上最有名的银器店里买首饰。一个男人走进店里,向店员要了个一拃宽的银手环,直接戴在卓玛的手腕上。那银手环上镶着一颗鸡蛋大的绿松石。
“你是谁一个?”卓玛问道。“扎巴多吉。”他用一口地道的西北话说,“你当我是谁一个唦?”哇,他果然是跳进尕海子再也没出来的扎巴多吉。“可你不是在尕海子里么?”你惊讶不已地问道,“怎么就到拉萨了呢?”“尕海子通着拉萨河哩嘛,我一口气就游过来了。”他撇撇嘴说,“哎呀,多大的个事唦!”“早知道这么价我们也从尕海子里游过来了,”卓玛揶揄似的说,“就不用坐班车了。我们走了半个多月。唉,我晕车都快晕死了么,胃都
①根据格鲁派的观点,白哈尔神是世间护法神中的主神。②隆达,也有人称之为“祭马”、“禄马”、“经幡”、“祈愿幡”等,不过,人们更习惯称它为风马,因为“隆”在藏语中是风的意思,“达”是马的意思。
差点儿吐出来了。”你把扎巴多吉拉到酒馆里,庆祝他的复活。他弹起扎聂琴,唱起了歌。
尕海的恋人。那年我们在玛曲。被水吞没的你变成了鱼。变成鱼骨化石。天黑了,我在树下坐等,心脏自口中逸出。尕海的恋人。那年我们在玛曲。嘴唇搂着嘴唇。被水吞没的我变成了鱼。变成鱼骨化石。天亮了,你在树下坐等,眼睛里飘着云彩。
那一次,你喝多了,醉了整整三天三夜。等你醒来的时候,看见枕头边放着你送给卓玛的银镯子。你找遍了整个拉萨城也没有发现扎巴多吉和卓玛的影子。你明白,卓玛戴着那个一拃宽的银手环跟着扎巴多吉跑了。
玛尼干戈到了。懒洋洋的司机把班车停在了路边。几只乌鸦聒噪着,在房顶、汽车和垃圾堆里觅食,几个游客挎着相机晃来晃去。乌鸦镇定自若地观望着游客。它们是玛尼干戈永远的土著,仿佛拥有着接纳
或驱逐过客的权力,而且那权力至高无上。三位乞讨的藏族老阿妈伸出油腻、肮脏的手,念诵着经文,向游客乞讨。她们的脸上祥和、宁静,似乎她们不是在行乞,而是在接受人们的捐赠。游客脸上露出嫌恶的表情,这使他们看上去既丑陋又猥琐。她给了每位阿妈一块钱,然后握了握她们的手。她们为她祝福。施舍的习惯是跟他学的。无论什么时候,他身上都带着零钱。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遇见乞丐,他都会施舍。施舍是一种修行。施舍时,你千万别把乞丐当成乞丐,要把他们当成神的使者。他们在试验你的慷慨、怜悯和慈悲。修行就是要求你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他总是这样对她说。
玛尼干戈的阳光温暖、明净、灿烂。在这川西大草原,阳光照耀着广袤土地上贫穷而自足的居民和那些行色匆匆的流浪汉。她走在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眸子清澈的吐蕃特小姑娘歪着脑袋,靠着电线杆眺望雪山。她的脸蛋很脏,脏得那么美丽,铅华荡尽般摄人心魄。
一位面色黝黑但却泛着光泽的老阿妈上了车。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四处张望着,寻找空余的座位。“阿妈,坐这儿来吧。”她说。老阿妈微微一笑,从过道里挤了过来,撩起藏袍的裙裾,坐在了她的身旁。“哦呀,卡照①!”她说。她用右手转动着金光闪闪的转经轮,左手数着念珠,嘴皮子像嗑瓜子一样不停地念着经文。“阿妈,您要去德格吗?”她问道。
①卡照,康巴藏语,意为感谢。
“喏。德格,那里是我的家。”老阿妈说,“我的小女儿在玛尼干戈,刚刚生了孩子,我来看她。你要去哪里?”
“我去德格找一个叫丹珠的老阿爸。”
“丹珠嘛,哎呀,多得很。”老阿妈说,“你要找的是酒鬼丹珠呢嘛还是赌博汉丹珠呢嘛还是吃汽车的丹珠?吃汽车的丹珠嘛,他是我的邻居。”
“我要找的是开卡车的司机扎西尼玛的阿爸,他的名字叫丹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