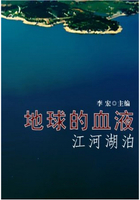她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河滩上,一群秃鹫争抢着腐尸。扎西尼玛把车开上一座小桥。色曲河在这里流进了金沙江。四川和西藏,中间隔着宽阔的一条江。“一下雨,这条路就很难走。”扎西尼玛指着前面堆满石块的土路说。“对不起,我没有听阿爸丹珠的话,”她看着扎西尼玛,很不好意思地说,“因为我……”“我理解你的心情。”扎西尼玛猛打方向盘。车轮贴着江边的路基,拐过一个急转弯。她无需俯身或者探出头去,就能看见汹涌的江水。江水浑浊。江面上漂着枯木和动物的尸体。雨像崩塌了似的,下得更大了。扎西尼玛那边紧挨着的悬崖不断有被雨水冲下的泥沙。“我开车送过他的一个大胡子朋友,也是这么大的雨。”扎西尼玛说。
五月,诗人来看他的时候,曾在这条路上走过。在一首纪念他的诗中,关于这条路,诗人也曾写到过。一万座山。冷。并且——(当我们在雨的上方)显现出倾泻的脉络/石头跳跃,沙子在阻止汽车通过/人们在半路上,远远地望/他睡在野地的泥浆中/水,会把他/冲洗成形。大约过了一小时。路变得愈来愈狭窄。扎西尼玛把车停在一块江边的岩石前。他从兜里掏出一叠隆达,撒向江面。唵,嘛,呢,叭,嘧,吽。被水吞没的你变成了鱼。变成鱼骨化石。她想起他曾经唱过的歌,眼睛里满是止不住的眼泪。“就是在这里,乡政府的吉普车滚落而下,掉入了金沙江。”扎西尼玛对她说。当时,他乘坐的正是那辆乡政府的吉普车。她想起了诗人为他写过的悼诗。
在雨水崩塌的地方/你摸索着滞留在狭小山路/翻/打猎人的山冈/你忘记了来时的目的:五月(杜鹃花才开)还十月的心愿。
扎西尼玛继续开车前行。“一个女人从北京打电话,要我给亚嘎老师捎个口信,说她要来看
他。”扎西尼玛说。“他就到县城来接她?”她问道。“是的。亚嘎老师等了三天,她却毫无音信。那天下午,亚嘎老师就搭乡政府的吉普车,沿金沙江边的这条路回去了。以前,他从不走这条
路。每次进城,他都是骑马或者徒步,从牧场上走。”“那个女人再也没来?”“来了。她来晚了。”“她叫什么名字?”“她没说。”“那她是做什么的?”“她说她登过珠穆朗玛峰。”“她在亚嘎老师出事前就死了。”“啊!怎么会呢?她说,一听到亚嘎老师失踪的消息,她就从北京赶
来。走得太急,没来得及换衣服,所以她只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我把大衣给她,她披在身上却一直在发抖。那一天雨停了,阳光照得人浑身暖洋洋的,但她却一直在发抖,而且脸色苍白,嘴唇如果不是涂了口红的话肯定会显出紫色。能看出来,她精心打扮了一番,眉毛修过,又弯又细,头发好像做过离子烫所以显得又黑又直。我跟今天一样,开着车。她不爱说话,我想那是太伤心的缘故。她在亚嘎老师失踪的地方站了很久,我的一包烟抽得只剩下两支了。她也不哭,就那样默默地站着。可你怎么说她在亚嘎老师出事前就死了呢?难道我遇见的是个鬼魂?”“我看过她写给亚嘎老师的一封信。”信。现在,我就坐在三联书店外面的石阶上。天黑了。昏暗的路灯下,人来车往。恍惚之间,有种虚妄的空气在大街上迷漫。透过这虚妄的空气,失去方向的人影在我眼前飘来飘去。在北京,你也有过这种感觉对吗?你那儿已经下雪了吗?你是不是骑着马,冒着大雪到了德格县城?前两天我打电话,他们说你在戈麦高地。给你打电话有些突兀,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你的那位摄影师朋友让我看到你的摄影和诗歌作品以后,我就想找到你。
你那些关于西藏的摄影作品我非常喜欢。我从来没有见过别人用那样的眼光看待西藏。你知道,我们平常在旅游杂志上看到的西藏摄影,全是雪山、草原、河流……这滤光镜下艳丽的色彩,只是一种空洞无物的表达,是充满艳丽色彩背后的心灵干枯。而你不同,你生活其间,用心灵在感悟那片土地。你的摄影作品粗粝、朴素,充满西藏高原的野性之美。我了解那片土地。八年前,我从美国回到北京,一心想去西藏。有一天,我开着一辆二手吉普车,从北京出发,沿着青藏公路,直抵拉萨。一到拉萨,我就爱上了那个地方。那时候的拉萨,人都特别纯朴,藏人过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离的生活,一种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现代大都市中那种紧张的生活节奏,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在拉萨全都不存在。那时候的拉萨,像是神刻意给这个世界保留的一方净土。那里的人们沉浸在宗教之中,过着纯粹精神和信仰的生活。我决定不回去了,既不回北京,也不回巴黎,更不回美国。我的母亲住在北京,而我的父亲住在巴黎。当年,为了能让我父亲去法国留学,母亲提出了离婚。母亲天真地等待着父亲学成归来以后跟她重新结婚。她等了三十年,结果却发了疯。最后,我那已经是医学博士的父亲从巴黎赶来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
好了,不说这些了。我们还是说说拉萨吧。在拉萨,我开了一间小小的酒吧。今年九月,我离开了拉萨,回北京了,因为拉萨昔日的宁静已不复存在……对,你说得对,商业气息太重了。当然,回北京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要和相恋七年的男友结婚了,他是个电视台记者。七年前,他来拉萨拍纪录片,我和他一见钟情。每年夏天,他就到拉萨来看我,而到了冬天,我就去北京看他。这一次,我再也不回拉萨了。我要装修房子。我要筹备婚礼。我要养育孩子。一个三十二岁的女人,再不生孩子就来不及了。这么多年来,我似乎错过了许多东西,马不停蹄地错过。错过一季,就是错过所有的季节。但这一次,我不能再错过了。但是,他突然对我说,他是一个有妇之夫,他们结婚都十年了。你应该理解我那种快要崩溃的状态。我曾经两次为他去堕胎!我突然发现自己无法适应这个城市。这繁忙、冷漠而虚妄的城市……曾经,我和你一样,也是从城市逃亡出来的流浪者,热爱自由,热爱大自然,像这个世界上最后的理想主义者和青铜骑士,冲毁了世俗社会加诸自身的道德樊篱,成为一个反叛者。而现在……
那时候,雪一直在下,草原上的格桑梅朵开得正艳,点地梅从金沙江岸一直铺到戈麦高地。一匹白马驮着她,从山谷那边的灌木林里缓缓走来。一场盛大的婚礼正等着她。你把她从马背上抱下来,一直抱进小木屋。过了一会儿,你俩穿着艳丽的藏袍,走出小木屋。戈麦高地上的牧民全都身着节日的盛装,从遥远牧场上骑马赶来。人们载歌载舞,觥筹交错。婚礼结束以后,你牵着她的手向草原深处走去。一条小溪在山谷里潺潺流过。那涓涓细流,澄澈见底,一条条鲜红艳丽的鱼儿驰翔在水中。鱼,依源而行,道出潮汐。人,沿途而猎,获致爱情。你定睛细看,发现每条鱼都长得奇形怪状,有方形的,有菱形的,有不规则形状的。你兴冲冲捞起一条又一条,可那滑腻腻的鱼身子,怎么抓都抓不牢。终于,一条鱼被你逮住了。你捧着那条鱼兴高采烈地唱起来,想要献给她。可她却不见了。空旷的大草原,雪一直在下。你呼唤着她的名字,山谷中传来一阵阵回声。你哭泣着,自言自语:“你为什么要抛弃我?”那时候,你手里的鱼动了一下。你低头一看,却见她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一条玫瑰形状的鱼,躺在你的掌纹里。她的眼里噙满泪水,不知道是出于忧伤还是出于幸福。
那些日子,你总是做这同一个梦。你把那些日子叫做逮玫瑰鱼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