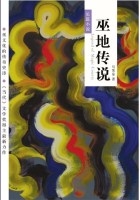雪晴低下头才发现,果然把盖头捏反了,手上捏着边尾,要绞的那边却在另一头,脸上微微一红,重新把盖头正过来。
陆太太摊开盖头,见上面绣的百合,却不是双‘喜’,“子容在外面找花姑娘了?”
雪晴眼一瞪,“他敢?”
陆太太看了看女儿,淡淡的问,“那是有哪家小媳妇看上他,缠着不放了?”
雪晴皱了皱眉,“我天天跟着呢,谁敢缠他?”
陆太太拿了根针,引了红线,绞着红盖头另一边的边,“你不跟着呢?”
雪晴想也不想,一撇小嘴,“那他也不会理会那些贴上门来的女人。”
陆太太抬起脸,直看着雪晴,“那你还在愁啥?”
有些话,雪晴埋在心里也没敢跟人说,一直这么憋着,也难免闷闷不乐,虽然娘是这年代的人,也免不了有些这时的世俗思想,但总的来说还算是开明。
想了想,从贴身的怀里取出一个做得极为精致的小荷包,边是用七彩线绞的麻花针,中间绣了只毛绒绒的老虎头,娇憨可爱,最难为她的是,这么小小的一个虎头,不同的角度看倒象是会眨眼一般。
她绣这荷包上的虎头的时候,陆太太到是见过,好一阵子的夸,没想到女儿有这手艺,虽然不知她哪来学来的,但确确实实看到她绣出来了,而且绣了四幅,绣好后,做成荷包反而没见过了,问过雪晴几次,雪晴只说丢了,陆太太还心痛了好些日子。
雪晴又另外绣了幅丝帕送给陆太太,绣的是一对鸳鸯,也能眨眼睛,说一只是娘,一只是爹,才逗得陆太太眉开眼笑,嗔骂女儿不正经,对那帕子却是极爱的,小心收着,也不舍得用。
陆太太见她这时候取了这老虎头做的荷包出来,正反正各一个小老虎头,又是贴身藏着的,那另两幅小老虎头在哪儿,心里也有数了。
雪晴松开小荷包上的金丝绳,从里面倒出一粒小指甲大小的小金珠,上面雕着一个精致的篆花图案,递给陆太太,“娘,你可认得这东西?”
陆太太拈着这珠子细细的看了,这图案好象在哪儿见过,低头想了好一会儿,猛吃了一惊,看向雪晴,“你这是哪儿的?”
雪晴从陆太太手里拈起那金珠子,慢慢的捻着,“娘,你先别问从哪儿来的,先跟我说这标记是什么?”
陆太太慢慢的回想着很久以前的一件事,把那些事挑挑捡捡,道:“那时我还小,我们镇子上出了一个能人进京当了官,家眷却没带去,他家的小儿子,不时向我们那些小孩显摆,说他爹如何如何的在朝中得势。大些的男孩就不肯信,硬说他吹牛,那孩子小,受不得激,有一日果然偷了一个铸币出来给我们看,说是他爹爹的,那个图案,与这个虽然不同,但却有相似之处,所以我琢磨着可能是朝中大臣或者权贵之士的标记。”
雪晴点了点头,“我以前也没想到是什么,但上次接的那批军布,也有个标记,也如娘所说,虽不相同,却有相似之处,后来我撞到那衙差,多嘴问了句,他当时就说我呢,说我一个妇道人家,不认得也是正常,那是京里梁大人的标记。”
陆太太看向她手中正慢慢打着转的小金珠,“那这……”
雪晴将那金珠转过来,图案朝上,“或者这正如娘所说的,是哪个臣中命官或者权贵中人的标记。”
陆太太看那金珠因为年日已久,有些色陈,但仍能看得出打磨的极为光滑细致,那图案雕得更是精致之极,中间穿了小孔,象是可以穿绳索之用,“那这东西,你到底从哪儿来的?”
雪晴神色一黯,“这是子容的。”
“什么?”陆太太一声惊呼,忙捂住了嘴,“他哪来的这东西?怎么从来没听他说起过?”
雪晴望了望门口,仔细听过,确定没有人听见她们谈话才道:“娘保证不告诉任何人,包括爹爹,我就告诉您。”
陆太太见女人如此谨重,点了点头,“我听了就烂在肚子里。”
雪晴将小金珠放回荷包,小心的扎上封口,捏在手上把玩,“这是子容没到我们家前就有的。”
陆太太愣了愣,“这怎么可能?他那身衣衫是我和你爹给他换下来的,你爹亲手烧的,什么也没有,几时见过这东西……”说到这儿,蓦然住了嘴。
当年,她给子容脱衣裳,他脖子上挂着一个小荷包,她当时不好解开来看,但倒是捏了两下,里面装的确实是珠子一类的东西。
难道就是这个……
雪晴紧紧攥着那个荷包,另一只把玩着下面的黑黄交替的穗子,“真是他的,那天我出去接着扫门口的雪,拾到了这个,当时也不知什么,又是哪儿来的,却认得是金子,以为是哪个过路的在门口休息落下了,便收了起来,等有人来寻,便还他。后来子容在门口翻着雪寻东西,我才留了心,问他寻什么,他开始不肯说。后来我总见他寻,又问了他,他才说寻一颗珠子。我当时就想到了这颗金珠子,但想着他都要饿死了,怎么还会有这样的东西,如果有这东西,还不会拿去当了换银子吗?就问了他寻什么样的珠子,看我有没有见过。”
陆太太不知怎么的心里抽了一下,“他怎么说的?”
“他见我问,便猜到了我是拾到了什么,就说了这珠子的模样。我取了珠子还他,问他为啥要饿死了,都不拿去当了。结果他接过珠子看了会儿,又交到我手上,说这是他爹留给他的唯一的一样东西,让我帮他好生收着,不能给任何人看,也不能告诉别人。我一听这话,就不肯接,他说他要东奔西走的干活,怕再丢了,让我帮他存着,他安心些,我才收下。这一晃,这么些年过去了,他也从来没提过这珠子,更没问我要来看过,也不知是不是把这事忘了。今天我把这事说给娘听,已经是违了我和他当年的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