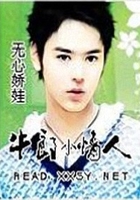“席先生,我也给你讲个故事吧,不过这个故事不长,也不是发生在什么豪门贵族,只是一个平凡人的故事——一个年轻的女人爱上了一个英俊帅气、能言善辩的男人并嫁给了他,婚后那个男人却背叛了她,与初恋情人远走天涯,那个女人独立将女儿抚养成人,却从不教她去恨,要求她爱自己更爱别人。”
“后来她的那个女儿长大的,很健康自强的一个人,虽然她的成长清贫而艰辛,可是她并没有因此泯灭良好的性情,变得恣睢而狭隘,因为她的那个母亲教过她——种植爱的信念,就会收获良好的心态。”
“如今她的那个女儿长大了,并有了自己的事业,也许在有些人眼中她是卑微平凡,不值一提的,但是她却很满足,因为她活的本分快乐,独立自由,用自己辛苦赚的钱养活自己,在这个生活的舞台上不仅活出了平凡的精彩,还让别人因为她的存在而幸福着。”
“那个女儿就是我!”
蒋穆纯说完在席维彦那灼亮的目光中打开车门走了下来,然后对着车子的男子轻笑着摇摇手。
“再见,席先生!”
雪不知何时已经停了,昏暗的路灯下,蒋穆纯站在路边看着那计程车疾驰而去,不由得暗暗叹息,又损失了好几十元的车子。
不过即使损失再多的车钱,她也不愿在和那个如狼似虎的男人再多呆一刻。因为那个男人太危险太可怕又太贪婪,她只怕她这只小麻雀到时被吃的连骨头都不剩,她确实怕了他,不想再体会那种心机用尽、步步为营的感觉。
人烟稀少的路上,蒋穆纯倦怠的脉动着步子向小区行进,她实在太累了,不只身累,心更累。这一场场的战争都打得太艰难了,再加上那个让她热泪涌流的故事,她真觉得自己已耗尽了元神。
“你还回来呀?怎么没在外面过夜?”忽然一个冷冷的嘲讽声传了过来,不过似乎被凛冽的北风吹得微微颤抖。
“啊……”蒋穆纯循声望去,这才发现在墙边站着一个身披斗篷……不,毯子的人。
看着那个披着毯子站在雪地里的高瘦身影,蒋穆纯勉强的一笑道:“你怎么披个毯子站在这儿?真滑稽!”
因为担心她,已经在这里等了将近两个钟头的莫俊烈一听这话顿时满腹怨气的控诉道:“你又不让我穿你的衣服,我再不披毯子,在这里等这么半天,难道你要让我冻成冰糕吗?你这个死女人,你真没良心,我站在这里还不是怕你有事吗……”
可话说到这里又猛地打住,微微一顿,然后又嘴硬的补充道:“你别得意,我可不是担心你,我只怕到时你出了事,没人给我煮饭吃而已。”
蒋穆纯定定的看了那站在雪地里瑟瑟发抖的人,心里的某根柔软的弦猛然间被触动了,忽然想起了小时候母亲每个黄昏等在家门口的那清瘦身影,多少年如一日,耐心执着,泪水霎时间朦胧了视线。
莫俊烈可能感觉出了不对劲,急急地凑了过来,当看到蒋穆纯满脸的泪水时,狭长的眸子不由得一缩。
可是这要怎么做呢?
面对着一个哭泣的女人,不舍的也不可以抽身走掉,要哄吗?可该怎么哄呢?
他不自然的搓了搓手,然后呐呐的开口道:“木糖醇,你……你哭什么?你就是哭也没用,下顿饭还要你煮,我……我不会煮的。”
看着那眼前那紧张无措的倔强少年,看着那狭长眸子里的真实的关切之情,蒋穆纯只觉得胸腔中有一股淡淡的暖意流淌,冰冷的身子似乎在霎时间也暖了起来。
“我累了,上楼去吧,外面太冷!”蒋穆纯轻声道,然后转身向着前面的公寓楼区走去。
“你冷吗?那毯子给你披吧!”
莫俊烈见蒋穆纯好像并没有生气,嘴角不由暗暗地翘了起来,快步追上蒋穆纯将毯子披在蒋穆纯的身上。
“你怎么了?流了好多血,有人欺负你了吗?”但是忽然间他的眸光一凛,一把抓住蒋穆纯的袖子道。
“没有,我……我没事,你看看我并没有受伤呀,是……别人的血。”蒋穆纯本想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可是不知为什么却鼻子一酸,纷纷落下泪来……
莫俊烈看着那无声落泪的女人,只觉得心里有麻麻辣辣的闷痛泛上心来,他禁不住狠狠地攥紧拳头,骨节发出清脆的响声。
这份森冷而凝滞的气场让蒋穆纯不由一阵心惊,莫俊烈的血腥和暴力她是深刻领教过的,她可不想将他牵扯进来。
她做中学的小女生时,就没有享受过男生为她打架的待遇,如今对这种事更是敬而远之。
“回来的时候,我碰到了一个摔破膝盖的孩子,这血是染得她的!”她随口扯了一个谎,说着还撸起自己的袖子让他看,“我手臂上根本就没有一丝的伤,哪里会流血?。”
语毕又定定的看着莫俊烈俏皮的道:“怎么?我若要被人欺负了,你会去帮我打架吗?”
“啊……”莫俊烈一怔,随后不屑的道,“哼,臭美!”然后径直上楼去了。
看着前面那个高瘦的背影,蒋穆纯清丽的脸上禁不住露出轻松而愉悦的笑容。
还是这个死小孩好骗!
但她却不知道她口中的这个死小孩并不是她认为的那么简单。
她的特异之处根本就瞒不过这个在不知不觉中对她早已是情根深种的少年,他早在她从急速飞驰的机车上跳下来的那次就感觉出她的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