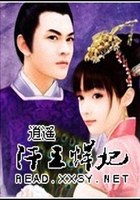张氏悲愤地哽咽,几欲昏死过去,可是偏偏没晕过去,只能清醒地忍受着这通天的屈辱。
曹老太太烤着火盆,曹家姐妹和俞筱晚围着说笑话给老太太听,俞筱晚面色如常,心里却嘀咕了起来,怎么还是这么安静?已经过去一柱香的功夫了。
她的计划是,让欧阳辰拦在路上,大声跟舅母张氏打招呼,只要说上几句老情人之类的暧昧话,让寺庙的僧人,和两府的丫头们听到就成。女人的名声经不得一点风吹浪打,有男人来跟舅母暧昧,就算舅父相信舅母是清白的,碍于面子也不会再让舅母主持家务,而且极有可能把舅母打发到家庙里去。
青灯古佛,对于极度热爱权势和名利的舅母来说,会比死了更痛苦!
俞筱晚暗暗掐紧了袖缘,她不用舅母死于非命,她只需她永堕无边地狱,活生生地饱受煎熬,她才能算是报了大仇。
只是,为什么还没有任何消息传来,难道是欧阳辰没能靠近,亦或是他突然改变了主意?
俞筱晚猜得没错,欧阳辰是自己改变了主意。一开始他一心想杀了张氏和张夫人,待沈天河告诉他让她们失去所拥有的一切,才是最好的报复方法之后,他才重新开始思考自己的复仇计划。他是个商人,狡猾奸诈,又生意失败,所以便想到了一条拿捏住张氏和张夫人法子,这样才能生生世世,永无止尽地从她们那里拿银子。
张氏怎么也躲不掉那四只手两张嘴,浑身哆嗦着,也不知是愤怒的还是惊惶的,被人作贱了个够,才听得为首的男人道:“好了,得走了。”说着也走过来,在张氏的胸上摸了一把,极为惋惜地道:“这娘们的皮肤嫩多了,早知道我该摸她的。”
然后站起来,将张夫人和张氏的肚兜往自己怀里一揣,又各从她们头上拔了一支簪子,笑得十分邪恶,“你们两个以后都算是我的半个娘子了,当娘子的要帮夫君操持家务,以后记得每月弄点银子给为夫花花。为夫要得也不多,每个月三百两就成了。”
张氏一边哆嗦着穿衣,一边抖着声音啐他,“做梦!”
那男人的脸瞬间狰狞,眼神阴狠,“做梦?那我就把你的肚兜拿到大街上挂起来,让大家都来看看新建伯夫人的肚兜是个什么花样的,你说好不好?”
张氏怒瞪他,“你以为旁人会信?”
那男人笑得极度阴险,“加上你胸口有颗红痣,你说旁人会不会信?我也不求多了,只要你家爵爷相信就成了!”
张氏的脸也瞬间苍白,又气又羞又窘,更多的却是惧,这种人,是穷凶极恶的,是无耻没有边界的,他一无所有,什么都不怕,可她却有名誉有地位有儿女,不能不惧,不能不怕。张氏低头哆嗦了半晌,才挤出一点声音道:“我没这么多银子。”
那男人露出嘲讽的笑容,“你们两个都有嫁妆,还有要当侧妃的女儿侄女,这点银子还拿不出来么?哼!”说罢不再纠缠,挥手道:“我们走。”
走到外间,看到曲妈妈和王妈妈两个手脚被捆着缩成一团,那男人“好心好意”地道:“给她们解了绑吧。”
曲妈妈和王妈妈恨不能化成一个小点,钻到地缝里去,救不了主子,又看到了这样的事情,她们俩个只怕是会……可是手脚上的束缚被解开,身为奴才,还是必须去服侍主子。两人手脚并用地爬到里间,服侍着两位夫人穿戴整齐,重新蓖了发。
张氏忽然象疯了一般直朝张夫人冲过去,王妈妈赶紧拦在主子跟前,张氏就揪着她的头发压低声音嘶吼,“都是你这个贱妇!”
王妈妈的头皮都快被张氏揪掉了,却不敢发作,只苦苦哀求张氏住手。一直不言不语的张夫人忽然发作起来,跳起来,隔着王妈妈扬手给了张氏一个耳光,“都是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你还好意思说!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欧阳辰,武氏不给银子,就把主意打到我们两的头上!”
张夫人越说越气,好象要发泄似的,“我们找他是为什么,还不就是为了你,为了你能稳稳地当你的正室夫人,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反而害得我受牵连。”
张氏愣了几愣,随即反驳道:“什么叫我没用,还不是你没跟他说好,后来明明还有机会的。再说了,这也是为了你家君瑶。”
张夫人冷哼,一口唾沫吐到张氏的脸上,“我家君瑶是堂堂的侧妃,这回入选的五人中,她的份位是最高的,要不是为了帮你这个姑母,她用得着这种下作手段?我告诉你,从今以后咱们我走我的阳关道,你过你的独木桥,别想再让我帮你。王妈妈,咱们走。”说着扶着王妈妈的手往外走,虽然腿还软着,虽然走得不稳……走到一半又顿住身形,回头鄙视道:“蠢得象猪一样,你就等着被武氏给挤出曹家吧!”
张氏气得浑身颤抖,回敬了一句,“你老得也就那个男人肯摸了,就等着我大哥的通房生上十来个庶子庶女吧。”
张夫人顿时怒目而视,张氏也毫不怯场地瞪回去,两个妈妈忙各拦各的主子,“曹老太太还在香房里等着呢,已经出来半个多时辰了……”
两人这才察觉不妙,又互瞪了一眼,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色厉内荏,知道对方不会将今天的丑事说出去,这才暗暗放了放心,互不理采。出了小屋,顺着一条小道往前走过一个月亮门,才发现这仍是西院……幸亏早将此地隔了出来,闲杂人等不能入内,两人同时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