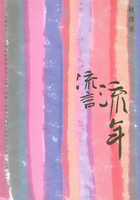我仔细地看着老印手指停留的地方,上面写着:
自一九五六年四月十日起至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日止
我嘟囔了两遍之后,突然发现了端倪,于是满口惊讶地说:“1956年4月20日,这不正是你老婆出事的那天吗?也就是说,你的两位结拜兄弟张树海、李光明审讯战士冯健结束,从这天之后他们就失踪了……”我看了两眼老印,接着问道:“这会不会仅仅是巧合?”
老印摇摇头:“我在怀疑这种巧合的概率有多大。赫子,让我们来大胆地推测一二。假如这不是巧合的话,那么他俩一定是审讯战士冯健的时候发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换句话说,张树海、李光明发现的东西诱发了他们最终的失踪!只要我们从这个逻辑着手,必定会把他们找出来,找出他们之后,我不就可以问清当日他们跟我老婆说了什么吗?”
我说:“你的意思是,准备在卷宗里寻找促使他们失踪的原因?”
老印狠狠地击了下手掌:“对。目前这份卷宗只有第一册,刚刚我阅读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足以让他们销声匿迹的线索。我想其中的秘密必然就在第二册上。只要我们找到卷宗的第二册,让这份卷宗完整起来,那么一切不就水到渠成了吗?没错,我们必须找到第二册卷宗。”
老印满脸的激动不已无法遏制地感染了我。毕竟这份神秘的卷宗已经折磨了我许多个夜晚,只要找到它的第二册,我岂不是可以重新享受游离已久的高质量睡眠?我想着从前睡梦中时常出现的那些温婉可爱、笑靥如花的姑娘,她们云飞雪落般的神情不禁让我会心一笑。老印见我莫名其妙地傻笑,一脸疑惑。我连忙收敛自己的失态,正言道:“好。印老,就让我们联合起来放手一搏,直捣黄龙,查出事情的真相。”我想起警队长时常挂在嘴边的话,最后又补充道:“显我警威!”
大概是因为我的豪言壮语吹过了头,说完这些之后,激动的嘴巴竟一时有些回不过神,我忙问老印:“那么,接下来咱们该干什么?”
老印先是冲着服务员摆摆手,然后故作神秘地说:“结账。”
我和老印走出宋家屯美食城时,天色已经有些黯淡。熙熙攘攘的街道上车铃此起彼伏,“永久”和“凤凰”依次从身边闪过。老印跟我告别之前,问我能不能把卷宗再借他看上一晚,我不由分说便给了他,随后又半开玩笑地说:“小心卷宗里的人让你睡不好觉。”
老印撇嘴笑道:“我已经很多年没睡过一个好觉啦,兴许有卷宗里的人陪陪,反而会睡得更踏实。”
我看着老印瘦小的背影消失在清脆的车铃声中,突然觉得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心里便有些怅然起来,香烟不知不觉便叼在了嘴里。但是这种情绪只停留了片刻就消失得了无影踪——在穿梭不止的人流中,我一下子看到了波涛汹涌,姑娘们穿在身上略带透明的的确良衬衣总会让我流连忘返,尤其是她们费力地蹬着自行车时,晃动的姹紫嫣红把整个夏天都照得无比迷人。
翌日一早,我和老印以查案为由来到卅街档案馆办公室。由于之前那场熊熊烈火,所有的档案目前都临时存放在一间废弃的仓库之内。在年轻的档案管理员小李的带领下,我们走进了混合着灰土味和淡淡燎灼味的仓库,堆积的档案足足占领了仓库的半壁江山,它的数量让我此前的信誓旦旦瞬间就萎缩了半截。而老印则不动声色地仔细找寻起来,因为此前对他的承诺留下了把柄,我也只好硬着头皮扑向堆积如山的纸片。
三天之后,我的鼻孔已经彻底被霉味占据,甚至连香烟的浓厚味道都无法遏制它们的生长,只是我和老印的苦苦努力,最终却只换来了连连的腰酸背疼。这是一个让人沮丧不已的结果。不得已我们只好请求小李把存档目录拿给我们,但是翻遍了所有的目录后我们依然一无所获。老印满脸疲惫地向我提出质疑:“赫子,那份卷宗你确认真的是从档案馆里散出来的吗?”
我肯定地回答了他之后,说道:“该不会是因为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没有记载在目录里吧?或者,你曾经说过通化城的档案不应该出现在我市,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原因呢?”
老印面色凝重地踟蹰了一会儿,忽然问我:“赫子,你还记得当时运送这批档案的司机吗?我想咱们应该找他了解了解情况,说不定会查出一些眉目。”
于是,我和老印开始从这个方向着手,通过多番打听终于找到了那名司机。只是他听完我们的询问后,一脸惊悚地说:“你们是说,那些封面带着红色‘慎’字阴文印章的绝密卷宗?如果是的话,我劝你们最好就此打消继续找寻的念头。”
司机的语气里充满战战兢兢,这让我和老印不禁错愕起来。老印毕竟在人情世故这方面经验丰富,他说笑间由包里掏出一支烟给司机点燃,接着顺手把烟盒塞进司机的兜里,然后又掏出一盒未开封的也塞了进去。司机夹着香烟抽了一口,烟雾和他的得意同时冲出嘴巴:“他娘的,还是这阿诗玛带劲。敞亮。老敞亮啦!”
老印笑着说:“你先抽着,回头我再帮你弄两盒。”
司机立即喜笑颜开:“好吧,我把知道的通通都告诉你们,不为别的,就为你这两盒阿诗玛。那天,我把整车的档案由卅街运到废弃的仓库以后,等待接收的工作人员只有两个人,他们一老一少,好像都是档案管理员。我听见那个老的管那个年轻的叫小李。老管理员很紧张,吩咐身边小李不要管旁的档案,先找封皮带‘慎’字阴文印章的那些。结果两个人跳上车,把整车档案翻了个底儿朝天,凡是封皮没有印章的他们通通不在乎,像是扔垃圾一样往地上撇。我见他们忙得满头大汗,也只好上去帮忙寻找。后来我们仨从上午十点多钟一直忙活到傍晚,总算把那些带印章的档案全都剔出来了。”
老印惊讶地问道:“你是说那些带‘慎’字阴文印章的档案不是一份两份,而是有一堆?”
司机撇嘴道:“好多咧!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打开一份,还没看两眼就被老管理员一把抢在手里。他横眉立目地骂我,不要命啦!这些都是绝密文件,看了会死人的。我当时心里恨得直骂娘,心想老子辛辛苦苦帮你们忙活,你反倒给我整这么一句。可是老管理员后来又满脸哀求地跟我说,千万不要再跟第四个人说起这些档案,这关系到他余下的风烛残年能不能过得安生。我见他这么认真于是就答应了他,他连连称谢,最后还感激得流下了眼泪。后来老管理员和小李把那堆带‘慎’字阴文印章的卷宗——起码得有百十来卷——通通放在一辆手推车上,然后小心翼翼地弄走了。事情经过就是这样。后来我觉得这些档案可能真的事关重大,想来也有些后怕……所以,今天我把这事告诉你们了,你们以后千万别说是我抖搂出来的。”
老印拍了拍司机的肩膀:“放心吧,绝对不会的。”
说着他把手伸进司机的兜里扯出两根阿诗玛,一根夹在了自己的耳朵上,另一根撇给了我。我们拐进胡同之后,老印嘟囔出一句让我吃惊不小的话:“干!赫子,那是两盒阿诗玛哇!我他娘的一个月都舍不得抽上一根。”
我嗤笑了一声:“这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下一步咱该干吗?”
老印把夹在耳朵上的阿诗玛小心翼翼地放在兜里,然后说:“咱们去卅街,打听打听那个老管理员的情况。”
我们马不停蹄地重新返回卅街档案馆办公室,通过询问小李才得知老管理员已经退休。我们要来了他的地址之后,简单地到宋家屯美食城吃了些东西,接着便按照字条上的地址飞奔而去。
老管理员住在我市城西一幢破烂不堪的旧楼里。他对我们的到来显得非常吃惊,连忙将堆积在沙发上的旧书搬开,空出了两块能放下屁股的地方。我环顾四周,发现整间屋子倒像一家旧书店,满坑满谷的书籍歪歪扭扭堆砌得铺天盖地,一股刺鼻的书霉味驱逐了夏日的光线,不禁让我脚底腾升起一阵寒气。
老印把早已准备的糖水罐头推给老管理员,他说:“这是孝敬您老的。”
老管理员正言道:“可不敢。公安同志,有什么事情需要老头子帮忙吗?”
老印清了清嗓子:“确实有点小事。我们手头上有个案子需要查阅两份卷宗——就是封面带有‘慎’字阴文印章的那批,听说您知道它们的下落。能不能……”
老管理员“霍”的一声站起身来,他举起的手臂停在空中拼命地抖着,突然指向房门:“公安同志,老头子不知道什么‘慎’字阴文印章的卷宗!如果你们没别的事情尽快离开吧。”
老印像是早有预料,他说:“老人家,我们都已经调查得清清楚楚,那批卷宗就在您手里。如果您不交出来,我们可要说您私吞公共财产,同时再给加上一条妨碍公安办案的罪名。您可得想清楚喽。”
老管理员显然被老印的恐吓给唬住了,他支支吾吾了好一阵儿才满声叹息地说:“我都一把老骨头啦,你们现在就可以把我带走。我只是不想再死人了,我已经被搞得家破人亡,你们就放过我吧。”老管理员说着说着竟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就近的书籍稀里哗啦砸在了他的身上。老印见状连忙俯身去掐他的人中,他颤巍巍地指着自己的裤兜说:“药。”
我赶紧将药瓶掏了出来把药片塞入他的嘴里,老管理员干噎了两下之后又要水,喝了两口他才缓过劲儿来。待老印把他扶起来后,他连连哀求道:“你们就听我一句劝,不要再找那些东西啦。老头子一把年纪不会害你们。再说,那些……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烧掉了。我知道我这么干犯了法,但是要能多救下两条人命我也值当了。你们赶紧走。走。不要再来!”
老管理员这番话让我摸不着头脑,我在心里重重地打了一个问号:难道区区的一份卷宗真的能要人命?我绝不相信这是真的。这其中一定有什么难以言说的隐情。
老印见他的情绪仍然波动不止,于是冲着我使了使眼色。老印对老管理员说:“老人家,您好好歇息吧,保重身体要紧。”
我垂头丧气地跟着老印离开老管理员的家,待下楼之后,我急不可耐地说:“印老,这事就这么完了?”
老印说:“我觉得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先是这些卷宗来历不明,而且封面上的‘慎’字阴文印章,似乎并不符合处理档案的一贯作风。据我所知,如果卷宗确实很重要的话,顶多也就是在封面加上机密或者绝密的字样。现在老管理员又说看了它们会死人,这就更蹊跷了。会不会是……”
我见老印有些欲言又止,忙问道:“会不会是什么?”
老印瞄了瞄四周才压低声音说:“我曾经听一个老警察说过,国家有一部分档案是永久尘封的。这些档案牵扯了许多无法解释的事件,所以被特殊机构故意秘密藏匿了起来,为的是只让少数人知道,不致引起民众们恐慌。当时我以为他跟我胡诌,就没怎么放在心上。依目前的情况来看,八成真有这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