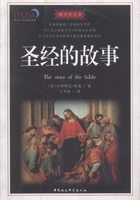对于可凡这个人名。
其实,堇祎是做过挣扎的。
不然,她也不会在下班后去健身房做瑜伽,听玄学。
不然,她也不会遇到她。
也许是时间地点不对,她笑。有些人很好,但未必成为朋友。
原以为能找到像伯牙和钟子期那样高山流水的知音,海阔天空,相依相伴。现在发现什么事情都不能说的太早。
很久以前,我就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我对你说过,生活有时是无法选择的。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人。就好像是你喜欢商场里形形色色的鞋子,当它们摆在打满灯光的橱窗里时是那么明艳动人,穿在脚上却不一定合脚。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
那是个奇怪的瑜伽教练,所以她的养生瑜伽课总是爆满。
一般教练通常只是那些单调的口号:呼气,吸气,感受你的气运到了肩膀,然后整个肩膀松弛下来。诸如此类。
再高档次的会告诉你:想象你躺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然后蓝天白云,你看着它们,你整个人都感觉神清气爽了,你要全身放松。
听听,万变不离其宗,总归要回到这里。
兜兜转转一大圈,总要回到原点。
每个人都是如此,不是吗?
其实,堇祎是做过挣扎的。
因为,往往想逃避现世的人都喜欢谈老庄。
瑜伽课上,宋芷若大段大段的说辞。
堇祎好像真的忘却了,忘却了所有的所有。
忘情寡欲,心斋坐忘。
何其美好。
每节课,堇祎都固定的把天蓝色垫子放在靠门的角落里,然后静静地端详坐在前面的,梳着马尾,黑漆的头发垂到腰际,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黄金比例的,雕塑一般的人物。每次,她冲那个人微笑,却从来不关注是否有回应。
那一次,在呼吸吐纳之间,每一个都沉静了下来,空气中也氤氲着凝固的静谧。每一个像被催了眠,背景音乐是《天空》,她让我们顺着意境将头深深埋进肩膀搭成的所谓的桥,想象自己是一只受难的鸵鸟,但不能有任何惊慌。
这时候,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又开了腔:
法国的哲学家帕斯卡曾经这样说过,
人,不过是一棵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不用整个宇宙拿起武器,才能将他消灭。
一滴水,一口气,都足以将人类置于死地。
但是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他仍然比置于他死命的东西,更加高贵。
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对于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却一无所知,所以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现在,请大家慢慢地抬起你高贵的头颅,
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
阳光普照,有什么事情是你所不能磨合的呢?
那已经是堇祎在这里的第六十四次课了。
一个巨大的声响从她那里发出,人们忘了那是嗤笑、咳嗽、喷嚏还是别的什么。总之,这些都不重要了。
总之,她们就这么相识了。
关于名字,她们经常互相开这么一个玩笑……
“师太,玉女心经不要走火入魔了。”
“锦衣卫最近有什么新任务啊?”
有那么一段时间,她们终日黏在一起,就像需要做手术才能分开的连体婴一样。
堇祎一直一直听《下一个天亮》,单曲循环播放。
为的只是告诉自己:如果黑夜太漫长,便许自己一个天亮。
两个女人不能终日聊老庄,聊人生,聊信仰。
尽管一个整日坐在电脑前码字与文字为伴,一个修身养性愉悦灵魂。我想,她们还是凡人。
对,凡人。活在浮华都市的,寂寞的,女人。
谈到感情经历,两个人常常去一些白天惹她们诟病的地方,买醉。
堇祎知道芷若也是个命苦的女人。在醉酒后颠三倒四的陈述中,堇祎还是整理出来了一些。28岁,丧夫,新婚丈夫在执行任务中不幸离去了。
堇祎知道这时候不该像电视上那样对她丈夫一番歌功颂德,什么死重于泰山,死得其所,什么他的死是伟大的,是光荣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对于她来讲全是放屁。就连一起崇拜的庄子“鼓盆和而歌”也完全是没人性的典型写照。
是,很多人表面上仁义道德,实质上一肚子男欢女爱,或许,不该去盲目批判他们。
只是很多事情没有摊到你身上。
这些事情也只是她告诉,堇祎知道,堇祎也没有读心术。
可是芷若却读懂了,她说,你很孤独。然后摇摇头,不,你不只是孤独这么简单。你拥有过,或者说,正在拥有。
似乎所有的心事都被她了然于心,真可怕。
我看得出来,你还没有同命运握手言和,姑娘。她说。
你很执拗啊,或许,你能撑一辈子。她也说。
是异地恋吗?
我知道那种感觉,就是你和单身并没有多大差别。于是,一个新的纠结体就产生了。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想他的时候,你不确定他有没有也在想你。你开始不安,开始缺乏安全感,开始情绪化。你难过的时候,你哭泣的时候,你会想,如果你在就好了,那样我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狼狈,但是你只是凭空这么想,毫无用处,没人陪在你身边,没人同情你廉价的眼泪。走过所有艰辛的路,你发现,你还是自己一个人。但是,你仍不甘心放弃这段感情,毕竟好过单身,至少世界上有个人承认你的身份,但是,你又不如单身轻松自在,没有负担,你身上背着沉重的甜蜜的负荷,始终不愿放下。
但你,始终还是一个人。
“哼”,堇祎从鼻尖发出一声不知是何情绪的声音,音色也怪的异样,让芷若也睁大了眼睛,想知道下文。
你终于猜错一次了。
我承认,异地恋很痛苦。
真的,很痛苦很痛苦。
说什么只要有爱,没有逾越不了的鸿沟。
全他妈扯淡!
不过,有距离的恋爱总算好过我。
所有异地恋的男男女女都应该认识我,有我给他们垫底。
因为我甚至不知我恋的人是生是死。
哈,这其实也算说的过去。
不过,我甚至不知道我恋的人究竟是谁,
是真实的某一个人还是,
只是我的一场幻觉。
这话打破了聒噪,两个人陷入了缄默。
一向对情感问题讳莫如深的堇祎这次将她和盘托出了。
跟我走!
芷若把她拉走了。
一路狂奔。
两个人突然异常的清醒。
上天给她们制造了戏剧性的一幕,然后,她们居然真的跟着这节奏表演了起来。荒诞得让人笑不出来。
十二月份的天气,很冷很冷。
没有鹅毛大雪,却下起了瓢泼大雨。
狂风骤雨中。
芷若的脸凑近了。
没有温热的气息。
冷的仿佛冻结成冰。
堇祎最讨厌的温度。
来不及看清她的眼色和表情。
倔强的不容许任何回旋的余地。
堇祎感到自己的身体被牢牢地揽住,动弹不得。
她的唇齿突然被一股外力分开了。
反应过来的时候,却怎么也挣不开。
还是奋力挣扎。
除了身体,还有唇齿间的余力。
突然,她挣开了。
她感到嘴里滞留的是,
是咸涩的血腥味。
她低着头。
冷冷地说了一句,变态。
然后落荒而逃。
始终不曾记得看一看,那个雕塑一般的女人有着怎样的面色。
她不敢。
唯有,
拼命地逃。
拼命地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