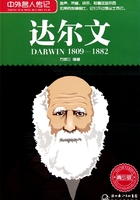他和我二哥是同班同学,本是我二哥的朋友。其实我很清楚他的缺点,但我坚持把他当一个忠实的朋友看待。母亲、大哥和妻子都告诫我,说我交友不慎。为了维持丈夫的尊严,我并没有把妻子的提醒放在心上,但却不敢不听母亲和大哥的建议。我仍坚持为他辩护:“我知道你们所说的他的缺点,可是他也有你们不知道的优点。他不会把我带坏,而我和他交朋友正可以改造他。如果他改过自新,一定会成为一个有作为的人。请你们不要担心我。”
我也不知道我的话是否能让家人放心,总之最后他们不再过问了。
后来事实证明我的想法错了。一个革新者是不应与他要改造的对象保持过于亲密的关系的。真正的友谊是灵魂上的契合,然而这是人间稀少的巧合。只有性情相投的两人才能结成高贵持久的友谊。
朋友是互相影响的,所以友谊中几乎没有改造的余地。我们应该尽量避免那种排他性的亲密关系,因为人容易学坏,却不容易学好,要么就孤独地与神灵面对面,要么就和全世界的人为友。也许我的想法是错误的,无论怎样,我想要培养亲密友谊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我刚遇到这个朋友时,一场“改革”的热潮正冲击着拉奇科特。他说我们的老师中有不少人背地里吃肉喝酒,还列举了本地许多有名的人,甚至有一些中学生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我既讶异又难过,向他追问原因。他解释道:“我们之所以是一个孱弱的民族,正是因为我们不吃肉。英国人之所以能够统治我们,就是因为他们吃肉。你是知道的,我身体强健,跑得也快,是因为我也吃肉。吃肉的人不会长血瘤,偶然长上了瘤也好得快。那些老师和社会名流并不是傻子,有好处他们才吃肉。你也不妨试试看,不要紧,亲自体验一下效果。”
他诱导我吃肉并不是一次和盘托出的,而是一次又一次的深入引导。我二哥已经坠入此道,因此他也支持我这位朋友说的话。同我二哥和那位朋友比起来,我确实显得很单薄,他们都比我结实、强壮、胆大。我当时也真的被这个朋友的技能迷住了,他跑步时速度又快耐力又强,跳高跳远也很棒,多重的体罚他都受得了,还常常在我面前展示他的技能。当一个人在别人身上看到自己不具备的才能时,常常会为之神往,我也是这样的。此时我有一种想赶上他的强烈欲望。我既不能跳,也不擅长跑,怎样能像他那样强壮?而且我还是一个胆小鬼:怕贼、怕鬼、怕蛇,夜里我甚至不敢到室外走动,恐惧常萦绕在我的心里。对我而言,黑暗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在黑暗里,我根本睡不着,我怕要么这一边来鬼,要么那一边来贼,或是另一边又来蛇。因此,如果房里没灯,我就不能入睡。我怎么好把这些都告诉睡我身边的妻子呢?那时她已经不是小孩了,也是一个青年了。我知道她比我勇敢,为此我常常自惭。她不怕蛇和鬼,夜里也敢出去。我的朋友非常清楚我的这些弱点。他说因为他吃肉,所以能抓住活蛇,不怕贼,也不信什么鬼。
当时,同学圈子里面流传着古遮拉特诗人纳玛德的一首诗:英人高大威猛,印人渺小可怜;强者盖因食肉,弱者必被其治。
我在这一切的影响下,终于妥协了,也渐渐地认同了吃肉有益这种观点,以为吃肉能使我身强体壮,胆识过人;以为如果全国民众都吃肉的话,便可战胜英国人。
于是我们便选定了一日,在那天开始了肉食体验。这一切必须秘密进行。我们家族都是毗湿奴信徒,我的父母更是笃信宗教,他们经常定期到哈维立的神庙参拜。我们家族也有自己的神庙,除此之外,古遮拉特盛行耆那教(Jainism)[产生于公元前6—5世纪,几乎与佛教同时。它提倡刻苦牺牲,消除物欲,自救而不被世俗所累。它有五个信条:一讲真言,二尚清贫,三不杀生,四不偷盗,五守贞洁。耆那教与印度教很像,因而教徒与印度教徒可通婚。
],这个教派随时随地都在影响我。耆那教徒和毗湿奴信徒都极其反对和厌恶吃肉,其厌恶程度是印度的其他地方或印度以外任何地方都罕有的。我成长在这样的传统下,况且我十分孝顺我的父母,所以一旦他们知道我破戒吃肉这件事,一定会吓坏的。再加上,出于对真理的热诚,我一定要谨慎从事。我并非不知道吃肉就是欺骗父母,但当时,我是为了“改革”,并不是逞口腹之欲,我并不觉得肉特别好吃,更多的是希望我自己和我的同胞变得强壮勇敢,从而打倒英国人而使印度获得解放。我倒还没听过“自治”这个词,但已经明白自由的意义。这种“改革”的欲望蒙蔽了自己。既然这件事是秘密进行,我便说服了自己:仅仅隐瞒着父母,算不得是违背真理。
七 一个悲剧(下)
体验吃肉的日子终于到了,很难描述那天复杂的心情。一方面,我好奇地抱着“改革”的热望,另一方面,却又惭愧自己像贼一样偷偷摸摸地做这件事。到底哪一种心情占上风,连我自己都分不清了。我们到河边找了一个僻静之地,在此处,我生平第一次看见了肉,还有面包店里买来的面包。我吃不出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味道。那天的山羊肉硬得像牛皮一样,根本无法下咽。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丢下。
那天夜里我很难过,一直在做噩梦。每当快睡着时,总感觉到肚子里有一只活山羊在苦苦哀叫,然后我就会懊悔得惊跳坐起。后来,我只好自慰道:吃肉是在履行一种责任,这样想想我的心情就会平复了。
我的朋友可不肯轻易罢休。接下来,他变着样地准备肉食,真是色香俱全。而我们聚餐的地方也不再选在河边僻处,而是在一家政府宾馆的餐厅里,桌椅应有尽有,都是我朋友和那里的主厨特别布置的。这种诱惑果然生效了,我先是爱吃洋面包,然后也不再对山羊抱有怜悯之心,虽然也并不很喜欢吃肉,但可以接受了。这种情况继续了约一年之久。不过实际上只吃了五六次肉,因为政府宾馆并非每天开放,而且经常准备那么多好吃昂贵的肉食也有困难。事实上,我并没钱来支付这种“改革”,每次都是我朋友筹钱。至于他的钱从何而来,我一无所知。可是他总是能弄到钱,因为他一心想把我变成肉食者。只是他的能力毕竟有限,所以后来这种肉食聚餐的次数就越来越少,间隔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每一次外出秘密聚餐时,就没法在家里吃饭了。母亲自然会叫我吃饭,而且还会问我不吃饭的原因。我总以“消化不良啊”,“今天没胃口啊”这样的托词来骗她,这让我不安。我知道自己在撒谎,还是向母亲撒谎。但我清楚,如果父母知道我变成了肉食者,他们会多么难过。这些念头总是咬噬着我的心。
因此我告诉自己:“尽管吃肉是必要的,在国内推行‘饮食改革’也是必要的,但向父母说谎比不吃肉更坏。所以在父母还活着的日子里,一定不可以再吃肉了。等到他们去世以后,我就可以随心所欲了,到那时,我便可以公开吃肉,不过在这以前,我绝不能吃肉了。”
我把这个决定告诉了我的朋友,从此再没有吃肉。我的父母丝毫不知道他的两个儿子一度成为肉食者这件事。
我不再吃肉是出于我的一种纯洁的愿望,即不愿向父母说谎。但我并没有和那位朋友绝交。我试图改造他的热望后来被证明对我而言是一种祸害,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就是这位朋友,差点诱惑我做出不忠于我妻子的事情来,还好最后得以幸免了。有一次,他把我带到妓院,还告诉我该怎么做,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连账都已经结了。我闯入了罪恶之窟,幸亏神灵以他无边的仁慈守护了我。在这淫邪之所,我几乎说不出话,看不见东西。我坐在那个女人的床边,什么也说不出来。她当然受不了,边辱骂着,边把我赶出门。作为男人的尊严被践踏,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然而真的永远感谢神灵拯救了我。回顾过往,我曾遇到四次类似的情形,最终得以解脱,绝大部分不在个人的努力,多半是幸运使然。
以严格的伦理观点来看待这类事情,无疑是道德败坏;因为这已然是肉欲的暴露,有这种想法和去做是同样的坏。但是以世俗的观点来看,一个人如果肉体上没有出轨,便已算是得救了。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获得了拯救。有时上天为他和身边的人作了安排,他就躲开了罪恶。一旦他醒悟过来,就会深深感谢神灵拯救他的慈悲。我们知道,就算有时一个人竭力去抵抗诱惑,终不免堕落;我们也看到,就算有时一个人要犯罪,而神灵却庇护他、拯救他。这究竟为什么,一个人究竟能获得多少自由,又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环境支配,究竟自由意志能发挥多大作用,命运究竟对我们产生多大的影响——这一切都是谜,而且永远是谜。
还是让我接着把这个故事讲完吧。哪怕是这件事,也没能使我认清这个朋友人品之恶劣。我因此还有许多惨痛的经历,直到我亲眼目睹他所做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劣行时,我才恍然大悟。有的留到后面再说,先按时间顺序讲。
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件事,我不得不提一提。还是因为这个朋友,我和妻子之间发生一些误会。我是一个既专情又妒忌的丈夫,这个朋友便火上浇油,挑拨离间我们的感情。我对他的话常常深信不疑,当初因为他的唆使,我粗暴地对待妻子,给了她诸多伤害,现在回想起来,真的无法原谅自己。大概只有印度教徒的妻子才能隐忍这种折磨,所以我常想:女子是宽忍的化身。做仆人的无故受了怀疑,可以辞工不干;做儿子的遇到同样的情形,可以离家出走;做朋友的则可以绝交;然而做妻子的,即便她怀疑自己的丈夫,也只能保持缄默;但如果做丈夫的怀疑了她,她就无路可走了,她能怎么办?一个印度教徒的妻子是不能向法庭申请离婚的,法律不能帮助她。我曾一度把妻子逼得走投无路,尽管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还是难以忘怀,始终无法饶恕自己。
直到我完全了解“非暴力”(Ahimsa)[意为不杀生,或不伤害。其核心是爱和感化,其方法是“坚持真理”。
]的真义后才得以根除怀疑这个毒瘤。我看到了“禁欲”(Brahmacharya)[照字面意思解,是引人到神灵那里去的行为。通常其意思为自制。
]的光辉后,才懂得妻子绝不是丈夫的奴隶,而是他的伴侣、助手,和他共享一切忧愁和欢乐。她有权像她的丈夫那样,选择自己要走的生活道路。每当想起那些充满猜忌的黑暗时光,我便痛恨自己的愚昧、荒唐和残忍,并为我盲目轻信这个损友而感到悲痛。
八 偷窃和赎罪
应当说一说,肉食时期以及这段时期前——差不多是结婚前后,我还犯过其他错误。
我和一个亲戚那时都喜欢上了抽烟。不是抽烟有什么好处,也不是迷恋烟草的味道,只是觉得吞云吐雾是一件好玩的事儿。我叔叔有这个嗜好,我们一看到他抽烟,就想学他。但我们没钱买烟,只好偷偷地捡叔叔扔掉的烟头抽。
烟头也并不是常有的,而且抽烟头也很没劲。因此我们便开始偷用人口袋里的零用钱,买印度本土产的烟卷抽。买来的香烟藏在哪儿呢,这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总不能当着长辈的面抽烟。这样偷钱买烟的勾当,我们干了好几个周。后来我们听说,有一种植物的梗中间有许多小孔,可以当烟,所以我们又开始抽这个了。
然而这些事还远远不能满足我们。我们无法忍受被束缚的感觉,做什么事都要经过长辈的许可,这让我们好难过。最后,我们厌世了,决定自杀!
然而到底怎样才能自杀呢?我们上哪儿去弄毒药呢?我们听说闹阳花的种子是一种好用的毒药,便去丛林里寻找,果然找到了。
想来想去,觉得晚上行事最适宜。我们晚上去了克达济神庙,把酥油倒进神灯上,参拜了神坛,找到一个僻静的角落准备自杀。然而到了最后那刻,我们失了勇气。“如果一下子死不了那怎么办?自杀究竟有什么好的?缺少一点自由就真的不能忍受吗?”这些念头在翻滚着,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吞下了两三粒闹阳花的种子。没敢多吃,我们俩都有些怕死了,于是决定到罗摩吉神庙去自我镇静一番,摈除自杀的念头。
我这个时候才明白:自杀是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此后,我听见有人嚷着要自杀时,全然不放在心上。
自杀的念头终于戒掉了我们俩抽烟和偷用人的钱去买烟的坏习惯。
长大成人后,我再也没有抽烟的欲望了。后来我总以为抽烟是一种野蛮的、肮脏的、有害的行为。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瘾君子。我无法忍受旅行时坐在一节充满烟气的车厢里,那样会窒息的。
然而不久以后我犯了比那种偷窃更严重的错误。偷零用钱那年是十二三岁——或可能更小时,十五岁时,我又犯过一次更严重的偷窃行为。这回是从我那位同是肉食者的哥哥的手镯上偷着撬下了一小点金子。那时他欠了一笔债,大约25个卢比。而他手上的镯子是纯金的,弄下一小块来并非难事。
金子到手了,债也还清了。然而这一回我实在不安,立志不再偷窃,决定向父亲坦白,可是我不敢和他当面谈,并不是怕挨打。不,我记得他从不打我们,我只是担心这件事会使他痛苦。但我还是要冒这个险,没有坦白的承认,就不能彻底的悔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