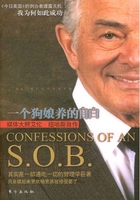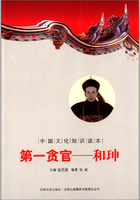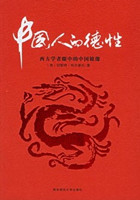航行十三天后,我们停泊在拉谟港口。我已经和船长成为好朋友了。他喜欢下棋,但完全是一个新手,特别需要一个棋艺更低的人做他的对手,因此他就邀请我一起玩。我倒是听说过怎样下棋,可是从来没有下过。精于此道的人常说,棋盘里有一片给人施展才智的广阔天地。船长主动教我,因为我很耐心,他觉得我是一个好学生。我每一次都输,于是他就更加热心的想要教我。我很喜欢下棋,但绝不沉迷,只在船上玩一玩,我对棋艺的理解仅限于移动棋子。
船在拉谟停泊了三四个钟头,我上岸去参观港口,船长也上岸了,他提醒我这个海港风浪很大,要我快去快回。
拉谟是个小地方。我去了邮局,很高兴在那儿见到了几个印度籍的职员,还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还见到了几个非洲人,我对他们的生活方式很有兴趣,就了解了一下,耽误了一些时间。
我在船上认识的几个统舱的乘客也上岸了,他们想在岸上做饭,好好地吃一顿。我发现他们正打算回船上去,便一起搭上一只小艇。港口的潮水在涨,而我们的小艇又超重了。浪潮如此猛烈,这只小艇搭不住轮船的吊梯,一挨到吊梯,就被浪潮冲开了。此时,起锚开船的头一遍哨子吹响了,我很着急。船长在船上看见我们,下令延迟五分钟开船。大船旁边还有另一只小艇,是我朋友花了10卢比为我租的。这只小艇把我从那只超载的小艇上接过去。这时吊梯已经拉上去了,我只好拉住一条长索上去,轮船马上就起航了,其他乘客都被丢在后面。这时我才体会到船长的提醒是有道理的。
拉谟之后的第二个港口是蒙巴萨,然后是赞稷巴。
船在这里停泊的时间很长,达八九天之久,于是我们换了一条船赶路。
船长很喜欢我,可是这种喜欢的方式值得商榷。他邀请了我和一个英国朋友陪他上岸玩一玩,我们坐着他的小艇上了岸。我不知道“玩一玩”意味着什么,而船长也不知道我原是不懂此道的人。有一个掮客把我们带到某些黑人妇女的住处,每个人进一个房间。我站在房里,又羞又呆。只有天知道那不幸的女人是怎么看我的。她大概看出来我为人清白。起初我除了害怕外再也想不起其他事情,后来羞耻感终于消退了,谢谢神灵:我没有对那个女人动心。我讨厌自己的懦弱,并为自己没有拒绝走进房间的那种勇气而深感可悲。
这是我一生中第三次经历类似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本来清白的青年,恐怕就是因为这种错误的羞耻感而滑向了罪恶的深渊。我想如果我当时拒绝走进那个房间,我会更信任自己。感谢神灵,多亏他拯救了我。这件事坚定了我对神明的信仰,也在一定程度上教会我抛弃错误的羞耻感。
由于要停留在这个港口一个周,我干脆住到城里,成天四处蹓跶,增长了许多见闻。赞稷巴绿树成荫,印度只有马拉巴才能与之媲美,那些高大的树木和巨硕的果子使我感到惊奇。
过了赞稷巴便到了莫桑比克。5月底我们到达了纳塔耳。
三十二 若干经历
纳塔耳的港口是杜尔班,又叫做纳塔耳港。
阿布杜拉赛(Sheth)[“赛”是阿拉伯语,原意为宝剑,现为一种对穆斯林的尊称。
]来码头接我。当船靠码头时,我就观察那些上船来接朋友的人,发觉这里的印度人并不被人尊重。很容易就能看出来那些认识阿布杜拉赛的人都很藐视他,这使我很难受,阿布杜拉赛却已习以为常了。盯着我看的人似乎都对我很好奇。我的服装有别于其他印度人,穿着长过膝盖的大礼服,头上却戴着头巾,很像孟加拉人戴的“普格里”(Pugree)[大头巾。
]。
我被送到那家商行,安顿在阿布杜拉赛隔壁的一个单间里。我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他读着他弟弟托我转交给他的信,更不知如何是好。在他看来,他弟弟给他送来了一头很难伺候的白象。我的穿着打扮和生活作风看起来很像欧洲人,这让他颇为震惊。当时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工作可以给我做。他们的案子正在德兰士瓦进行,立即把我送到那里没有意义。那么他如何才能信任我的能力和人品呢?他不会到比勒托里亚去观察我办事,而被告都在比勒托里亚,他觉得被告很有可能对我施加不好的影响。如果不放心把有关这案子的工作交给我做,那还有什么工作可以交给我呢,因为别的职员都能干得好?职员们如果做错了事,还可以责备几句,要是我也做错了,那该如何是好?如此看来,要是不把与这个案子有关的工作交给我,那么,把我留下来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实际上,阿布杜拉赛没有什么文化,但有丰富的经验。他很能干,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这一点特长。因为经常在工作中用到,他掌握了足够日常对话用的一点点英文,已足够他与银行经理或欧洲商人来往时自如地处理一切事务,以及向他的法律顾问陈述案情。当地的印度人都非常尊敬他。他的商行是当时那里最大的印度商行,或者说是最大的其中之一。他有许多长处,但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天性多疑。
他非常看重伊斯兰教,而且热衷于谈论伊斯兰的宗教哲学。尽管不懂阿拉伯文,但却颇为精通《可兰经》和一般的伊斯兰教文学。他善于旁征博引,能信手拈来各种例子。在和他来往的过程中,我获得了不少关于伊斯兰教的实际知识。当我们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后,常常长时间地探讨有关宗教的问题。
我到了那儿后两三天,他便领我去杜尔班的法院,介绍我认识了几个人,还让我坐在他的法律代理人身旁。庭长一直看着我,后来还吩咐我摘下头巾。我拒绝了,离开了法庭。
我意识到,未来这里也有斗争在等候着我了。
阿布杜拉赛向我解释了在法庭上责令一部分印度人除下头巾的原因:那些身穿伊斯兰教服装的印度人可以戴着头巾,但是其他印度人便要照例除下头巾。
为使读者了解为何有这么一点多余的区别,我必须详细地作个说明。在这两三天之内,我已看出来这里的印度人分成了好几派。一派是穆斯林商人,自称为“阿拉伯人”。另一派是印度教徒。还有一派是波希人,都是当职员的。印度教徒职员,哪一派都不属,除非他们投身于“阿拉伯人”的那一派。波希职员则自称为波斯人。这三个阶层彼此都有些社会关系。但是为数最多阶层的还是由泰米尔、德鲁古以及北印度契约工人和自由工人构成的。契约工人是指那些签了契约到纳塔耳来工作五年的工人,他们又叫做“吉尔米提亚人”,这个称呼是英文“协议”一词的变音。
前面三个阶层和这个阶层之间只有生意上的往来。英国人把这些人叫“苦力”,而且由于大部分印度侨民属于这个阶层,于是所有印度人都被冠名为“苦力”或“沙弥”。“沙弥”是泰米尔文的后缀,放在很多泰米尔人的名字后面,其实与梵文的“史华密”是一个意思,即“主人”。如果有哪个印度人不愿意自己被称为“沙弥”,又有足够的胆识,他就会反唇相讥:“你可以叫我‘沙弥’,但你不要忘了‘沙弥’的意思是主人。我可不是你的主人啊!”有的英国人听了就算了,有些人却会生气,破口大骂印度人,甚至拳脚相加,对他而言,“沙弥”是污辱人的话,把它当做主人的意思,简直就是一种诬蔑!
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我被称为“苦力律师”,而做生意的人也就被称为“苦力商人”了。“苦力”这个字的原意就这样被淡忘了,成为所有印度人的普通称呼。穆斯林商人很讨厌这种称呼,他们声称“我不是苦力,我是阿拉伯人”,或声称“我是商人”,如果遇上的是一个比较客气的英国人,便会向他道歉。
在这样的形势下,戴不戴头巾的问题显得非常重要。一个印度人如果被迫脱下头巾,无异于忍受一场耻辱。我想干脆改戴英式的帽子得了,免得遭受这种耻辱,还可能引起不愉快的争论。
然而阿布杜拉赛却不赞成我的想法。他说:“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影响一定很恶劣。你将置坚持要戴印度头巾的人于何地?何况印度头巾很适合你。戴上英式的帽子,倒显得你像个餐厅的服务生了。”
他的话里夹杂着真知灼见,爱国思想和一点点褊狭的思想。其中的睿智显而易见,同时,如果不是出于爱国,他便不会坚持戴印度头巾;而那么轻蔑地提起服务生,正好反映了他褊狭的思想。印度契约工人包括了三个阶层的人: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最后一个阶层是皈依了基督教的印度契约工人的子女。在1893年,这个阶层的人就相当多了。他们穿英式服装,大多以在旅馆里当服务生为职业。阿布杜拉赛批评英式的帽子,实际上指的就是这些人的服装。在旅馆里当服务生,被公认为是不体面的事。直到现在,还是有很多人有这种想法。
我总体上是赞成阿布杜拉赛的话的。我向报馆投稿谈了这件事,坚决捍卫我在法庭里戴印度头巾的权利。戴头巾的问题在报纸上引发了争论,我则被媒体描写成一个“不受欢迎的造访者”。如此一来,我到南非不过几天,这件事便出乎意料地为我做了一回广告。有人支持我,也有人激烈地批评我的冒昧。
我旅居南非期间,几乎一直戴着印度头巾。至于在南非我何时和为何不戴头饰了,后面再谈吧。
三十三 赴比勒托里亚途中
不久我便接触到了住在杜尔班的信仰基督教的印度人。我认识了法院的翻译保罗先生,他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还认识了当时新教会倡办的学校的教员苏班·戈夫莱先生,他是1924年出访印度的南非代表团成员詹姆斯·戈夫莱先生的父亲,现在已经过世了。大概也在这个时候,我还结识了巴希·罗斯敦济(现已故)和阿丹吉·米耶汗(现已故),所有这些朋友,当时只是工作上的交往,与他们在其他方面并没有往来,后来才成为关系密切的朋友。关于他们的情况,后面还要谈到。
正当我不断扩大我的社交范围时,商行接到了他们的律师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要充分准备好打一场官司,建议阿布杜拉赛亲自去比勒托里亚一趟,或是派一个代表去。
阿布杜拉赛给我看了这封信,问我愿不愿意去比勒托里亚。我说:“只有从你那里了解清楚这个案子的情况以后,我才有应对的办法。现在我都不知道到那里去我要做什么。”他叫来几个职员向我说明了整个案情。
我开始研究这个案子,感到我需要从头学起这里面涉及的问题。逗留在赞稷巴的那几天,我曾去法庭见识过那里的工作情况。见到一个波希律师盘问一个证人,问他不少关于账本所涉及的借贷问题,我一点也听不懂。无论在中学读书还是在英国留学时,都没有学过簿记。而我到南非来处理的这个案子,主要和账目有关。只有懂账目的人才能理解和解释其中的问题。那个给我讲案情的职员滔滔不绝地说着借方、贷方的内容,我却越听越糊涂。我不懂P.Note的意思,在字典里也查不到,只好请教那个职员,才知道P.Note原来指的是期票。我买了一本有关簿记的书,认真加以研究。这倒使我增强了一些信心。我终于弄清楚了案情。阿布杜拉赛其实也不会记账,可是他有很多实践经验,能够很快地解决簿记中的复杂问题。我告诉他们,我已做好去比勒托里亚的准备了。
“你打算在哪里住?”他问道。
“随便你安排。”我说道。
“那么我就写信给我们那边的律师,他会替你安排住处。我还可以给那边的弥曼朋友写几封信,不过我希望你尽量不要和他们一起住。我们的对手在当地有很大的势力,如果他们中有人设法看到了我们的来往信函,会对我们十分不利。你越是避免和他们来往,对我们就越有利。”
“你的律师叫我在哪里住,我就在哪里住,不然我就自己找个单独的住处,请放心吧。没人会知道我们的秘密。但是我倒是很想认识我们的对手,和他们交朋友。如果可能的话,我还想试试达成庭外和解。毕竟铁布赛是你的亲戚。”
铁布·哈齐汗·穆罕默德赛是阿布杜拉赛的近亲。
我提到的有可能解决这个案子的方法,多少令阿布杜拉赛感到意外。然而我到杜尔班已经六七天了,我们对彼此已经有些了解,我不再是所谓的“白象”了。
他说:“那好吧。能够庭外和解再好不过。我们都是亲戚,彼此都清楚对方的脾气,铁布赛不是一个轻易答应和解的人。只要我们稍一疏忽,他就会想尽办法钻我们的空子,一整到底。所以你做任何事情都要三思而后行。”
“关于这一点,请不必担心。”我说,“我无须和铁布赛说什么,也不必和其他任何人谈起这个案子。我只是建议他同我们达成庭外和解的共识,避免一场不必要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