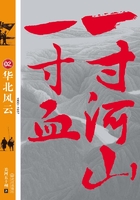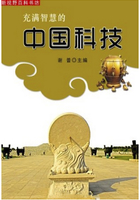然而,孟买还有一个以前留下来的案子待我处理,那是一个尚待起草的“状子”。一个贫苦的穆斯林在波尔班达的土地被没收了,他怀着像儿子对父亲一般的崇敬心情找到我。这案子看来没有赢的指望,但我还是答应帮他写一份状子,印刷费由他负担。我写好后,念给朋友听,大家都很赞许,这增强了我的信心,以为自己至少有足够的能力写状子,而事实也是这样。
如果我能靠免费为人写状子使我的业务兴盛起来也好,然而依旧无济于事。因此我打算找个老师的兼职来做。我的英文还算好,也很愿意到大学里去教刚入学的新生。这样我至少赚点钱弥补一部分花销。那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招聘英文老师,每日授课一小时,月薪75卢比”,是一所有名的中学刊登的。我递交了申请,并应约去面试,我兴高采烈地去面试,校长发现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他便抱歉地回绝了我。
“可是我是在伦敦大学通过考试的,还选修了拉丁文作为我的第二外语。”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只要大学毕业生。”
我无计可施,绝望地搓着双手。哥哥也很替我操心。我们盘算了一下:在孟买住下去也没有意义了,应当回拉奇科特,我哥哥自己也是一个小讼师,他可以给我介绍一些起草呈文和代写状子一类的工作,何况家在拉奇科特,不在孟买单过就可以节省下来很多钱。在孟买待了六个月之后,我在那儿的小家就没了。
在孟买时,我天天都去高等法院,不过在那里没有学到什么东西,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常常会因为听不懂案情而在那儿打瞌睡。里面还有不少人跟我一样,这大大减轻了我的负疚感。之后我连羞愧的心情都没有了,我发现在高等法院里打瞌睡已成为一种时髦。
如果现在的这一代里,还有人像我当年那样,在孟买当个没有收入的律师,我要给他们介绍一些有关当时生活的实际情况的概念。尽管当时我住在吉尔关,但几乎从没坐过马车或电车。我习惯徒步四十五分钟走到高等法院,当然我也是步行回家,我已习惯了被太阳晒。这样来回步行,确实节省了好多钱,当时,我在孟买的朋友们常常会生病,而我却不记得我生过病。即使到我开始赚钱时,还保持着徒步上下班的习惯,也一直受益于这种习惯。
二十九 头一次打击
怀着失望之情,我离开孟买回到了拉奇科特,建立起我自己的事务所。我在这里的收入倒还可以。给人写写呈文状子,平均每月大约有300卢比的收入。得到这样的工作机会与其说是靠我自己的本事,倒不如说是得利于朋友的帮助,哥哥的合伙人在这里已经打下了一个颇为牢固的工作基础。所有真正重要的,或他认为重要的诉状,全都被送到大律师那里去。而送到我这里来代理的,都是那些贫苦的当事人的呈文。
在这里我必须得承认,我在孟买认真坚持的不给回扣的原则向现实妥协了。在孟买,回扣是给中间人的,而在这里却是付给合办案子的讼师的;而且和孟买的情形相同,所有的律师都无一例外地以回扣的形式来支付一定的佣金。哥哥的理论令我无法辩驳。“你要知道,我是在和另一个讼师合伙做事。我们到手的案子,只要是你能受理的,我都设法分给你去办,如果你拒绝给我的伙伴回扣,我一定会为难。假设是你和我合伙开事务所,你的收入就等于我们共同的收入,我自然也要从中分到一份。再说我的合伙人,如果他把同一个案件转给别人去做,他一定也可以从别人那里得到一笔回扣。”我同意了哥哥的说法,觉得如果自己要做律师,就不应当在给回扣的问题上固执己见。我就说服了自己,换句话说,是这样来欺骗自己的。但我应当补充一句:在其他来源的案子上,我没给人拿过回扣。
那时我的收入已勉强可以维持生活,也是在这个时候,我遭受了平生第一次打击。以前就听说过英国官员如何如何,却一直没有机会面对面地遇见过。
在纳萨希布王公(现已故)即位之前,我哥哥曾经给他当过一阵子秘书和顾问。这时有人跑来控告我哥哥在职时提过错误的建议,而且还把这件事捅到一向对我哥哥心怀成见的英国政治监督官那里去。我在英国时就认识这个官员了,他对我还是相当客气的。哥哥想让我借着这一点交情去替他说几句好话,以消除那位官员的成见。我很不赞同他的这个想法,我不愿意利用在英国时那点很浅薄的交情来说事儿。假使我哥哥真的有过失,我去说情又能怎样?如果他没有犯错,应当通过正当的程序递交呈文,说明真相,静候结果。我哥哥不赞同我的意见。他说:“你不了解卡提亚华,更不了解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什么都靠人情。你是我的弟弟,去向你认识的官员替哥哥说情,是你的责任,你不应当逃避这个责任。”
我无法推诿,违心地去见了这位官员。我知道自己没有权利去找他,也知道这样做十分有损我的自尊心。但我还是求见了,预约了并获得批准。当我提起往日的交情时,立刻发现了卡提亚华和在英国的情形不同;同一个官员,在职时和休假时简直判若两人。监督官承认我们相识,但提到那些交情只是使他态度更加强硬。“你绝不是到这里套近乎,来滥用交情吧?”他语气生硬,眉宇之间也透露出这种态度。尽管如此,我还是说明了来意。这位老爷不耐烦了,“你哥哥是一个阴险的人,我不愿意再听你说下去了。我没有时间,如果你哥哥有什么要解释的,请他通过正当的途径提出来。”这种回答已经令人不堪了,其实也是我应得的。但是自私令人盲目,我继续往下说。这位老爷干脆逐客:“你现在该走了。”
“但是请您听我把话说完。”我这样说使他更生气。他吩咐听差把送我出去,就在我还在迟疑时,差役进来两手一架,把我推出了房门。
然后那位老爷和差役都走了,我也恼羞成怒地离开了。马上写了个条子让人传给他,大意是说:“你侮辱了我。还让你的差役粗暴地对待我。如果你不道歉,我就要告你。”
监督官马上让他的随从送来答复:“是你先对我不敬,我请你离开,你又不走。我别无他法,只好命令差役送你出去。他来之后叫你离开,但你还是不肯走。所以他不得不把你弄出去。你要怎样,悉听尊便。”
我揣这封回信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把事情从头到尾地告诉了我的哥哥。他很难过,但也不知道如何安慰我。因为我不知道怎样控告这位官员,他便把这情形告诉了他当讼师的朋友。碰巧费罗泽夏·梅赫达爵士为了处理一个案子,从孟买来到了拉奇科特。但是像我这样一个小律师,怎么敢去见他呢?于是便通过聘请他的那位讼师把关于此案的文件转托给他,请他指教。他回话说:“告诉甘地,这是许多讼师和律师都会遇到的事。他才从英国回来,年轻气盛,还不了解英国那些官员们。如果他打算在这里平平安安过日子,就把那封信撕掉,忍下这个侮辱吧。控告那位老爷对他不会有什么好处的,反而会毁了他。告诉他,他还不懂人情世故呢。”
这个忠告对于我无异于苦涩的毒药,但我不得不吞下去。我忍下了这个耻辱,也因此而获益。我告诉自己:“绝不再陷入这样错误的境地,绝不再这样滥用友谊。”从此以后,我再没有打破这个誓言。这次的打击也使我的生活历程发生了改变。
三十 准备赴南非
去找那位官员无疑是个错误。但与我的错误相比,他盛气凌人的态度未免也太过分了。他没有必要驱逐我,我最多占用他五分钟的时间,只是他完全不想听我说的话,其实他大可以客气地请我走,可权力已把他迷醉到了一种不可理喻的地步。后来我听说,这位英国官员完全不具备忍耐的美德,经常侮辱来访者,只要他稍感不如意,就会暴跳如雷。
当时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在他主持的法庭里开展,我不会同他和解,因为不愿意拍他的马屁。况且,既然我说过要控告他,就不甘这样沉默。
我开始在这个时候对小地方上的官场政治有了一定的了解。卡提亚华是由诸多小邦组成的,自然是免不了钩心斗角之争了。各邦之间、官吏之间的争权夺利是家常便饭。王公们都听信身边那些阿谀奉承的人。像上次那位官员的听差,要被小心伺候着,而那位官员的文书作为他主子的耳目和翻译,则比他的主子还厉害。这位文书的话就是法律,他的收入比他的主子多,也许有点夸张,不过他的确不是靠拿薪水过生活的。
对我而言,这种气氛毒害身心,怎样才能不被沾染倒成了困扰我的难题了。
我深感苦恼,哥哥也察觉到了。我们都觉得,要是我能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就有机会离开这个钩心斗角的地方。因为如果不耍一点手段,想当上部长或法官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且我和那位官员发生了冲突,要在本地继续执业是困难重重。
当时,波尔班达已属英国人管辖,我在那里还有一点工作可以做,就是替当地的王公争取更多的权利。为了解决佃农负担的地租过重的问题,我还得去见当地的一个行政官。尽管这位官员是个印度人,气焰比上次那个英国官员还嚣张。他很能干,可是当地的农民并没有因此得益。我或多或少给王公争得了一些权益,但佃农的负担并没有减轻,而佃农们的苦难这样被漠视,这实在令我大为震惊。
我的工作令我相当失望。法官对我的当事人并不公道,可我又无法主持公道,顶多只能向政治监督官或省督提出上诉,但他们会以一句“我们不便干涉”便把我的上诉驳回。如果有什么规章条文可以管制他们的做法,我还有办法,可是在这里,官员的话就是法律。
我无限愤慨。
这时,波尔班达的一家弥曼(Moman)[伊斯兰教中的一派。
]商行给我哥哥写信,提出邀请:“我们是一家大商行,在南非有生意,正在那里打官司,涉及到40000英镑。这个案子已经拖了很久了。我们聘请了最好的讼师和律师来帮助我们。如果你能让你弟弟过来协助我们,对我们彼此都有好处,他能够恰当地指导我们的顾问,也可以借这个机会见见世面,结交新朋友。”
哥哥跟我商量这件事。我没搞清到那里只是从旁协助顾问,还是亲自出庭,但我愿意试试。
哥哥介绍给我去见赛·阿布杜尔·卡利姆·嘉维立,他是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股东,最近才去世的。这家公司就是信上所说的商行。他向我保证:“这不是一件难事。我们有很多欧洲朋友,你到了那里就有机会认识他们。你的到来对我们铺子上的生意很有帮助。我们的大部分往来信件是用英文的,在这方面也需要你帮忙。到那里后当然你是客人,不会承担任何费用。”
“需要多长时间?报酬是多少?”我问道。
“不超过一年。我们负担你坐轮船头等舱的来回船票,另外付给你105英镑。”
这待遇不像是给律师的,倒像是给商店雇员的。但当时我真的很想离开印度,这是一个不该错过的好机会,可以去新的国家体验新的经历,而且那105英镑的收入可以寄给哥哥补贴家用。于是我欣然接受了这个邀请,准备赴南非。
三十一 抵达纳塔耳
这回去南非,并没有当年赴英国时所经历的那种离别之苦。母亲已经去世了,心中少了一份牵挂,现在我多少已懂得了一些人情世故,并且已经有了旅居海外的生活经验,而且从拉奇科特到孟买的来回奔波更是家常便饭了。
这一次我只是舍不得妻子,因为要离开她而难过。从英国回来后,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出世了。这时我们的爱虽然还没有彻底摆脱肉欲,但已经越来越纯洁了。回国后我很少和妻子住在一起,而且还当起了她的老师,尽管她不怎么关心,我还是帮助她作了某些改革,我们都觉得,要继续进行这些改革,需要有更多的时间相处,然而去南非的吸引力超过了别离的痛苦。我安慰她:“不到一年我们就能相聚了”,然后便离开了拉奇科特去孟买了。
到孟买后,我需要通过达达·阿布杜拉公司的代理人来购买船票,但舱位已经卖光了,而且如果不坐这一趟的话,我就得滞留在孟买。代理人对我说:“我们已想方设法去买头等舱船票了,可是怎么也弄不到。若你坐统舱,仍然可以被安排在餐厅就餐。”那时,我出门都乘头等车坐头等船,而且身为一名律师,怎么可以乘统舱?我拒绝了他的建议,还怀疑是他们故弄玄虚,我不相信他们买不到一张头等舱船票。得到代理人同意后,我设法自己去买船票。我直接登上轮船,找到了船上的大副。他坦白地告诉我:“平常并不是这么挤,因为这一趟的乘客中有莫桑比克的总督,所以所有的舱位都被订走了。”
“能不能给我腾个地方?”他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笑着说:“还有一个办法:我的房间有一个床位,通常是不卖给乘客的,不过我打算给你。”我连忙道谢,通知代理人去买那张票。1893年4月,我满怀着期待,动身赴南非去碰碰我的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