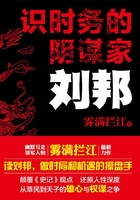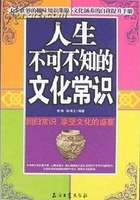虽然我对印度教以及世界上其他宗教都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我清楚当我经受着考验时,这一点点知识还远不能使我得到拯救。究竟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一个人经受考验,他是不会先有所感的。没有信仰的人,一定会将自己获救的事归功于机遇。而有信仰的人,会说这是神明拯救了他,是他自身的宗教修养或他的精神信条发生作用的结果。然而在他获救时,他并不清楚究竟是他精神信条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拯救了他。那些深信精神力量的人,不是也看见过精神也会被世俗折服吗?在经受考验时,所谓的宗教知识与得自经验的知识是不同的,它不过是戏言罢了。第一次发现靠宗教知识是无济于事的,是留学英国时。当时我太年轻,也说不上来是如何从以前经历的几次遭遇中得救的。但现在我已经二十岁了,已经有了做丈夫和父亲的经验了。
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最后一年,也就是1890年,我和一位印度朋友应邀去参加在朴次茅斯举办的一次素食者会议。朴次茅斯是一个海港,驻扎着很多海军人员。那里的公寓住着许多名声不好的妇女,她们并不是真正的妓女,但是品行不端。我们就被安排住在其中的一个公寓。老实说,会议的组织者也不知道这里的情况。要在朴次茅斯这样的城市里区分住所的好坏,对于我们这种偶然来到的旅客是十分困难的。
我们开完会后,晚上回到寓所,吃完晚饭后大家一起坐下来玩桥牌,女房东也参加了,这是英国的一种规矩,哪怕是上等人家也是如此。每个玩牌的人一般要讲一些无伤大雅的话,可是我的朋友和女房东越说越不像样。我以前没看出来我的这位朋友是精于此道的人。我被吸引了,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他们的谈话。正当我打算越出界限,放下手中的牌然后去做坏事时,我的这位朋友向我发出了警告:“你哪儿来的这种坏念头啊,我的孩子?离开吧,快!”
惭愧顿时涌上心头,我接受了警告,向朋友表示了衷心的感谢。想起在母亲面前立下的誓言,我立即从现场狼狈地、颤抖地、心慌意乱地逃回自己的房间,像一只猎物从猎人手心逃脱一样。
这是我印象中除了妻子以外第一次对异性触动了情欲。那一夜我辗转难以成眠,各种念头在脑中盘桓。我是否该离开这屋子?我是否该逃离这个地方?我现在在哪儿!如果我失去了理智,会发生什么?我决定今后要小心行事:不但离开这个公寓,而且要离开朴次茅斯。这次会议两天就开完了,第二天晚上我便离开了朴次茅斯,我的朋友在那里多住了几天。
我那时还不了解宗教或神明的实质是什么,也不知道他们如何对我产生作用,我只是模糊地觉得那一次是神明拯救了我。我经历考验的所有时刻,都是从神明那里获得拯救的。如今我才了解“神灵拯救我”这句话更深刻的含义,但我并不能完全明白它的意义。只有更多的经验才能帮助我作更透彻的理解。但就我所经受的一切精神性的考验而言,我敢保证,无论是身为一个律师,还是管理公共事务、从事政治活动,都是神明在庇护着我。当一切希望都趋于幻灭时,即“孤立无援而全无安慰时”,神会在我不确知的某刻出现,给我帮助。不能将祈愿、膜拜、祷告算作迷信,它们是比饮食住行更为真实的行为。即使说只有它们才是真实的而其他一切都不真实也不为过。
这种膜拜或祷告不是长篇大论,也不是说说而已。它发自内心深处。所以,当我们的心灵达到“除了爱以外别无杂念”的境界时,我们会感觉到“无法用眼睛看到的天籁之音”穿透心灵。祷告是静默的。它本身是独立于任何外物的精神上的修为。我完全相信通过祷告是可以清心绝欲的,但要做到这一点,还是必须对神灵怀着谦逊的心。
二十二 纳拉扬·亨昌德罗
纳拉扬·亨昌德罗这个时候到英国来了。早就听说他是作家,我们也在印度国民大会的曼宁小姐家中见过面。曼宁小姐知道我不善于交际,每次去她那儿我总是默默地坐在一边,除了回答别人的问话外,自己从不吭声。于是她把我介绍给纳拉扬·亨昌德罗。他不懂英文,那天穿的衣服也很古怪——一条粗陋的裤子,一件皱巴巴的肮脏的波希人(Parsi)[波希人大多聚居于孟买,他们是8—10世纪间移民印度,坚持信仰琐罗亚斯德教而不愿改信伊斯兰教的波斯人的后裔。
]常穿的褐色外衣,既没打领带,也没有打领结,还戴着一顶有穗子垂下来的绒帽,留了一颔长须。
他个子不高,体格瘦小,圆圆的脸上布满了出天花后的留下来的斑点,鼻子既不挺也不扁。老是用手抚摸自己的胡须。
这样一个样貌奇特、穿着奇装异服的人,在这个时髦的社会里自然特别醒目。
我对纳拉扬·亨昌德罗说:“久仰大名,读过您的一些作品,如果您愿意光临寒舍,我将深感荣幸。”
纳拉扬·亨昌德罗声音沙哑,面带笑容地回答我说:“当然可以,你住在哪儿?”
“斯多尔大街。”
“那我们是邻居呢。我想学英文,你可以教我吗?”
“只要我知道的,我都愿意教您,我会尽力效劳。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到您那儿去。”
“那怎么好意思?还是我去你那儿吧。我还要带翻译练习本去。”我们就这样约好了,不久之后便成为好朋友了。
纳拉扬·亨昌德罗对于英文文法一无所知,他认为“马”是动词,而“跑”是名词。我记得诸如此类的笑话还很多。可是他丝毫没有为自己的无知而气馁。我的文法知识也有限,不能帮他学通。但说真的,他从不以自己不懂文法为耻。
他全然漫不经心地说:“我从来不觉得在表达思想时需要什么文法。你懂孟加拉文吗?我懂,我在孟加拉旅行过。就是我把玛哈希·德文特罗纳斯·泰戈尔(Maharshi Devendranath Tagore)[哲学家、社会活动家。是印度现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1861—1941)的父亲。
]的作品转译成古遮拉特文的。我还希望把其他外文著作都译成古遮拉特文。你知道我很满意于我的译文可以表达出来原文的精神。别的人可能知识更丰富,将来可能做得更好,但是如今,不懂文法的我所能做到的也很令人满意。我懂马拉底文、印度文、孟加拉文,现在又开始学英文。我所缺的不过是丰富的词汇,你以为我的抱负仅止于此吗?别担心,我还要去法国学法文。我说过,语言是更广博的文学。可能的话,我还想去德国学德文呢。”就这样,他会说个没完,对于学外文和到外国旅行充满着无穷的兴趣。
“然后,你还要到美国去吗?”
“当然。不去见识一下那个新大陆,我怎么能够返回印度呢?”
“可是你要上哪儿去弄钱?”
“我要钱干什么?我又不像你那么时髦,我只求有吃有穿就行了。维持这种生活需求只要靠我写书和朋友们的接济就够了。我旅行时总是坐三等车的。即便去美国,也一样搭统舱。”
纳拉扬·亨昌德罗的简朴是十分自然的,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率直的人。他一点也不骄傲,只不过对于自己写作的才能过分在意了些。
我们天天见面,思想和行动常常不谋而合。我们都是素食者,又常在一起吃午饭。那段时间我正过着自己做饭,每周只花17先令的日子。有时我去他那儿,有时他到我这儿。
我煮的饭大多是英式的,他却是除了印度菜之外,一律都不爱吃。他顿顿不能没有黄豆汤(Dal)[印度特产,印度人日常吃饭必备的黄豆汤,豆粒很小。
],我做的却是胡萝卜汤,而他始终不认同我的口味。有一次他弄到了一点地道的蒙豆(Mung)[印度豆类,颇似扁豆。
],煮好了带到我这里来一起吃,我吃得很爽。此后,我们之间经常交换食物,有时我把好吃的东西送到他那儿,有时他带美食给我。
当时,曼宁主教名声大振。由于约翰·伯恩斯和曼宁主教从中斡旋,码头工人的罢工才得以提早结束。我告诉纳拉扬·亨昌德罗,狄斯荣立十分赞赏曼宁主教的简朴。于是他说:“那么我一定要见见这位圣人。”
“他是大人物,你怎样才能见到他呢?”
“怎么会见不着?我自有办法。我必须请你以我的名义写封信给他,告诉他我是作家,想以个人的名义当面祝贺他对人道主义的贡献,再告诉他我不懂英文,所以带你同去,你当翻译。”
我照他的意思写了一封信。两三天后,曼宁主教真的回信约见我们了。于是我们一同去拜访这位主教。我穿上平日会客的正装,纳拉扬·亨昌德罗依然故我,还是从前那副邋遢打扮。我对他开起了玩笑,可是他却大笑起来:“你们这些文明人都放不开,其实大人物从来不关心一个人的外表,他们注重的是一个人的内心。”
我们进了曼宁主教住处的大厅。刚一坐下,便看见这位瘦瘦高高的老绅士走出来同我们握手。纳拉扬·亨昌德罗表达了他的问候:“我不想占用您太多的时间。久仰您的大名,特地来当面感谢您为罢工工人所做的善事。拜会世界名人是我的习惯,所以今天冒昧地打扰您了。”
这自然是我帮纳拉扬·亨昌德罗做的翻译,他讲的是古遮拉特话。
“很高兴你们能来看我,希望你们在伦敦称心如意,也希望你们能和这里的人多来往。愿上帝保佑你们。”
说完这几句话,主教便起身和我们告别。
还有一次,纳拉扬·亨昌德罗穿着一件内衣,裹着一条“拖蒂”(Dhti)[一般印度男性的传统服装,就是一块宽长的白布缠在身上当裤子用。
]到我这里来。
我那位好心的女房东开门后,便慌张地跑过来找我。这是一位新来的房东,她不认识纳拉扬·亨昌德罗,于是对我说:“外面有一个疯子要见你。”我连忙跑到门口,没想到就是纳拉扬·亨昌德罗,我吃了一惊。他却一如平常,脸上充满笑意。
“难道街上的小孩子没有追你吗?”
“是的,他们追着我跑。可是我不理会,他们也就不闹了。”
在伦敦住了几个月后,纳拉扬·亨昌德罗便到巴黎去了。他果然开始学起法文来,而且还翻译了法文书籍。我的法文程度倒是足够帮他校对译文了,所以他就常常将稿子寄给我看。严格地说,他那不算是翻译,只是写下了大意罢了。
纳拉扬·亨昌德罗最后果然实现了他访问美国的愿望。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弄到一张统舱船票。到美国以后,他有一次因为穿那件内衣和“拖蒂”上街,竟以“奇装异服”的罪名被起诉。
我记得他最后被判无罪开释。
二十三 大博览会
1890年巴黎举办过一场大博览会。我早就听说了关于这场博览会详细的筹备情况,也怀有热望想去看看巴黎。因此我觉得这时候去巴黎真是一举两得。这场博览会最吸引人的是一座高1000英尺左右、完全用钢铁铸成的埃菲尔塔。当然博览会上还展示了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无疑这座铁塔是最突出的,因为那时人们还认为这么高的建筑物是很难安然屹立于地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