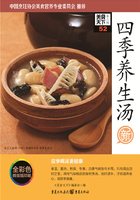鼻息间就涌入浓烈的血腥味。
“公主?司徒绝?”随着脚步声跑近,紧接着是小饼惊慌的咆哮出口:“血?公主?你受伤没有?”
他迅速伸手想把司徒绝拉开,怎奈后者双臂捆得死紧,无论小饼如何用力也拉不开。
受伤?想到方才危险的一幕,血?血腥?大脑一阵天旋地转,我用力想要挣脱他的禁锢,可是怎么也挣不开来,只能轻轻伸出双手环住他的背,顿时,所触之处掌心温湿。
“司徒绝?是你?大叔……大叔……”
溢出口的呼唤是多么颤抖又充斥着惊慌失措,司徒绝背上都是血,是替我流的,他现在昏迷不醒,不知道死了没有?他是个利用我的坏蛋,到死了也要我带着愧疚。
我吓得嚎嚎大哭,似乎还带着另一层无法形容的伤心。
“喂……我没……死……笨蛋……”
清得几乎听不见的男声流入耳畔,我确定没有听错,立刻嘘声。怔怔看着近在鼻尖前的面容,苍白,俊美,还带着强行挤出的,吃力的微笑,可是怎么看怎么心酸。
他没死?睁开了漂亮的眼睛,幽幽发亮的眸子,美得如同黑耀石一般璀燦,映出我泪汪汪,甚至还挂着鼻涕的脸。
“小绝?”
他嘿嘿一笑,冷汗从额际滚了下来,银牙咬了咬:“我早就想跟你说一句老实话。你,真丑。”话音落,两眼一闭,晕了过去,重重压在我身上。
“喂喂,司徒绝,司徒绝……”我哭着又喊又叫,尽管有小饼帮忙,可这货不知是吃什么长得,重的跟头牛似的,怎么也拉不起来。
这时大叔走了过来,顺手轻轻一拎就将他扛上肩,两指在脉膊处拈了拈:“死不了。”随后飞也似的消失在我们眼前。
小饼匆匆跑过来,拿出帕子给我擦鼻涕:“吓死我了,你没伤着吧?我看看,手没事,脚没事,腿也没事。呃?脑子呢……矮油!一定摔坏了,竟然为那个卑鄙小人哭?”
“你脑子才坏了呢。”没好气抢过帕子砸上他那张大饼脸。老娘气极败坏追着大叔跑去。不管怎么说,那家伙都是因为我才受伤,于情于理置人家不闻不问都说不过去。
待我气喘吁吁赶回小屋里时,大叔已经在为司徒绝的伤口上药,他的衣服被扒光了,露出精壮精壮的身体,虽然只有背部,几道极深的痕迹已呈黑紫色烙在肌肉上,血已经止住,但伤口深可见骨,单是看着我双腿就禁不住打颤。话说就是上次偷看才知道这
“他的伤要紧吗?”掩不住内心疼的,紧张坐在一旁,我的口气里掩不住焦急,若不是生怕打扰到大叔捣药,我已经两手扯上他的嘴巴非逼他点头说“小伤,没事儿”。
身旁小饼气鼓鼓也坐了下来,凉凉开口道:“不是说‘死不了’了吗?残不残就得看造化了。”
他在一旁把弄着草药,不停的看向大叔,嘴里咕噜:“高手就是高手,看不见还能摸得这么准。”
“你能不说话吗?”没好气横去一眼,我强忍住悲痛与不耐烦迸出几个字,再看向一直捣药的大叔时,心又提了起来:“会残吗?”
“不会!”答得干脆。我不由心里一松,刚要松口气:“最差也就是醒不过来。”
“那还不是一样?”惨叫起来,大叔的意思是说司徒绝可能就这么睡到死为止。你老母的,还不如残呢。
“喂喂,那么担心他干嘛,别忘了他利用司徒绝的身份接近你,欺骗你欺骗我,还逼你嫁给他的事啦?”胳膀被小饼猛然撞撞,稍一用力,就似千斤重力压下,勒得我喘不过气来。
对面小饼神情凝重,认真。
我也不知该怎么解释,只要一想到他奋不顾身为我拦了那致命的危机,原本愤愤不平的怒火瞬间化为灰烬。
就连那些明骗暗逼,我也懒得花心思去计较了。
沉默在我们之间漫延开来,不大的小屋内唯有大叔捣着草药的声音,不多会儿,当他把最后一小把药汁抹上伤口后,才说:“这个年轻人就是第二个骗你的?”
“是,嗯?不,算是吧。”到现在为止我也无法肯定了,“欺骗”与“救命”哪边天秤重些?谁都会选择后者罢!
“还恨他?”听得出话里的调侃,大叔将剩下的药草硬塞进我手里:“草药每天捣一回,换一次。若是恨他,就不用管了,不出三天,这家伙一定气绝身亡,也不会脏了你的手。”
这算什么?间接杀人?
我飞快的把他们推开,可惜大叔不接,我只能放到地上,带着哭腔:“我,我,我,我不杀人。”
“这又不算杀,你若真怕的话就离远些,三四天后再回来。”慌乱的我看不到勾在大叔嘴角那抹揶揄的笑意。
对,曾经为了活命,我确实举起过屠刀,但对方同我亦确实有血海深仇。
可是眼下情况又不同,司徒绝并没有真正从实质上害过我,除却欺骗以外,很多时候他都是挺身而出,为我解决一个接一个惹下的麻烦。
急得抹了一把又一把泪,生怕真看到司徒绝紧闭的眼与毫无血色的唇,抱紧满心的害怕转过身体:“我不,那跟亲手杀人有什么区别,他也算我的救命恩人啦,我,我……”
见状,大叔拍拍我的背,温柔的气息似我慈详的父皇,安慰着我:“丫头,生死忧关之际做出的反应也许不是最正确的,但却是最诚实的。”
“大叔?”睁大眼睛,脑海里有什么东西刹那间翻滚沸腾,仿佛眼前一条死路突然绽放光明,结郁多日的心结茅塞顿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