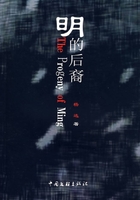“嗯,不错。”他点点头,听得似乎很认真,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又千方万计把我找回家,告诉我,诺大家业与我共享。我当然不会再傻得相信了,于是逃了出来。如果是您的话,您会信吗?”
大叔认真沉思了一会儿:“得看清情况,用心去看。人的嘴巴会说谎,但是心却不会。若看不到心,就看眼睛。”
“你说得太难了,我也一直看着他们的眼睛,可是除了一对眼珠子什么都看不到。所以不久前又被第二个男人骗了。他易容成我曾经的好朋友接近我,为的也是我家的产业。”该死的司徒绝,哦不,不是司徒绝,老娘连那货的真名真姓是什么都还不晓得,别辱没了小绝英勇的灵魂。
说到痛恨处,我忍不住拍腿愤慨:“你说这世上的男人怎么一个比一个贱。都说女人虚伪,风尘女子无情,见钱眼看。叫老娘看这些男人更不是东西,睁着眼睛把女人骗得团团转,达到目的后过河拆桥,想杀就杀,想剐就剐,连尸体都不留直接丢了喂狗。”
我不是为姬芷如抱屈,只是为同是被夜离歌这个贱男所骗而表示一丁点同情的哀悼罢了。
我差点都忘了身旁就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不过他似乎没有被我激烈的言辞打击到,却是轻描淡写应了几句:“你把家产全部扔干净,就会遇得到好人了。”
“问题是连我自已也不知道那笔钱藏在哪里,可是他们偏不信反而越搓越勇,满中原追着跑。可怜我就跟逃犯似的。”也差不多了,夜离歌的暗卫半数出动,个个手里持有我的画像,就差强贴皇榜满天下捉人了。
我曾想过把玉佩丢了一了百了,可毕竟是父皇留给我唯一的东西,丢了实在大逆不道,只好留下,可毕竟是个烫手货,揣哪儿都不安稳。
“天下大多数人皆是念心不足,一辈子你争我夺,最后还不是归于黄土。”悲凉的叹息,仰头用那看不见的眼眶盯着头顶上方漆黑的天幕。我觉得大叔的背后一定有更加伤感的过去。
我是睡在大叔的屋里的,他估计考虑到我是女孩子,所以没有进屋。
大半夜被尿憋醒了,实在忍不住便跑出去找了个地方解决,当然步子踉跄往回走时,无意瞅见屋后的山包上,大叔独自迎风而立,微仰首,不知想些什么。
我一溜小跑上去:“你不困吗?”
他跟没听见似的,不理不睬。讨了个没趣,我又禁不住寒冷,自个儿回去睡大觉了。第二天,第三天……亦如。他似乎有想不完的心事,却不肯说出来。
直到第十天白天,我突发奇想打算为他收拾屋子,狸狸从床塌里边叨出个东西来,摇着尾巴讨巧,我顺手接过仔细一看,不过是把普通的玉钗子,便随手打算放到一边,不想手一滑,玉钗子生生从掌缝中坠落,摔到地上“啪!”断成三截。
“啊?”我傻眼了,这是别人的东西。
然而滚滚旋风而过,大叔不知何浑身笼罩寒意奔进来,大手把我推至一边,我的身体重重撞在墙上,疼得我差点掉眼泪。
而大他则急迫的在地上摸索起来。很快,他颤抖的十指触碰到破碎的玉片,仿佛被针扎到似的僵滞如石。
无形的悲凉在沉默中漫涎开来,一滴,两滴……愈来愈多的泪流了出来。
“对……对不……起……”我懊恼的站在角落里不敢上前,不敢去看他泪流的,空洞的眼眶。
“那个,我帮你拣起来吧。”刚一上前,却被他一记掌风打开:“滚……”
暴怒的嘶吼撕扯着我耳膜,他吼过之后,双手小心翼翼的把碎玉一点一点拣起来捂在掌心里,怜惜的贴在心口,然后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我跑到门口,看着他散发着绝望的背影,鼻子一酸,眼泪流了下来。
我不是故意的,真的。狸狸慢慢爬到我腿上叽叽低唤着,我抱起它忍不住哭了出来。
我太没用了,以前摔坏腰佩,现在弄坏大叔的钗子,是不是我天生八字不好,碰到谁就克谁?
大叔当夜没有回来,我静静等到第二天早晨,可是一连几天,他就跟消失了似的不见踪影。这天早晨,居然来了一个打死我都想不到的人。
当门被推开的那一刹那,刺眼的阳光钻进来照在我脸上,吵醒了我的美梦。我伸了个懒腰瞅见门口逆光而立的人影,当下以为大叔回来了,立刻蹦下床大叫:“大叔你终于回来了。”
“公主?”门口的人影身形一晃,脱口而出。
仿佛当头浇下一桶冷水,这声音极为耳熟,可是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而且,他不是大叔!
我揉揉眼睛打量,惊讶不逊于他:“小饼?怎么会是你?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大叔呢?”
“这该我问你吧?公主您是怎么跑到这里的?”他打量了一下:“这可是悬崖底呀!”
“什么”崖底“?我是被黄河发大水冲到这儿的?”边说边挥手比划着“发大水”的架势,待到话匣子一开,我立刻揪起他领子:“你呢?什么话也不说就走,生意重要是吧?你算哪门子的世交?亏得我为了给你牵线脸都丢尽了。”
“等等等等。我没有不辞而别。你冤枉我了,哦……我知道了,一定是司徒绝那个卑鄙小人,他是这么跟你说的?”小饼嘶心裂肺大喊,焦躁的双眼急迫地等待着我的回答。似乎只要我说一个“是”,他立刻一头撞墙去死以证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