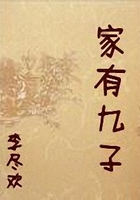最后还是坐上云剑宵的马车,上次是他目前我入宫,今天换成小饼站在门前,孤零零的。
“阿贱,那几个刺客怎么样了?死了吗?”
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最好是死翘翘,不是常言说得好么: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杀人不灭口,仇家追着走。
云剑霄在外头赶车,他轻柔的嗓音如抚水春风:“那些乌合之众,皇上还没放在眼里。只是害得公主受了苦,他们的日子可想而之不会好过。”
“我倒没受什么苦。”小声自言自语。
不经意间倏地阿贱惊惶的叫喊:“有刺客,公主坐稳了。”马车剧烈颠狂起来,只听鞭子在空气中抽得响亮,马儿越路越快,颠得我晕天暗地,刚刚吃下去的点心全吐了出来。
“阿贱……阿贱……怎么回事……”
我颤颤抖抖的掀开帘子一角,就见阿贱的背影绷得笔直,他握紧缰绳的手用力牵制受惊吓的马儿,掌心泛起丝丝红色,可依旧不肯松开半分。
这时候竟然会有刺客?杀我的?要命油!
“该死。”在我思绪天马行空之际,阿贱低咒一声。
只见他长臂一捞把我拎出马车腾空跃起,紧接着“轰”巨响,马儿刹不住脚一头载进河里,滚滚河水浪涛涛,瞬间给冲得没影儿了。
阿贱则带着我轻悠落地,我正庆幸捡回条命,可却发现他脸色不太好。
“阿贱你怎么了?”
他睁着被淹没入河中的马车,沉思许久,直到我使劲扯他袖子方才回过神来,牵开一缕笑:“没什么,回宫吧。刺客不会再来了。”
“你怎么知道?”难道他跟刺客一伙的?
似乎看出我心里写的,阿贱轻哼:“对方没想要我们的命,只是给个警告。”
这算什么理由?我不屑的撇嘴。马车没了,大概得走回宫去吧。
“公主。”阿贱突然开口:“姬聘如没死,她从宫中逃了。”
刚迈出一步路,听到这个消息如同被雷击中。莫非这就是姬聘如干的?这女人还真狠,她的报应为什么要强加在我身上?由始至终,我与她都没有过任何恩怨。
栖凤宫的大门大开,太监宫女们跪了一地,就是没见着兰萱的身影,当我一踏进立刻感觉到无数道凛冽寒意迎面扑来。
夜离歌斜靠在软塌上,慵懒而悠闲的品茶,漆黑的长发如泻倾下,气宇邪魅却不挡眉目如画。那姿势怎么看怎么风华绝代,但我却生生打了个冷颤,生怕被他抓到小辨子。
不会吧?我是被绑走的,不关我的事。
嗯!就这么说,打定主意,我屁颠屁颠蹦上去攀住他脖子高呼:“慎之……”
“嗯?舍得回来了?”连眉毛都没挑一下,随手将玉茶递给了随伺的宫女:“朕还以为你会趁机跑到天崖海角,连朕是谁忘到下辈子去了。”
你老母的,猜得够准。
嘴角抽搐几下,我呵呵贼笑:“我一辈子生生世世都忘不了你。”
“朕该不该信呢。”他冷酷牵唇,泯出的笑意说不出的春风荡漾,却又压抑着无法渲泄的苦涩:“凭那几个没脑子的刺客竟然轻车熟路找到乾清宫,朕觉得宫中一定有内应。”
“你……”我哽辞,面目怔滞,连虚伪的假笑都消失在脸上。怔了片刻,扯扯嘴:“也许他们有地图吧。我被撞见的时候他们手里都拿着很大的纸,应该就是,嗯?对!”
废话,那是老娘的画,不过借鉴一下也没什么关系,反正黑祸你们都背了,再背一次怎么了?
腰际一紧,夜离歌横过手臂把我捞上塌来。他宽阔的身体翻了个身把我压在身下:“遂君,你说谎的时候眼睛总是转来转去,是不是朕逼得太紧了,让你千万百计总想逃离?”
阴邃而深沉的眼睛光芒直逼下来,几乎能扎进我骨子里去,把我的心思摊开在阳光下。
不行,不能承认。我刚要张嘴。
上头落下似有若无的低叹:“罢了。”
还没来得及咀嚼这两个字的意思,夜离歌就执起我的右手,“当!”一个冰凉的东西套在了上面,我定睛一看,竟是个奢华无比的手镯,它由八根雕龙金线纠缠扭结而成,上面镶嵌着十多颗宝石,手背正中配以鸽蛋大的夜明珠,光华璀灿,流光溢彩,这玩意儿我小时候偷进“珍宝阁”见到过,好像是叫什么……不记得了。
“给我这干什么?”抬手晃了两下,怎么觉得很重呢?还拖着什么似的,感觉怪怪的。
他已经直起身子坐好,大手拍拍我的脑袋:“把你牢牢的‘锁’住,直到你的心不再想逃为止。”
他老母的,不管我怎么解释就是无法打消他心底的疑惑。哼,算了,看在这个价钱货的份上,暂时不跟你计较。
打了个哈欠,负气的翻过身背对她,我扬扬手:“算了算了,怎么说你都不信。我要睡觉了。”
我看不见他眼底涓涓流溢的深情与矛盾,唯知道一只宽厚的大手抚摸过我脸颊,耳际,捻齐碎发,而后,拉好被子,方才轻声离去。
直到确定他真的走了之后,我才跳下床来,刚走几步,就被同时传来的奇怪的声音顿住了。就好像当日在地牢里,锁住姬聘如的铁链子被拖动时发出的声音。
怎么会出现在我的宫殿中?难道说是姬聘如的鬼魂回来了找我索命?不要哇,头皮一阵阵的发麻,浑身骨架子虚软。
但是很快又想到,白天的时候阿贱才说姬聘如没死,那我不是自已吓自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