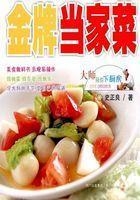再问更多的事情,石玲不肯说了。
沉默十几秒钟以后,她说:“常坤不让我跟你说案子的事情,他怕把你卷进来。”
说完以后又突兀地笑了一下,说:“可他也明白,你迟早都会卷进来的。”
我问她:“今天中午是什么情况?”
她说:“我们在村里做入驻查案的准备,有一个村民,好端端的,突然就死了。”
“你在场?亲眼看见的?”
“我没有。但我们有一个同事亲眼看见的。”
“死因?”
“现在还不清楚,解剖报告要后天才出来。”
“疾病?还是谋杀?”
“不知道。”
有一点冷场。
然后她突然说:“你看见程莉莉的话,转告她一声,别上山了,也别打这个案子的主意了,我知道她想博出位,但这个案子不行,她就算花再大力气也都是白费劲的,上面不会允许她报道。”
挂掉电话,怔怔地看着窗户外面蓝得恍惚的天。
黎淑贞坐在椅子里发呆。
像雕塑。
了无生气也了无生趣。
我猜她灵魂里面有一个巨大的洞。
只是猜不到用什么才能够认真填满。
出门。
下楼。
隔壁单元的戚老太婆站在路灯下面,抱着一只颜色漆黑目光冷锐的猫。
从她身边经过的时候,我听见她在喃喃自语。
她说:“老是想起那些事情,越想越怕,不敢睡觉。”
像是在跟我说,也像是自言自语。
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这个戚老太婆很可怜,有点疯,儿子儿媳不理她,孤身一人住,遇见谁就喋喋不休喋喋不休说她从前所经历的事和所受的苦。像祥林嫂,谁都避之不及。
我走出好几步远,还能听见她在后面说:“越想越怕啊。”
声音发颤,语气悲凉,听上去是真的在害怕。
拐弯的时候我回头看四楼自己的家。
黎淑贞站在阳台上。
灯光勾勒出黑色剪影。
寂寞到心里发疼的样子。
我想我是真的愿意去爱她,像石玲爱她母亲那样,有笑,有亲密,有拥抱,有柔软,有温暖。
可从来都事与愿违。
很多时候我怀疑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精神病患者,有严重的强迫症,轻微的广场恐惧症,可能存在的抑郁症,超出常人忍受限度的洁癖,疯狂的控制欲,间歇性歇斯底里症,也许还存在某种程度的幻听幻视和臆想症。
还做很多不是正常母亲会做的事情,拆看我的情书;偷看我的日记;跟踪我和男生约会并且躲在电影院的后排偷看我们接吻;用疯狂的极端方式操纵我的整个人生规划,毁掉我的恋爱,并曾试图用菜刀自残逼我嫁给一个我看见就想要吐的男人。
我不知道应该拿她怎么办。
我猜我是真的很恨她。
这大概算是人世间最悲惨的事情。
走到小区外面的报亭买一份晚报。
晚报上只有一则关于陈家坞事件的报道,简短到几乎能够被忽略:陈家坞,4月1日中午12点40分左右,村民于成林,离奇猝死,警方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正在调查中。
又是正在调查中。
发稿人是程莉莉。
站在路灯昏黄灯光里抽烟,然后给程莉莉打电话。
打通,听她在电话那端尖叫。
尖叫。
尖叫。
歇斯底里地叫。
猫一样张扬而疯狂地叫。
她说天啊,黎绪!
天啊!
天啊!
天啊!
疯掉一样喊。
她说天啊,黎绪,你看新闻了吗?陈家坞!今天!死人了!跟你说了你都不能相信!我今天也在山上!也在村里!
近乎病态的狂热,凌乱,语无伦次。
我能想象程莉莉在电话那端的样子,裹着白色浴袍,露着白片丰满雪白的胸和两条修长的腿,披散海浪一样的酒红色卷发,拿着免提电话光着脚在客厅的羊毛地毯上来来回回走,张扬舞爪,眼神因为兴奋变得像某种兽类。
每次遇到劲爆的新闻,她都会是这副样子。
她说她和摄影师小张,司机老王三个人早上九点进村,下午三点半下山,没有目睹死亡发生,但是亲眼见到尸体。
她说她手里掌握最狠最劲爆的资料,并且在下山的路上写好稿子,还配有照片,想抢今天的头版头条,可惜,赵清明把稿子压下,说是上面的意思。
她在电话里用最恶劣的词句骂赵清明,说他懦弱,狗屎,混蛋。
赵清明是程莉莉的上司。
也是我从前的上司。
她说:“黎绪,幸亏你辞职了,不然今天跟赵清明拍桌子的肯定是你!”
笑。
我不想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