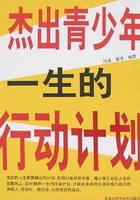会所的这间套房设有餐厅、游戏室、影音室、卧房,所需设施一应俱全,人齐了吩咐后厨走菜,一干人等在房间里吃吃喝喝,说说笑笑,玩玩闹闹。
舒灏看起来很高兴,喝的有点多,就是喝的太多了,即便那唇角咧得开开的,白牙闪亮亮的,也会猜测他是否真的高兴。
他们这帮人喜欢喝军供的白酒,说那才真是酒,外头卖的就跟掺了大半水似的,不够劲儿。
女生面前各自摆放不同口味的果酒,度数极低,和饮料差不多。
兄弟们给寿星公敬酒,然后寿星公再找各种理由回敬过去。
实在没理由了,舒灏举起酒杯顿了顿,嘿嘿一笑,“哎呀,我怎么就这么高兴。”扬起脖颈,一饮而尽。
酒这个东西,只要不想自己醉,怎么也醉不了。要是想醉,对于一个酒精考验的战士来说。
可就照这么个自虐式的喝法,还是弄得大伙一愣一愣的。
坐他身边的苏格拉倒是没觉出不妥,刚接受了池华曦的敬酒,又和另一侧的穆西年轻声交谈着什么。
她这样子看得池聿铭直皱眉。
其实也不能怪她不劝不管,她不过是过于相信舒灏说过的话了。
当年他们还窝在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喀拉拉邦乡间,买瓶啤酒都要开老半天车进城,想吃什么可以下地摘的地方。
某天舒灏借公干间隙来看快成农夫的舒灏,带了一箱子茅台,两人边喝边聊折腾了大半夜。
当时苏格拉还是挺怕他喝多难受伤身的,又不好当着他朋友的面出言扫兴,只趁着池聿铭去厕所的空档悄悄告诉他少喝点。
舒灏挺高兴,捏上她的下巴摇了摇,给她讲了个故事。
话说当年周总理曾和许世友上将拼过酒,喝的就是茅台。
上将是大口喝酒大口吃肉的豪迈性格,酒量极好,压根儿没将总理看作对手。
总理呢,不紧不慢,一小盅一小盅的喝着。
结果呢,上将喝到抗不住了,总理仍是谈笑风生,那酒也不比上将喝的少。
他对苏格拉说,就这么一杯杯的喝,又不是大口灌,啥事儿没有。
这么说她就信了,并且看样子是一直坚信至今。
穆西年探身瞧了一眼,拍拍她的手背,凑近低声说,“你不劝劝?他喝太多了,找这么喝下去非倒不可。”
她有些惊讶:“是吗?”
穆西年被她的愚钝震慑住了:“......嗯,我很确定。”
眼看舒灏又斟满了一杯,刚要举起来,杯沿口就被一只纤细白嫩的手掌覆盖上了。
饶是桌上的诸位见多了世面,也还真没见过这种拦酒的行为。
他们是不是被这姑娘的柔顺外表蒙骗了?内涵竟是这般霸气。
苏格拉只是想要是劝他可能劝不住,眼看他马上又要干了,本能的动作先于思考,只想着阻止来着。
“呃......”她觉着唐突了,侧过头看着舒灏放软了声音道,“还是多吃东西,别喝了吧?”
舒灏略挑单眉,他的眼神已经略显迷蒙,无所谓的耸肩,“没关系,我没事儿。”
他试图抽动了下,清凉的酒水微微晃动,湿滑浸润了她的掌心。
苏格拉的秀眉飞快皱了下,抿抿唇,手心一拢,手指划过他的,捏起卑鄙从上方抽出了酒杯。
“知道你没事,我想喝行不行?”
说罢贴上唇畔,一仰头灌进去了。
白酒冲鼻的味道还没等凑近就刺激她的鼻腔,真喝下去更是不得了,从喉咙口一直向下灼烧,热辣辣的,像是吞下了一团火。
她初时还感慨自己真够厉害的,都能吞火了。等反映过味儿来,才真觉出身体的不适,咳嗽个不停,迅速抓起水果酒咕噜咕噜的咽下去。
舒灏今天是各种心里忐忑消化不良,喝的确实有些多了,不过这下也被她吓精神了,一面拍她后背,一面着服务生拿矿泉水来。
一桌子人被这突发状况弄得哭笑不得,有多久没见过斤两这么浅还敢扮孤勇的人了?
“好没好点呀?”舒灏的声音透着掩饰不住的温柔。
他瞅着她慢慢转过脸朝向他,脸颊粉嘟嘟,双唇润透透,眼睛里更是水汪汪的像泓池水。
酒精似乎涌上了天灵盖儿,他艰涩的滑动下喉结,停在她背上的手又加了些下压的力气。
不好!他好像摸着了bra的带子,那个凸起处是搭扣吧?
他现在只要食指从下面挤进去,挑起来中指和拇指向中间对压,就能解开了!
甚至不需要一秒钟!
“嗯,好多了,这东西度数真高,灏子你今天真不能再喝了。”
舒灏僵硬的扯动唇角算是笑了,讪讪收回手,捞起方才她喝了一点儿的evian水瓶咽了一大口。
“不好意思啊各位,兄弟我今天就喝这么多了,恕不奉陪。”
众人绝倒,谁陪谁啊?都是纵着你寿星公呢好不好!
有人要是欺负人水果酒没度数,那水果酒肯定不乐意。
所以,苏格拉这也算是喝了混酒了。
当然和把伏特加、朗姆酒混入啤酒中的“锅炉厂鸡尾酒”不能比,可只要是混酒就容易醉是真理,尤其是没有经历酒精忠诚考验的。
珍珠白的水晶灯光下,苏格拉开始看身边的人都像是笼罩了一层珠白的光晕,特神圣。
每个人的动作都开始变慢,声音也含混不清。
她分不清自己是困了还是晕了,手肘撑在桌沿儿上,整个人如在水面上,被温柔的水流轻轻包裹,飘来荡去的。
“格格,你醉了?”
舒灏在她眼前“晃”着问,凑的很近,两人的呼吸可闻,都是酒气,可她的也是,一时间混成一团。
“嗯?我好像......”她的眼皮落下,又蹭地睁开,“好像有点儿困。”
他轻笑出声,深邃的眼瞳像是遥远的寒星,眼窝深陷像是要将人吸进去,颊边两处浅浅的笑涡只有这个时候方才显露出来。
“那就是醉了。我带你到卧房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他又凑近了一点儿,附耳说道。
她只觉耳廓又热又痒,抬手上去揉了揉,顿时通红一片,更热了。
这会儿她根本撑不起眼皮了,眯着眼淡淡摇头,“不好,大家都还在。”
舒灏勾过她的小蛮腰,让她跌趴在自己胸前,“不用理他们,等他们要走的时候,再叫你起来送,这样行吧?”
虽说是询问的话,但他或许没有那份心思,另一手直接兜起她的腿弯儿,抱着她站了起来。
苏格拉纵使喝多了,也觉出不对劲了,在他怀里蠢蠢欲动的想要下来。
“别动,老实点。”
他们俩旁若无人的喁喁私语,完全不顾及旁人的“忘我”行为,让大伙压力好大。
这下舒灏要把人抱走了,大伙压力就更大了。
许南川道出众人心声:“你,还过来么?我们要不要现在就撤?”
这要是池聿铭说的,他一准儿“滚”就打发了。对着大哥,他可不敢造次。
“别撤,我很快就出来。”
他窘迫的抱着苏格拉一溜烟的跑进了卧房,就跟她没几斤分量似的轻松。
把她抱进房不难,搁床上也不难,两手撑在她身侧,要退离开这事儿很难。
尤其是对方显然神经迟缓,意识不到自己的处境,那种无意的邀请别提多抓心挠肝了。
苏格拉落在床上,也顾不得方才怎样了,她觉得脑袋在发胀,想要翻个身,却被他的胳膊隔住了,她在枕头上歪了下脑袋,眯着眼睛,视线模糊不清。
“嗯?”带着点鼻音,绵长慵懒的腔调。
于是,舒灏干了件他这辈子都要觉得丢人不已的事儿。
他想是在掌心上装了两只弹簧,腾地弹了起来,死盯着她向后退。
退了一步,不想脚跟抵住了大床旁一方长绒毯的硬质麻编底,高大的身躯像是倾覆的大厦轰然坠落。
那长绒毛吸收了他坠落引发的声响,迷迷糊糊的苏格拉只觉这人突然就消失了,纳闷他跑的还真快,翻个身会周公去了。
根据重力加速度原理,可以想见他那么高的身材摔在地上会有多疼。
好在还有块毯子可作缓冲,否则屁股非要开花不可。
他被个姑娘家吓跑了,人家还浑然不觉他的惨状,幸或不幸?
舒灏赖在地上又坐了会儿,盯着她因侧卧而起伏的背影瞧,然后慢腾腾站起来,帮她脱了鞋,揉了揉自己的两瓣屁股,这才昂首阔步走了出去。
苏格拉原本想着小眯一阵的,猛然醒过来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在酒精的作用下睡得很沉,连梦也没做一个。
她睁开眼,卧房内昏暗一片,只有鹅黄的壁灯,如烛火般散发出微弱的光芒。
缓了缓神,她换了个平躺的姿势。
“醒了?”
舒灏的声音已经很熟,只是这样突然发声还是吓了她一跳。
她按着胸口侧过头问道:“他们呢?我是不是睡了很久?”
舒灏掳了下袖子,看了一眼手腕上的江诗丹顿Malte,“他们走了。也没多久,两个小时。”
他回答了她的问题,眸色沉沉,神色晦暗,语气平板的不像是他的风格。
她撑着身子坐起来,神情有些懊丧,“怎么不叫我一声,这样多不好。”
“你等我一下,先别起来。”
她揉着太阳穴,听到他的话随意点了下头。
喝酒这事儿,要么不沾它,要么就能喝,没有中间地带。
大约一分钟的时间,房门再次开启,一辆移动餐车从门外率先入内,上面放置的是燃着一根蜡烛的生日蛋糕。
这是……什么情况?
今天舒灏穿了件深蓝紫色的V领丝光绒衫,他弯身推着小车,火光照亮了他胸前露出的蜜色肌肤,浅浅一道肌肉线条显得愈发深邃。
他走的很慢,像是每一步都经过了审慎的斟酌。他垂着眼帘,更显出一副深思的模样。
这情况好像过生日的是她,苏格拉急忙跳下床迎过去。
“你还没有吃蛋糕么?是不是也还没许愿?几点了?还来不来得及?”
她难得的快言快语,他却是冷静非常,深沉地说,“你先坐到床上去。”
她“哦”了声,转身又回到床上去,舒灏将小车推过去,横在床前。
“快许愿!”烛光活泼地跳跃了下,映照着她嫩滑的脸和晶莹的眼。
舒灏定定的看着,然后在蛋糕前单膝跪下,隔着蛋糕就是她。
她尚未察觉有什么不妥,一边催促他许愿,一边欣赏这只铺陈了朵朵精致逼真深红玫瑰的翻糖蛋糕。
翻糖作出的东西简直可以以假乱真,只要环境合适,保存时间会很长,据说世界纪录保存最长时间的翻糖蛋糕足有几十年的历史。
眼前的这只,每一朵的花瓣轮廓、叶脉线条,乃至枝条上细小的刺都清晰可辨,好似还能闻到花的芬芳,还真是舍不得把它吃掉。
舒灏清清嗓子:“我要许愿了。”
“嗯,要闭上眼睛,虔诚的向神祈祷,不能说出来。”
“会灵验么?”
“一定会!”
舒灏扶住推车两侧把手,仰头直至看着她盈满笑意的眼,字字句句清晰的说:
“我,舒灏,爱苏格拉。如果神明有灵,希望她愿意嫁给我。这就是我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