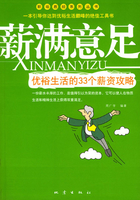翌日约摸快到中午的光景,翻来覆去折腾到近天朦朦亮时睡着的舒灏才醒转过来。他的作息不算健康,这个时间才起床也不算稀奇,以睡眠时长计算,这还算起得早的。
他四仰八叉躺在床上,两只大脚还探在床缘外,眼中的困顿神色尚未消散,甚至还挂着疲乏的血丝,歪了下脖子调整角度,望着天花板上莲花形状的顶灯,眨眼再眨眼。
许是唤醒了些意识,他舒展开颀长身体伸了个懒腰,顺便附赠一枚响亮的哈欠,觉得舒坦了又咂巴咂巴嘴,于是发现自己饿了,这才翻身利落地坐起来。
叉开双腿,平抬两臂,屈肘双手交握,左右转身扭腰。
浅金色的阳光照拂在男人周身,他借着窗子上模糊映照的影像审视自己,宽肩、平滑的锁骨、窄腰、未扣搭扣裤腰微敞大略可见的髋骨、纠结分明却不突兀的肌肉线条……他很有资本呐。
唇角刚有上扬的趋势,却凝住又回落,资本也要有赏识的人才能兑换成为实用价值不是?
对面楼下停着一辆家具城的送货车,身着统一制服的工人正小心翼翼从车厢上搬运家具,欧式田园风繁复线条花朵乱缀高级货。
舒灏看着看着就又打了个哈欠,比格格家还让人眼晕啊。想起苏格拉,他又琢磨着不知人走没走,给没给他留口饭呀。
转身就是一床凌乱,他微蹙眉,还是弯身一样样叠好,虽然折好的边沿纵横交错,可也聊胜于无,他很得意。
直起身时又是嘴角上翘再回落,因为他看到了那双迷艳止诡异的红缎舞鞋。
“红色舞鞋,穿上便不能脱下,惟有永无休止的舞蹈,至死方休。”
这是《安徒生童话》里的一段故事,一双凶残噬人的舞鞋,美则美矣,寓意凄惨。
舒灏并不迷信,可他见这东西就观感不佳,何况格格如今不跳舞了,摆这么个东西做什么?
小方厅没有人,厨房里也没有,苏格拉的卧室门是打开着的,舒灏几步走过去,撑着门框往里望。
她还在,没有躲着他!他很惊喜,眸光却缓缓地变得柔和清凉。
秋日里,即便是正午的阳光也只是温暖,仿佛色泽上褪去了夏日的浓烈,便一并将热闷也带走了去。
他的格格正抱膝坐在宽敞的藤编包覆的窗边矮榻上,并拢的双脚前方搁着一只盛了半杯白水的长颈玻璃杯,杯沿上还燃着一小簇闪耀的光芒,他看着不由得眯了眯眼,嫌太亮。
苏格拉并没有意识到舒灏的存在,她正享受着暖融融的阳光,整个人像是罩了层透明却夺目的金罩,一边舒服喟叹,一边遥看油油的绿化带养目,顺便望个搬家的风景,惊讶于搬家工人强劲的力量。
“喂!望什么西洋景呢,我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