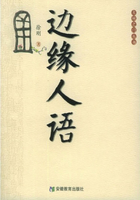一首诗的美,无法用语言诠释。就像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表达的是含蓄绵密的情意,最能心领神会的是那个有情人。诗,是想念的信物,是情感的象征。因为诗,我们被理解,被安慰,被包容,被温暖。纪伯伦曾说: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一个笑窝涌出的一首歌曲。最初的那一首诗,一定和情感有关。
和风吹动我窗,
可是来自故乡?
请去寻找我青梅竹马的恋人,
将她带到我的身旁。
最初的爱恋,应该是猝不及防的。
阿旺嘉措的爱情是开在春日里洁净的玉兰花,他和爱人的相遇,应该是纯净的天山水,犹如乳白色的月光流连在窗前,一低头,看见无尽的相思;又宛如温润的玉,躺在岁月的河里,泛着莹莹的光泽。阿旺嘉措用最简单的音符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忧伤、失落和希望。不用任何粉饰,他用最简单的字眼唱出生命的每一个片段,吟出最纯美的旋律,在高原清定的风里,裹着青草的芬芳,在鼻翼,在眉宇间,爱的波光流转经年。
在那个年代,人们从高原雪山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佛的身边,倾听达赖喇嘛的教导,。偏偏,阿旺嘉措是佛的使者,他却是一个把爱情当做宗教的人。在阿旺嘉措的心灵历程中,爱情的萌芽要追溯到家乡门隅。
北部的达旺地区是门隅宗教、文化中心,这里气候温润,风景如画,被门巴族誉为美丽的“松耳石盘子”。北部高原的边缘,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来自南方的温湿气流阻挡在峡谷之中,即使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时节,河谷地带仍是山青水碧、春意盎然。这片温润的土地默默地看着生长在它怀抱中的儿女。
这是一片天然的乐土。聚集在这里的门巴族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情歌在门隅的田园中蜿蜒流淌,这个古老的民族,崇尚自由,尊重爱情。
这里的爱,可以肆无忌惮。诞生在爱情理想天国的转世灵童,他身上吸收了这块圣地的灵气。
在错宗那最好的寺院学习,还能得到很多高僧的亲自传授佛学精要,这样的荣耀不知羡煞了多少寺僧。但是仓央嘉措却觉得“沉闷”。十四岁,阿旺嘉措的心开始蠢蠢欲动。如果还是在民间,这个孩子或许只是一个俊逸的男子,不谙世事,过着简单的生活,有烦恼和苦闷,坚持着简单的快乐。
一个活佛的少年时代,不同于普通的孩子。阿旺嘉措的少年和其他活佛的少年时代又不大相同。入寺学习,平添了阿旺的睿智。和智慧一起成长的,还有年华。此时的阿旺,因为多了佛书的熏陶,他的眉眼里更多了清定的气质,将世俗的烟火抵挡在千里之外,这样的佛风仙骨,看在曲吉和多巴的眼中满是欣喜。
平淡的日子一天一天流走,阿旺嘉措一直觉得,日子应该就是这样平淡度过的。风从家乡吹来,一个讯息打碎了日子的平静。
多巴带来消息说,母亲次拉旺姆病故了。
这样的消息一下子重击阿旺嘉措。早在几年前,操劳一生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是阿旺嘉措在门隅最强烈的牵挂。这么多年,记忆中还是母亲年轻的样子:她双眸明亮,像黑夜里跃动的烛光;细细的眉毛是春风中浮动的水杨梅,脸若满月,高原的风吹起,宛若绯红的桃花。那些诗句中盛放的桃花,是母亲柔美的容颜。
法国的雷尼伦曾说:孤独是已经死去的一切仍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座活坟墓。阿旺嘉措的离家带走了母亲一部分灵魂,母亲不再像过去那般活泼喜乐。阿旺在家时,家中时不时会传出母亲的歌声,傍晚劳作不忙的时候,母亲还会弹奏口弦,动听的口弦声在橙色的黄昏中传出很远很远,很多孩子赶着牛群归来,循着乐声就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不多久,丈夫扎西丹增的离开更让母亲陷入到孤单,蚀骨的思念蜕变成顽强的病毒,她一病不起。终于在一个寂寞的秋日里,萎谢而终。
巴桑寺的佛堂里,阿旺嘉措默坐着,面无表情,撕裂的心宛如残阳喷薄的最后红暮。一连几天不念经、不打坐、课程在沉默里一一搁浅。师父们脸上的担忧愈来愈明显。经过协商,师父们决定,允许阿旺出寺散心。
这样的决定,一片苦心可见斑斓。还是十四岁的孩子,苦闷的寺院难以排解内心的忧虑,出去散步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是师父们说服彼此的最好地理由。也正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阿旺的一生。
一个少年的沉闷心思,高僧们不能理解。母亲的去世,让阿旺更多了对生命的思索。佛家常说:万法皆生,皆系缘份,缘起即灭,缘生已空。这样的母子情缘是不是太过于浅薄?宿命无常,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即使是活佛也不例外。师父曾讲,活佛是西藏至高无上的神,即是神,又何来地肉体的泯灭?疑惑一个一个在心中打上了问号,把他推进一个无望的漩涡。
阿旺是个内敛隐忍的人,心中这样的郁结自然不能说与师父听,这样的困惑,在师父们看来是一次出局的臆想。最好的选择,是将波澜归于沉寂。
出寺散步,或许排解苦闷的一个好方法。阿旺最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命运给予的是怎样急促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