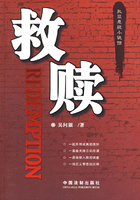想到这些,郭颖感到背脊发凉。卓然没来得及说出她遇到了什么,而也许是类似的东西,现在正一步步向谢晓婷逼近。并且,自己也已经在这个可怕的边缘上徘徊了。从寝室到后山,那个莫名其妙的东西看来盯上了她们,并且采用一个一个击倒的方式,先是卓然,现在轮到谢晓婷和自己了。
郭颖感到身体发抖,她紧紧抱住谢晓婷,这个罗曼蒂克的美人儿在饱受惊吓后已昏昏入睡了。当感觉到谢晓婷结实的乳房正紧紧抵着自己时,郭颖突然想到“他吻了我的胸部”这句话。真是奇怪,这句话使郭颖的惊恐情绪慢慢地掉换了方向。看来,有一种东西是足以对抗恐惧甚至死亡的。
郭颖感到身体正渐渐热起来,那热量从谢晓婷的身上源源不断地流向自己。她从谢晓婷的胸部间接嗅到一种异性的气味,那残留在谢晓婷身上的电流使她头晕目眩。她将手放在自己的腹部,想到了中学时在姐夫家的经历,那是一种极度惊恐和兴奋的体验。她想,如果当时持续下去,足可以让人死掉的。
那么,这种极乐园里的果实是否天生和惊恐、死亡有联系呢?郭颖想到了后山,在这个冷静、有序的医学院里,那座林木茂密的后山却藏满了男女同学们的激情和不羁,而这仅仅是因为暗黑的后山可以为每一个人保守秘密吗?会不会是因为,曾经深埋在后山下洞穴里的亡灵散发出的气息像一种激素弥漫在后山?
二十年前,正是郭颖、谢晓婷们出生的年代,四个学生——三男一女被关进了这后山下的防空洞里,这四人当时的身份是红卫兵组织勤务组成员,也就是头儿的意思。医学院是这个红卫兵组织的大本营。大本营被另一派红卫兵组织的炮火攻占后,头儿们自然性命难保。但这种死法没人能想到——被秘密地绑进防空洞里,用砖头水泥封住了洞门,以致无人知晓这一残酷的事实。直到十年过后,这秘密才得以曝光,但人们看见的只有白骨了。学院老校工讲到这些往事,手就有点发抖,“一堆白骨,还有衣扣、钢笔和一个发夹混在白骨中,惨啊!”
关于“文革”,郭颖从书籍和长辈们的回忆中知道一些概况,但万万没想到,当时才刚刚出生的她,今天居然在校园里嗅到了这个久远年代的气息。一切都从卓然捡回那个发夹开始,那个不知谁失落在后山的发夹,它将卓然带向了精神分裂的迷雾中。
郭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一定要解开这个谜团!这个突然袭来的决定使她兴奋得有些发抖。她从谢晓婷身边坐起来,望着蚊帐外的暗黑已在变淡,天快亮了,后山又将显露在夏日的晨光中。可是,它的秘密潜伏在密林中,到晚上便随风而行,她一定要弄明白这个东西。
她轻手轻脚地钻出蚊帐,拿了牙刷毛巾去洗漱间。各个寝室的同学们都还未起床,走廊上空旷得像是一条无人地带。她坚定地踏响步子,心里说,我什么也不怕!我要弄清楚一切,并且,就从今天晚上开始,我要去后山观察。
后来,郭颖所做的一切,让胆大的男生们也瞠目结舌。
我的这本书始终写得战战兢兢。一方面,十四年前发生在医学院里的怪事搅得我头晕,从女生寝室到后山的那一片地带显得危机四伏,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郭颖至今心存疑虑,这增加了我在写作中试图发现真相的难度;另一方面,闯进我书房里来的不速之客严重干扰了我的写作,要命的是,吴医生证明这人是一个已死去的精神病患者,这使我对自己和自己的处境都产生了某种虚幻感。
可疑的是,据吴医生介绍,这个叫严永桥的精神病人已住院三年了,他在一个多月前的夜里从医院跑出,死在夜半的高速公路上。既是这样,作为医院的护士,董枫怎么会表示从来不认识这个人呢?
更让人迷惑的是,我的那个年轻朋友张江在望远镜里爱上的女人竟是董枫。我详细询问过了,张江家住在城南大道体育馆东侧,他在窗口用望远镜看见的那个女人所住的楼房在他家斜对面一百米左右,是一幢杏黄色的七层住宅楼,他望见的女人住在二楼,窗帘是乳白色的,阳台上有晾衣架和六盆植物。一切都没错,那是董枫的家。然而,当张江昨夜推开董枫的房门时,怎么会是一个老太婆正对着他呢?
真是邪了。我差点要怀疑是不是我正在写作的书触犯了什么,那些十四年前的鬼魂通过那个不速之客要给我带来一连串的惩罚。
无论如何,我现在连退缩的余地都没有,我必须搞清楚一切才能心安。
上午十一点,我举手敲响了董枫的房门。真是活见鬼,我现在要见董枫这样熟悉的人时,心里也有点七上八下。
门开了,董枫站在我的面前。她穿着一件鹅黄色的薄绒浴衣,长发盘在头顶,眼睛里已有了往日的光亮。看来,她已逐渐从遭遇黑屋子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了。
坐下后,我说:“你精神好多了。怎么,医院黑屋子的事搞清楚了?”
“在家睡了两天。”她说,“我想,也许是我的幻觉吧,当时是雷雨中,又是深夜,闪电打在窗上,也许让我看花眼了。那间病房长久无人住了,怎么会出现一个正在梳头的女人呢?我反复想了,只能是我的幻觉。”
“也许是吧。”我一边应和着,一边起身走向阳台的门,“通通空气。”我推开了这道门,看见了阳台上晾着的几件衣物和花盆。
夏日的阳光从阳台上射进来。我转脸问道:“你晾在阳台上的丝裙掉到楼下去了呢?”
董枫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这事奇怪极了。那裙子如果要掉,只能是往楼下掉的,可是不,它莫名其妙地出现在我门外的楼梯上。今天早晨,我听见下楼的邻居在问,谁的裙子呀,怎么扔在这里?我开门一看,那不是我晾在阳台上的裙子吗?真是奇怪,我拾了回来,泡在水池里,还没洗呢。”
看来,张江没找错地方。我把张江在望远镜里被她迷住的事详细讲了一遍,当讲到昨夜张江从楼下拾起她那被风吹下的裙子送上来,推开门却看见一个老太婆时,董枫惊叫道:“不可能不可能!昨夜我没听见有人敲门呀!”
我说:“据张江说,门是虚掩着的,屋里没有开灯,屋里的老太婆正对门坐着,嘴里还说了句‘你来干什么’,他吓得转身就跑,那裙子也就掉在楼梯上了。”
这事实让人迷惑。如果说张江上楼时找错了地方,这裙子就不该掉在董枫门外的楼道上。可现在事情对上了,那么,这里哪来的老太婆呢?而且,昨夜这门是虚掩着的,屋内没有开灯,一个老太婆正在暗黑中对着门坐着……
我望着董枫,鹅黄色的浴衣衬出极好的身材,长发盘在头顶,还散发出浴后的香味。这年轻的女子在夜里会变吗?我在一刹那间脑中掠过这个荒诞的想法,心里惊跳了一下之后,随即感到好笑,看来,我也快让这些怪事给搞昏头了。
董枫想了想,说:“哪来的老太婆?那个张江是不是神经有问题,或者,他故意编造这个故事来吓我们?你想,躲在窗帘缝中用望远镜看女人,这说明他心理本身就有些阴暗。”
董枫毕竟是精神病院的护士,喜欢对人的行为从精神方面作出解释是一种习惯。但是,我知道,事情还不是这样简单。
我说:“不对。据我的了解,这个爱好文学的大学物理系学生非常健康。别把正常人都想成你医院的患者。至于在望远镜里的一瞥便迷恋上一个人,这对于一个敏感而富有想象力的年轻人来说,完全可能是这样,正常得很呢。”
董枫的脸上飞过红晕,她将眼光垂向地面,喃喃地说:“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突然想到,董枫的隔壁邻居是什么人呢?会不会是一个老太婆,而张江昨夜上楼来走错了门。
然而,董枫肯定地说:“没有什么老太婆。这幢楼的邻居我都不了解,但隔壁这家我是知道的,住着一对夫妻,常人说的老夫少妻吧,男的五十多岁,女的二十多岁。平时只有这女的一人在家,男的在外地办公司,每个月回家来住两三天,哪来的老太婆?”
为了证实隔壁的情况,我让董枫以借解刀修电器为由,敲开了隔壁的房门,我也顺便跟了过去。
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站在门内,穿着白色的吊带背心,胸脯高耸。她的身后是一个漂亮的客厅。
“解刀,”她笑吟吟地说,“我家没有这种东西。”说话时她同时望了我一眼,我想她一定把我看成是董枫请来的电工了。
“哦,”董枫应道,同时编造着说,“昨天有个老太婆在楼下找人,是你家的客人吧?”
那女子笑了起来,“我不知道,我家没有客人来的。”
回到屋内,我和董枫都很纳闷:张江昨夜在这里的遭遇是怎么回事呢?我曾一度大胆地想到,董枫租住的这套房子以前是不是有一个老太婆住过,后来这老太婆死了,房东把屋子打扫干净,又租给了不知情的董枫。这想法一闪而过,但我没说出口,因为我自己也知道,这种设想绝对荒诞,毫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