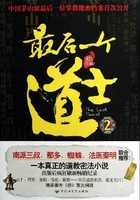冬日的黎明总来得晚,机警的公鸡怕是等得心急了,一见到黎明送来的第一抹玫瑰色霞光,就吹起了起床号,早就睡够了的小银似乎在伸懒腰,仰首长鸣。天光从窗帘敞开的缝隙中偷偷地溜进了我的卧室。在凌乱的被褥之间,我听着雄鸡的啼鸣,思念着阳光,盼望着白昼的来临,多么幸福的事情啊!
我在想,如果不是遇见我,小银会过着怎样的生活?也许它会被卖炭的人驱赶着,去偷松枝,那小小的身躯,在夜间霜冻的小路上艰难地行走;又或者成为那些穿着破烂的吉卜赛人的驴群当中的一个,还是最毫不起眼的那个。我敢打赌,它肯定不会是现在这种颜色,因为它会被涂得五颜六色。吃肯定吃不饱,据说吉卜赛人给驴吃的是砒霜。此外耳朵也要遭殃,它们被扣着,不能放下来。
小银又开始叫了。这个小家伙,难道它感受到我的思念,在回应我吗?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那么喜爱它。在这旭日初升之时,人很容易怀旧,对小银的思念就像黎明即将到来一样令我兴奋。感谢上帝,它有一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那是我为它建造的厩栏,就像一只摇篮,里面有我能给它的全部温暖,当然还包含了我对它的思念!
小花
——献给我的母亲
我母亲曾对我说,特雷莎大妈去世时曾在嘴里不停地念着一种小花的名字。不知为何,小银,我总会把这种小花,跟我儿时梦中见到的几个星星联系起来。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种小花的名字,它就是马鞭草,它有好多种颜色:玫瑰色、天蓝色和紫色……
我常在庭院的铁门前,透过铁门上镶着的彩色玻璃看太阳、月亮,那变成蓝色或是暗红色的太阳或月亮,真的别有一番美丽。那时我似乎看见过特雷莎大妈,印象中的她总是那个样子:弯着腰,在天蓝色的盆花和白色的花坛前久久地凝视。她几乎是木然地待在那里,从不曾回头,不管是在八月毒辣的太阳下,还是九月冰冷的大雨中,她总是那样站着,我甚至怀疑她会不会在那儿变成化石,以至我总忆不起她有张什么样的脸。
小银哦,我母亲说,她在病重呓语时还一直叫着一个园丁的名字,大概是那位曾经很温柔地带着她在花园中散步的园丁吧。在我残存的记忆中,特雷莎大妈也总是微笑穿过马鞭草的花丛走向我,她的这种爱好,现在几乎成为唯一能让我想念她的事情:在她曾经走过的窄窄的小径的两边,全部种满了那种小花,那种让大妈死前还记挂的天蓝的、玫瑰色的和紫色的马鞭草,在我儿时的睡梦中,这些花常伴随夜空中的流星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