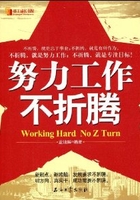眼看着雨下得越来越大,若是不赶紧赶到前面的镇子上去,只怕他们就要雨夜露宿荒野了。
聂涯儿心中看着焦急,无奈又不知该怎么开口说。阿难陀的身体很虚弱他是知道的,看公子现在对她这么好,是决然不会同意让她在这个时候淋雨的,到底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他又忍不住想起那个总是在他没辙的时候帮他出主意的人,虽然多数时候他的主意都很馊,但至少每一次都能帮他解决问题。可是现在,那个人却再也不能帮他了。
苏焕啊苏焕,你倒是好了,一走了之,轻轻松松的。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公子麻烦重重,我不但帮不上忙,反倒总是给他添乱,你在天有灵,帮帮我好不好?
想起苏焕,聂涯儿的眼泪不由自主地落了下来。
所幸,他正站在雨中,雨水打在脸上,早已分辨不出,究竟那些是雨水还是泪水。
突然,马车动了一下,稍微向前一倾。
聂涯儿被吓得一愣,愣是站在那里傻住了。不会这么灵验吧,他刚刚祈祷苏焕帮他,就真的有人帮忙了?
再看看马车,里面突然没有了洛夜白的身影,只剩姜儿守在软榻旁看护着阿难陀。
“公子——”聂涯儿惊叫了一声。
“你去驾马。”马车后面传来洛夜白清冽醇厚的声音,话音刚落,一道闪电划过头顶,几乎要照亮了半边天空。
聂涯儿心中一惊,不敢再耽搁,连忙跳上马车,拉住缰绳。
“啪——”鞭子狠狠一抽,马儿吃痛,拼命地往前拉。
如此反复多次,好不容易才将马车拉了上来。马车一上来,驾车的马顿感身上一阵轻松,一溜烟地跑了出去,任聂涯儿怎么唤都拦不祝
就在他着急无奈的时候,突然身旁一暗,多了道人影,转身看去,洛夜白白色的衣衫早已湿透,雨水打在他的身上,他却似乎浑然不觉。
“专心驾车。若是再陷入坑里,你就可以回听七楼了。”他冷冷地吩咐道,似乎不带一丝感情。
然聂涯儿却拼命地点点头,只是一句话也说不出——
洛夜白坐在他身旁,手中执了一把伞,几乎整把伞都罩在聂涯儿身上。尽管聂涯儿心里明白,洛夜白这么做,除了是担忧他,更多的是希望能尽快赶到前面的镇上,也好继续替阿难陀解毒,可是他的心里还是忍不住难过起来。
曾几何时,他的主子是个多么不可一世、高高在上、受万人敬仰的七公子,他冷酷无情,心若冰冷,可是那样的他至少不会受到伤害,不会受世俗牵绊。
而今,公子依旧是公子,却是早已不再是以前的公子。他有了感情,他为了那一个女子,甘愿步入红尘,受尘事煎熬。为了她,他学会了太多,也做了太多。然终究,不过徒劳无功一常
“驾——”聂涯儿心中苦闷,却哭诉无门,只能把怨气洒在马的身上。狠狠的一鞭子抽下去,马的速度更快了。
等这一次的事情办完了,他回去之后一定要找苏焕好好喝一顿,告诉他自己这些日子过得有多烦闷,一个人有多痛苦。
马车的门帘始终是撩起的,透过朦胧的雨帘,依稀可见那道挺拔的背影,凄清之中带着无尽的苍凉。偶尔,他回过身看向她,沉敛的眼底是幽冷的眸光,让人不由得心惊。
“阿难陀,你还是不愿告诉他真相吗?”姜儿有些不忍心,扭过头来替阿难陀拉好毯子,犹豫地问道。
“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不能说。”阿难陀神色凄迷,懒懒地躺在榻上,沉沉地阖上眼睛。“不过,现在似乎已经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爱上了别人。
尽管那个人是她,可是终究又不是她。
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他爱上的,究竟是这张脸,还是这个人。
也许,都不是。他只是在这个混乱无助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可以紧紧抓注自以为可以解救他的人,所以就再也不想放开。
这样也好,至少,他终于摆脱了尘如语的厄运。
从今以后,终于不用在担心他会因为尘如语而受伤,而那牵情蛊,也终于伤不到他了。
或许,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渐渐忘了尘如语,忘了他们曾经一起走过的日子,忘了曾经一起做过的事,救过的人,也终于会忘了,那些被尘封的往事。
从今以后,他爱的人,会是她阿难陀,一线天的主事阿难陀。
这是一件多好的事,两全其美,各得其所。
可是……
“姜儿,将车帘放下。”她侧过身去,背对着车门,淡淡吩咐道。
双手努力捂住胸口,试图阻挡那股突然袭来的寒气,可惜却是徒劳无功,寒气直直袭入心底,传遍了全身。
因为这一场突如其来而又拖延如此之久的大雨,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镇子,仍然堵截了许多南来北往的路人,商人、旅客、四处游历的江湖人士……
看着这些身份繁杂的人士,姜儿心中着实担忧,生怕被人知道了阿难陀的身份,会有宵小之徒趁机作乱。无奈这里处于金陵和苏州的中间,前不着后不靠的,再说外面的雨下的那么大,想要转移绝非一件容易的事,只得勉强留了下来。
马车在一家不大不小的客栈门前停下,姜儿撩起帘子看了看,见客栈的门楹上挂着一块上书“听七客栈”。
“这客栈的名字好生奇怪,怎么听起来这么像听七楼?”姜儿兀自嘀咕着,回身一看,阿难陀尚在昏睡之中。
马车刚一停下,聂涯儿就迅速跳下马车,走进客栈里与掌柜耳语了几句,掌柜即刻便迎了出来,满脸惊讶笑容地看向洛夜白。
孰料洛夜白根本没有理会他,只是淡淡地吩咐了一句“即刻准备上好的干净客房”,便转身跳上了马车,进了车内。
聂涯儿明白他要做什么,连忙撑起手边的伞,站在马车旁候着。
片刻过后,洛夜白从车上下来,怀里抱了一个人,只是那个人被洛夜白用那只绒皮薄毯包裹了起来,尤其的面容被遮得严严实实,再加上那人有意将脸对着洛夜白的怀里,外人自然是怎么也看不出洛夜白所抱之人是谁。
从进门到上楼,一直都有人投来好奇的目光,只是在碰触到洛夜白冰冷的眼神时都很自觉地避开了。
听七客栈,自然毫无疑问是听七楼在此处的一个联络点,平日里来这里投宿的那些人并不是傻子,都是明白之人,自然知道这一点。
这个身着白衫的年轻公子一出现,掌柜就抛下店里的生意上前恭迎,又吩咐小二带几人到楼上最好的客房,可见此人身份不一般。而如今在听七楼,如此装扮的年轻公子想来就只有七公子洛夜白一人了。
洛夜白始终面无表情,冷面相对,硬生生地逼退了所有好奇的目光。直到上了楼,进了客房,将阿难陀放下,他的脸色才有稍微的缓和。
“多有得罪了。”看到阿难陀并未被淋湿,他放了些心。
见阿难陀淡笑着摇摇头,面容却始终有褪不去的疲倦。
“聂涯儿,吩咐掌柜准备干净的热水,淋了一天的雨,二位姑娘要沐浴更衣。”他冷冷吩咐了一声,并不给二人说话的机会,转身走到外面的外厅。
这间客房挺大,外面是外厅,往里走是用饭的地方,再往里走才是卧房。
聂涯儿领着小二将热水和木桶送上来之后,就自觉地退到了门外。姜儿出来看了看端坐在外厅里的洛夜白,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意思,不禁有些赧然。
“阿难陀——”她轻轻喊了一声,阿难陀睁开眼睛看了看四周,眼底沉静如水。
刚才洛夜白抱她上楼的时候,她早已醒来,只是疲 惫让她根本不想睁开眼睛,所幸就这么一直闭着眼睛,半睡半醒地听着他们偶尔的几句谈话。
“怎么?”她睨了冒着热气的木桶一眼,勉强起身问道。
“七公子在外厅……”姜儿话说到一半便停下了,面上有些为难。
阿难陀会意,不由得轻声一笑,握住姜儿扶她的手,示意她不用担心。
她并没说要让洛夜白离开的话,她了解他,甚至超过了任何一个人。这个时候,她因为中毒而身体虚弱不堪,再加之她本就不会武功,而这里四周又是鱼龙混杂,想让他离开是决然不可能的事,尤其——
尤其,方才他已经承认了对她的感情。
尽管他自己尚不清楚那是一份怎样的感情,但至少不会因为避讳那些世俗的偏见和眼光,而就此撇下她们两个女子不管。
退去那一身莲色衣着,将整个人都浸泡在温热的水里,突然有很多事情跃然于眼前。
犹记得那日,像这般毫无顾忌地沉入水中的情景,白色的裙衫和水晶面纱飘荡开来,最终,她舍了那张面纱,自己独自沉入潭底……
不过是一个回身放下衣服的瞬间,再回身时骤然不见了阿难陀的身影,姜儿吓得大吃一惊。
“阿难陀——”她失声叫出声来,仔细看了看,水面沉静,根本不见阿难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