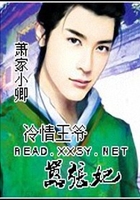悬月是由重楼一手带大,自是顺承了他所有的脾性,所以濯雨一点不奇怪翠微宫了无人烟般的宁,正如他从不奇怪紫宸宫满是鸟语花香,却无丁点人声的静。只是,他到是诧异着会在翠微宫见到一地杂乱。他记得,他那个弟弟,怪毛病一堆,对周遭环境要求的苛刻,更是当数第一。
“让王爷见笑了。”葵叶福身为他解释道:“公主想要迁居偏殿,决定下的匆忙,好些地方还未来得及整理,还望王爷见谅。”
濯雨微笑耸肩,心里对那种感觉多少是有些明了的。
自这皇城建成的那天起,这里就没少过冤魂恨意,即便是没自己下过手,要平心静气地待下去也是需要几分心力的。更何况,这次的孩子死在了自家的屋里头,死在了自己的眼前,还是那副惨状,连他这个对此等残忍血案早就习惯的男子都有些受不了,更何况是那个女子呢?
那孩子也确实可怜,怕是眼都没睁过几回,这个世界的模样都没瞧个清楚,就这么去了。要怨,也只能怨他自己生在这个家族,有这样一个母亲。
葵叶倾身为他推开房门,边不着声色地打量着身旁的红衣男子,猜测着他此时到访的意图。
这宫廷之事,太过错综复杂,她不明白,也不想明白,如果日子可以重来,她也希望悬月没有明白的一日,只是,生在这个环境,很多事便由再也不得自己选择。
因那个染了血的夜,龙帝憔悴了,雪嫔疯癫了,还有悬月,恐怕也不再是那个往日的她。
那个被云雁落藏起的盒子里头仅有一方雪锦,上头或许有些什么,她没读过书,识不得上头有的点滴,但是悬月看懂了,她笑了,拧皱了那块锦帕,悲哀凄凉地笑着,然后挥开了桌案上所有的杂物,打碎了整屋的瓷器,然后,踩着满屋的碎片,伏在几案上笑了,却也是哭着。
这样的悬月,看得她的心都拧了,可是却不知该如何抚慰,而那个唯一可以拯救她的男子却抽了身,再不会转身。
“你不需如此防着我,我的确不是什么好人,但也不是穿肠毒,至少对悬月来说,称得上鹤顶红的还不是我。”
濯雨侧过眼,上下扫视着眼前女子满身的戒备,戏噱的嗓音也是提醒着她刚才的举措已是越离了身份。
葵叶脸色一白,曲了膝,磕上冷硬的地面,“奴婢该死。”
濯雨甩甩袖,道:“有你这般忠心的奴才,若是我也当是乐的。只是,这里是皇宫,不是寻常人家,即便你只是想尽忠,那也是要花上几分心思的,不然,你的忠心只会为你的主子惹上麻烦。”
说完,便不再搭理那人,径自走入屋里,身后的葵叶这颤颤才起身,为他拉阖上门。
这偏殿不若主殿那般的大,濯雨入了屋,抬手挑开垂幔,便见到了那人。不知是刚起还是根本未睡,这时的悬月只着了件宽大的雪色长袍,未梳好的发垂落在地,与曳地的袍摆纠结缠绕,黑与白的界限本是明显,现在却又似乎淡了去。
悬月本是倚着软塌,屈指托腮研究着手中雪帕,一个转眼间,见到素色纱幔中少见的一点红,先是有些讶意,片刻后又回了神,直起了身子,敛束好微敞的衣襟,道:“坐。”又为他沏上一杯银毫道:“该说希奇着呢,你怎么会上我这来?”
“是给你送折子的。这几份就等你的意见了。”他推过放上几案的奏章道。
“这种小事,随便遣个人过来就行了,何需你特意跑一趟?”
“尽是坐着,也是闷。再说,”他挑了眉,勾唇露出妩媚的笑,悬月眉头一拧,那人已两指夹起一块雪色锦帕道:“如果不来这一趟,还不知有这等有趣的事呢!”
悬月稍一看,便知是自己手头的那一块,倒也不见惊慌之色,只是冷了嗓子道:“这等为一己之私而累及百姓江山的事,我不觉得哪里有趣。”
“至少对你来说,它是有趣的。”他支着颊,偏了脸笑问:“你想救云雁落不是吗?”
“我一定会救他,但不会用到这个。郝崖一役,多少人丧生,皇后必须为她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那雪帕上绣得便是皇后的亲笔通敌文书,连玺印也是落下了。
她只需要将它交给圣上,一切就都结束了。
“云雁落我一定会救,皇后也一定得受到惩罚。”这就是她思考多日得来的结论。
“你还有别的方法吗?”濯雨不以为意地摇摇头,“如果你坚持不走皇后那头,那除了公开云雁落的身份也没有其他出路了。”
“你知道!”她大吃一惊,看那人却是一脸平静,像是知道许久。
“别当我们是傻瓜。他那张脸是骗不了人的,虽不是十分,也有七八分的像,再花些心思推敲,那是猜得出来的。只怕,父皇,要等的就是这一天吧!”他道,看她一脸见到鬼的模样,忍不住笑出了声,“我可是圣上亲出之子,他的心思,多少是摸的透的。”
“方法也一定会有的!”
他再度摇头叹气,为她的固执,“其实这案子真相你我都是心知肚明。除了最后的你,那孩子是片刻都没离开过雪嫔。若是你不想事情最后的发展到你我都不可掌控的地步,听我一句,逼皇后交出雪嫔。”
他拍了拍她的肩,起了身。
“你来,其实是要告诉我这一桩吗?”她抬了头,攥紧了他递还的雪帕。
“你可以认为,我也不想这么多年的努力瞬间就成了泡影。”他停步,略偏过脸,应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云雁落若是当真上了位,碧天王朝的历史可能就要到此为止了。”
那个云雁落应该远远不止他们现在所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