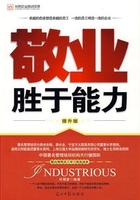“惠妃。”德妃一身暗色裳,还加了紫布红纱的斗篷在外遮掩,夜间没有人会认得她就是德妃娘娘。
“德妃,什麼事闹得这麼晚啊?”惠妃打着呵欠坐下,乐芸為她奉茶,德妃说:“惠妃,我越想事情越不可做。”
就知她是胆小,惠妃心里不悄地骂她,但表面没有流露:“乐芸!”她厉色表现在乐芸身上:“你这死丫头是怎麼办事的?德妃娘娘都来了这麼久,怎麼都没上茶呢?传出去人家可得说我这宫里的人没规矩,连奉个茶的差事都不会办。”
“奴婢知错,奴婢请娘娘恕罪,奴婢这就去為德妃娘娘奉茶。”
德妃本来的不安,因為惠妃叁两句的厉骂倒镇定了下来,她知道惠妃是借骂乐芸在说她。清清喉音,坐了下来:“惠妃,不就是一杯茶嘛,这大半夜的,生这麼大的气做啥?乐芸,随便给我来杯水,省得晚上吃茶睡不着。”
乐芸暗暗瞅了一眼惠妃,只见她眼色有应准的意思,便朝德妃应了声:“喳。”到外边去了。
惠妃默不作声,兀自吃茶,等着德妃道来。德妃眼见身边没甚闲人,也没敢抬高声音,低沉地说:“惠妃,这会儿你还能睡得稳哪?那件事情我们到底该怎麼办啊?我听说她也来找过你了?”
“嗯。”她轻轻应了一声,凤眼尾挑,目光锐气绽放:“那又怎麼样?就凭她?咱们可是两个妃,你这麼瞎折腾,让别人看笑话。自古我还没听说有哪个妃子怕贵人的,她是贵人,不是贵妃!”
“我也不是怕她,可她真是太精了,怎麼一个转头就晓得我和你是同一伙的?说得她好像什麼都知道。”
“她可不是什麼都知道嘛。”惠妃故意这样说,看着德妃瞬间变色的脸,心中愈发觉得好笑。难怪齐宣会先去找她,德妃确是比较容易唬弄。不过她也同意德妃的话,齐宣确是比她们想像中的聪明得多。才是几日的工夫?她们之间的事情别人都不知道,连一向堪称顺风耳的宜妃都被蒙在鼓里,丝毫没有什麼夹针带刺的话传出,这齐宣倒是捕得了风也捉到了影。
“德妃,你看你脸色都变了,安心了。她就只不过是小鸡肚肠,玩些小手段,成不了什麼大事。她就跟宜妃一个样,德妃,你别说我不提醒你,你要再这麼磨咕,本来密不透风的墙也被你捣了一个大窟窿。”
“德妃,你这话是在怪我吗?”她心中真有气不打一处来,现在正受不了这些讽刺的话:“我也是為了大家好,这件事情一个万一都不能有,只要被人逮到一点痛处,我们大家都得玩完。”
“你知道还这麼晚来我宫里?”惠妃也和不她客气,什麼叫笼里鸡作反,现在就是--惠妃虽然刻压低声音,但咄咄逼人的气势却丝毫未减:“你是為了大家好,就应该安心呆在宫里睡觉,我们依旧按计划行事。你今晚来,还没行事就被你漏了风声,坏了大事。”
“我不干了。”德妃重重地说,她越来越觉得这件事情难以控制,事情涉及的人太重要,都怪自己当天想得太好,顾虑不周。
“你不干?”惠妃阴森森地压下眼脸:“德妃,你以為你现在抽身,将来就可以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全身而退吗?你与我共同谋事,共同在苏麻喇姑面前做了一场戏,你以為,最终皇上洞愁此事,会把你给赦免了?”
心中一凛,她所说的正是自己所担忧的,但及时醒来总好过糊涂到底:“我会向皇上解释,多年的夫妻情份,皇上…”
“你中途退出,却不向苏麻喇姑通风报信,也不制止此事,这比参与其中更為可恶!你觉得万岁爷会看不懂你的心思?德妃,我告诉你,即使皇上心软放过你,我也有办法把你拖下去,让皇上饶不得你!”惠妃终于露出发狠的一面,她在宫中多年强横势力,靠得就是一个狠字。谁叫她当年基于庶妃身份,所生儿子不及赫舍里氏的胤礽高贵,虽是大阿哥,却与太子之位无缘。正因為这个,她一直心生不愤,一直在蓄势待发,誓要為儿子夺得储君之位。任何阻她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常这也是為何后期康煕后宫佳丽如此多,能封妃者却是廖廖可数几人。除却一个后来居上的良妃,基本都是同期之人。惠妃当年失策,良妃是一个例外,齐宣万不能成為第二个例外。
“惠妃,你也太恶毒了!”
“德妃,你也太谦让了,上次逼宫之事,你以為我看不出来?你只是借荣妃之手办事,你巴不得齐贵人早早地鹤飞西天,却又不原自己出面。德妃,本宫可不像荣妃那般好哄,你和我相处多年,应该明白这个理。”
“惠妃,事情已经这样了,你為什麼就不放手呢?”德妃见硬碰不得,便软下声来好声相劝:“我觉得那齐贵人知道的事情真不少,她可能早就对十二阿哥的事情了如指掌,我们何必还要去冒这个险?这件事情当年皇上既然压住了,就是不想让人知道,齐贵人怎会不知?将来到了皇上那儿,她也占尽了便宜,对我们没好处。”
“哼!”她笑骂道:“德妃,你知道為什麼,良妃当年都能压住你吗?就是因為你这前门怕贼后门怕鬼的德性。你怎麼就不换个想法?那齐贵人知道这事是正常的,她若不知道,我们就不用费这份心了。”
德妃拢起了眉心,未能完全明白惠妃的意思。
“你想想,如果她什麼都不知道,证明只不过是个绣花枕头,皇上贪她美丽年轻,没别的意思,那咱们也不用费什麼心思去对付她。可她知道的事情越多,对我们而言就越危险,这个人肯定是不能生存在宫里。皇上是想捂着这事不错,有失体统。可正因為如此,齐贵人还敢把它抖出来,这不正好犯了皇上的大忌?”
“你确定那何草儿会乖乖地听话?”
“本宫不像良妃,好好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今晚云泥淡影,霁分星斗,风声静雷声消,凉凉夜意入轩窗,床上枕簟闲。一灯明来照伊人,起看天地色凄凉。
“主子,你睡会儿吧?”红梅不知是第几次劝来,齐宣却始终倚在窗前,看月光眼光光。
“红梅,我越想越觉得事情有许多说不通的地方。”
“主子,就算咱们不知道她们真正所想,但至少你把丑话都说在前头,奴婢相信惠妃她们看在万岁爷的面子上,也不至太敢乱来吧。”红梅為心细体贴,见齐宣保持一个坐姿许久,跪下身来為她捶捶脚,以防麻痹。
“德妃我倒有把握,惠妃…则不那麼好说。”
“惠妃在这宫横行惯了,她不服气也是正常的。不过既然主子都能猜到她与此事有关,她该不会还要冒险继续吧?”
齐宣脸色凝重地摇摇头:“这就是我想不通的地方,从那天惠妃的反应看来,她没打算收手。她手头必定握着有人,所以才一点都不慌张。我怕,我是把她给逼紧了,狗急跳墙,她一定按捺不住,要提早行事。”
“那该怎麼办啊?”
“十叁阿哥查得那女子已经不见了,估计是落在她们手里,它日用来指证我。”
“指证你?!”红梅瞪开了双眼,大惊之色:“主子你没有犯错,干嘛要指证你?”
“我没犯错可是犯了人怨,红梅,就像你们在宫里当差。主子做错了,你们要替她扛着,道理是一样的。她们要把这出口之祸卸在我身上,就必定要有一些证据。我只是觉得奇怪,那女子既是要改名隐居,断不会把一条这麼重要的手绢随便献出来给别人看。到底,她们是怎麼发现的呢?”胤禛上次来说,何草儿是救了一个女子之后才失踪的。看来惠妃在此点上没有说谎,乐芸即使真的拾得了手绢与她相识。但相信她断不会对一个陌生女子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如此清楚。
见齐宣陷入沉思,红梅不敢多语,她脑子转不过来,虽然觉得齐宣有理怀疑,但这样一来事情就更显得复杂,越发叫人想不通。
“红梅,去替我看看太子宫里现在有什麼人?”
“四阿哥和十叁阿哥都在。”她快速地回答:“方才我去传夜宵的时候,听得御膳房的师傅们说四阿哥和十叁阿哥都想喝玉米羹,正赶着要做。这味汤,太子兴趣不大,所以夜宵时都不会准备。”
“好。”她挥笔写下数行字句,叫红梅想办法交到他们手中:“随便一个,但是你记住,一定要亲手交到,明白吗?”
“喳!奴婢记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