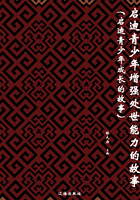他们带着一位看起来很英俊的老绅士和一位右手绑着绷带,相貌堂堂的年轻人前来。天啊,他们一直大声嚷嚷着嘲笑他们。可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而且我想这应该会使公爵和国王的神经为之紧张,他们的脸色应该会转白才是。然而才没有呢,公爵依旧面不改色地继续向四处咯咯地叫喊,看起来既快乐又满足,像个装满牛奶的罐子一般,至于国王嘛,他只是用悲伤的眼神——直看着他们,似乎一想到世界上竟有如此的骗子和无赖存在,就会让他胃痛不已。噢,他实在是装得太像了。许多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围着国王,让他知道他们是站在他那一边的。
而那位刚到的老绅士看起来一睑迷惑,没多久,便开口说话,一听就知道他的口音的确是像个英国人,跟国王的一点都不像,虽然他已经模仿得够好了。我记不起来他说了些什么,也模仿不来,然而他转身面向群众说话,意思大概是这样:“这真是令我意想不到,坦白说,我并没有准备好来面对这样的局面,因为我和我的弟弟路上遭受了一些意外:他的手折断了,而我们的行李在昨晚也因为作业疏失,而被错放在上一个城镇。我是彼德·维特斯的弟弟哈维,这是他的小弟威廉,他听不见,也不能开口说话——甚至连手势也学得不多。现在他只能用一只手来表示。我们的确是彼德的兄弟,在一两天内当我拿到行李之后,我便能向大家证明一切。但是目前我不愿意再多说任何话,只想到旅馆歇息,等待行李运过来。”
于是他们两个便离开了。国王笑着瞎说:“摔断了手——看起来很像一回事,不是吗?——这也太巧了吧,要装个骗子也不先学学手语。行李都丢掉了!这实在是太好了!——真是高招——尤其在现在这种情形下!”
他又笑了起来,其他人也跟着笑,除了三四个之外,也许五六个吧,其中之一就有那位医生,另外一位看起来是很精明的绅土,手里提着一个老式的毡呢箱,他刚从汽船下来,正对着医生低声说着话,不时瞄国王一眼,同时点个头——他是莱维贝尔,也就是那位去路易斯维尔的律师,另外一位是个看起来有点粗鲁的壮汉,他站在那儿听着那位老绅士说话,现在又转而听国王发言。当国王说完话之后,他站了出来,然后问:
“喂,如果你是哈维·维特斯,你是什么时候来这个城镇的?”
“葬礼的前一天啊,我的朋友。”国王说。
“那是几点钟啊?”
“在傍晚——大约太阳下山前的一两个小时。”
“那你是怎么来的呢?”
“我是坐苏珊·宝维尔号从辛辛那提来的。”
“那么那天早上你又为什么会坐着独木舟在品特村上岸呢?”
“我并没有在那天早上从品特村上岸啊。”
“你骗人。”
这时有几个旁观的人走到他面前,求他不要以如此的态度向一位老人和牧师说话。
“去他的牧师,他是个骗子。他那天早上的确在品特村上岸,我不就是住在那儿吗?那天我在那里,他就从那儿上岸的,我亲眼看见,不会错的。他与提姆·柯林斯和一位男孩搭着独木舟来的。”
那医生上前说道:“海因斯,如果你再看见那位男孩,你认得出来吗?”
“我想应该可以吧,虽然我并不太确定。哎,他现在不就在那儿吗?我很确定就是他。”
他指的就是我。
那位医生说:“各位邻居们,我不知道刚来的这两个人是不是骗子,但是如果现在在场的这两位不是骗子的话,那我就是个大白痴。在一切水落石出之前,可别让他们找到机会逃跑了。海因斯,来吧,其他各位也一起来吧,我们带他们到旅馆和刚来的那两位先生对质,我想一定可以问出些什么来的。”
这时群众似乎起了疑心,虽然国王的朋友们也许还认为他是正牌货。于是我们便出发了,这时天已经接近黄昏。医生牵着我向前走,他对我很和善,但是却从不放开我的手。
我们到了旅馆的一个大房间里,点了几根蜡烛,然后把刚来的那两人请了过来。
一开头,医生便说:“我不想对这两位先生太过严苛,但是我想他们是骗子,说不定他们还有一些我们不知道的阴谋呢。如果真的有的话,难道他们不会先带着彼德留下来的那袋金子逃走吗?这听起来是很有可能的。如果这些人不是骗子,他们应该不会反对把这笔钱先交给我们保管,直到他们证明自己的清白吧。大家同意我所说的吗?”
大家都同意医生说的话,我想他们用这一招可把我们压得死死的,但是国王只是面带悲伤地说:
“各位,我真希望这笔钱现在就在这儿,因为我也不想对于这种公开公平的调查有所阻挠,但是天啊,这笔钱现在不在这儿。如果你们不相信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查看。”
“那么钱到底是在哪儿呢?”
“噢,那天我侄女把这笔钱拿来交给我保管的时候,我把它藏在床下的稻草中,因为我们只想在这儿停留几天,所以并不想把它存到银行去,而且我想床铺应该是个安全的地方。我们对这里的黑奴不熟,觉得他们应该像我们在英国的仆役一样诚实才是。可是隔天当我下楼之后,那些黑奴便把钱偷走了。而在他们被我卖走之前,我压根儿都没想到钱被偷了,于是他们便带着那笔钱走了。我的童仆可以为这件事情作证,各位先生。”
那位医生和许多人都说:“骗人!”我想大家也都不全然相信他。有一个人问我是否亲眼看见黑奴把钱偷走,我说没有,但是我看见他们偷偷地从屋里溜出来,快速地离开,而我也没有想太多,以为他们只不过是怕吵醒了我的主人吧。他们就问我这些问题。然后,医生又急急地问我说:“你也是英国人吗?”
我说没错,他和其他人大笑,然后说:“胡说八道。”
他们继续做了些一般性的调查,我们就一直待在那儿,一个小时接着一个小时,大家也都忘了吃晚饭,甚至压根儿都没想到肚子饿——他们只是一直不停地盘问,真是把人都搞糊涂了。他们要国王把他们的身世说出来,同时也要求那位老绅士说出他的生平,除了一些心有偏见的傻子之外,任何人都看得出来那老人说的是实话,而国王则是漫天撒着大谎。他们要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国王用眼睛对我瞄了一下,于是我便开始说着谢菲尔德这个城镇,以及我们在那儿的生活,还有一切关于英国的维特斯家族的点点滴滴的事情,可是我才没说多久,那医生便笑了起来,而莱维律师便说:
“孩子,坐下来吧。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勉强自己胡扯瞎掰。我想你应该不习惯说谎吧,说起来一点都不自然。我想你需要的是练习,你说起来太生疏了。”
我才不管他对我的称赞呢,只是很高兴他们终于放过我了。罗宾逊医生开始说了些话,然后转过身来说:“莱维贝尔,如果你先回到镇上的话——”
国王立刻伸出了手,然后说:“噢,原来你就是我那位死去的可怜大哥常常在信中提到的老朋友啊。”
律师和他握了手,微笑着,看起来很愉快。他们谈了一会儿,然后走到一旁低声地说话,最后律师大声地说:
“就这样吧。我会把你的状纸连同你弟弟的一起带来,到时候就能证明你的清白。”
于是他们拿了些纸和一枝笔,国王坐下来,头歪到一边,舔舔舌头,在纸上写了—些东西,然后他们把笔递给公爵——这次,公爵的脸色看起来很不好,然而他还是拿起笔写了几个字。然后那律师转向新来的老绅士说:
“请你和你的弟弟在这里写上字,并签上你的大名。”那老绅土照做了,可是没有人读得懂他在写什么。那律师看了十分惊讶,然后说:
“噢,我被打败了。”然后从口袋里面掏出一些旧信,照着信件检查那位老先生的笔迹。对完之后说:“这些旧信都是哈维·维特斯写来的,而在这儿我们有他们两个人的笔迹,任何人都看得出来这绝对不是这两个人写的。”(这时,国王和公爵知道自己上了律师的当,露出一脸被骗的蠢样。)“而在这儿是这位老绅士的笔迹,大家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来这些信也不是他写的——事实上他在纸上所写的那些根本称不上是笔迹。这些信是从——”
那个新来的老绅士说:
“请让我解释一下,除了我弟弟威廉之外,没有人能够读得懂我的笔迹——这些信都是他替我重新写过的,所以在这些信上的笔迹是他的,而不是我的。”
“那太好了!”律师说,“这样就好办了,我手边也有一些威廉的信件,如果你叫他写几行的话,我们就可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