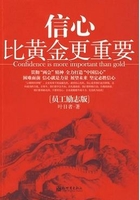你一眼就可以看出格兰洁佛上校是个十足的绅士,他的家人也是如此。据说他出身望族,而一个人的出身背景就和马匹的血统一样重要,就如同道格拉斯夫人说过镇上没有一个人敢否认她出身贵族,而老爸也总是这么说,虽然他自己连当只烂鲶鱼都不够格。格兰洁佛上校长得又高又瘦,皮肤有点黑黑的,一点红润的感觉都没有。他每天早上总是把他那消瘦的脸修整得十分整齐。他的嘴唇很薄,鼻子很小,有着高高的鼻梁,浓浓的眉毛,眼睛更是乌黑有神,深嵌在头颅中。他的前额很高,头发又黑又直地披垂在肩膀上。他的手很长很瘦,每天他都会穿洁白的衬衫和外套,从头到脚一身的雪白,那白皙的光芒亮得会刺伤你的双眼。
每逢星期天,他会换上一套有缝扣的蓝色燕尾服,带着一把银头桃木手杖。他的举止绝对不会有半点不庄重——甚至连讲话的声音也低低的。他实在是好得没话说——你可以感觉得到,而且会对他产生自然的信任感。有时候他会微笑,那笑容看起来真是令人心旷神怡,但是当他直挺挺地像根旗杆站立着,双眼如电时,你准会先爬上树梢,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甚至不需要四处告诫他人的举止——只要有他在,大家准是规规矩矩的。大家也都很喜欢有他在身边的感觉,他总是像和煦的阳光一般——我的意思是说,他使得一切事物都好像晴天一般美好。即使他偶尔晴转多云,也不会持续超过半分钟,而且此后至少一个礼拜都可以保持好天气。
每天早上当他和老妇人下楼来时,全家人都会站起身来跟他们说早安,而且直到他们俩坐下来以后才回座。然后汤姆和鲍伯会在酒柜旁调一杯苦艾酒给他。他会接过来,等着汤姆和鲍伯各自的酒也调好了以后,互相行个礼,听他们说:“爸、妈,敬你!”然后他们会彼此微微鞠躬,接着一饮而尽。这时,鲍伯和汤姆会倒一匙水,加一点糖、一些威士忌和水果酒,递给我和贝克,让我们也向他们二老请安。
鲍伯在家里的排行最大,汤姆次之。他们两个长得既高大又俊俏,有着宽厚的肩膀,两个人都拥有棕色的脸庞、乌黑的长发以及黑亮的双眼。他们也和老人一样,全身都穿着白麻布衫,头上带着巴哈马式的宽边帽。
接下来是夏洛琳小姐。她今年25岁,看起来很高,带点骄傲的神色,但是只要她没有被惹恼的话,她还算是好相处的,可是如果一旦有人惹她生气,她看人的样子就像她老爸一般,令人退避三舍。不过她长得很美丽。
她的妹妹苏菲雅也很漂亮,可是个性却和她不同。她温顺甜美,像只鸽子,而且只有20岁。
他们全家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的黑人侍者——贝克也不例外。侍候我的黑人很轻松,因为我不习惯事事都麻烦别人帮我做。可是贝克的黑奴可就忙得昏头转向的了。
以上呢,就是他们家族成员的状况。其实从前他们家里的人还要更多——本来还有三个儿子,但是都被杀死了,而艾莫琳也已经去世了。
这个老绅士拥有很多田产和超过100名的黑奴,有时候会有一群人从25英里外的地方骑马来拜访,待上个五六天。白天在树林里跳舞野餐,晚上则在屋里举行舞会。他们大部分都是这家人的亲戚,每一个人都配着枪,个个都有着不凡的气质。
这附近还有另外一个贵族——有五六个家庭——大多都姓薛佛森。他们和格兰洁佛家族一样富有、强大,他们两个家族以前是在距离这儿3英里外的地方乘着同一艘汽船登陆的,所以有时候当我和一些同伴去那儿的时候,常会看到许多薛佛森家的人也骑着马在那儿活动。
有一天贝克和我到林里去打猎,听到一匹马朝我们过来,当时我们正要穿过小路。贝克说:
“快点!快躲到树林里!”
我们赶紧溜了进去,从树缝中向外窥看,没多久一位风度翩翩的年轻人骑着马经过,他骑马的样子很熟练,像是一位士兵似的,胸前配着枪。我见过他,他是哈尼·薛佛森。我听见贝克的枪声在我耳边响起,哈尼头上的帽子就这样飞了出去。他立刻拔出他的枪,往我们躲藏的地方冲来,然而我们一刻也不停留地拔腿狂奔出树林。树林并不十分茂密,因此我一边转头往后看,一边小心地闪躲着子弹。我两次看见哈尼的子弹飞过贝克的头顶。后来他就骑着马回去了——我想应该是去捡他的帽子了吧。我们一刻也不停留地跑回家,那老人家的眼睛闪了一下——大概感到欣慰吧——然后他的脸色便和缓了下来,温和地说:“我不喜欢你躲在树林里放冷枪。孩子,你为什么不光明正大地在路上和他决斗呢?”
“爸爸,薛佛森家也不光明正大啊!他们老是占我们的便宜。”
贝克在讲这件事的时候,夏洛琳小姐像个皇后般地昂着头嗤鼻经过。那两个年轻人脸色凝重,但是什么话也不敢说。苏菲雅小姐吓得脸色发白,可是当她知道那年轻人没有受伤的时候,她的脸色才又转好。
后来我拖着贝克到树下的谷槽旁问他:“贝克,你刚刚是不是真的想要杀他?”
“没错,我就是要他死。”
“他对你做过什么吗?”
“他?他什么也没做啊。”
“那你为什么要杀他?”
“没有为什么——这不过是家族恩怨罢了。”
“什么叫家族恩怨啊?”
“唉,你在哪儿长大啊?”你不知道家族恩怨是什么吗?”
“从来没听过——跟我说嘛。”
“好。”贝克说,“家族恩怨就是有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吵架,然后杀了他,那死者的兄弟为了报仇也反过来杀了他,然后双方的兄弟就这样杀来杀去,最后连堂兄表亲也进来搀和一脚。到最后大家都死光了,那家庭恩怨也就结束啦。”可是这中间要花很久的时间呢,有的等啦。”
“那贝克,你们两家的恩怨已经很久了吧?”
“嗯,我想应该是吧!大概是30年前开始,或许更早也说不定呢,好像是为了某件事闹上了法庭,后来输的那一方就站起来一枪把赢的那一方打死了——当然他这么做是很自然的,换成任何人都会一样。”
“贝克,到底是为了什么事呢?——田地吗?”
“我想应该是吧,我不知道。”
“那是谁先开枪的呢?是格兰洁佛还是薛佛森呢?”
“那是法律的问题,我怎么会知道?而且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难道没有人知道吗?”
“噢,有啊,我想老爸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知道吧。但是他们现在也记不清当初是为了什么而吵起来的。”
“贝克,那时候死很多人吗?”
“对啊——举行过很多丧礼呢。但是他们并没有总是杀人,爸爸身体里面还有两三颗大子弹没拿出来呢。可是他说没关系,反正多了这几颗子弹也不会变得太重。鲍伯身上被砍过几刀,汤姆也曾经被伤了一两次。”
“贝克,今年有没有人被杀呢?”
“有啊,双方各死了一个。大概在3个月以前吧,我10岁的堂弟巴德在河的对岸穿过林子的时候,这可怜的家伙,身上竟然什么武器都没带。在一处偏僻的角落,他听见后面有人骑马追来,原来是老包尔迪·薛佛森拿着枪在后面追着,巴德还想他可以逃得开,所以就没有跳入树丛中躲起来。后来他们追了大概8英里左右吧,可是那老头仍然穷追不舍。后来巴德心想反正逃不了了,就停了下来,想跟他正面对决,结果被那老头当场射死。可是那老头也没走运多久,因为不到一个礼拜,他就被我们干掉了。”
“贝克,我觉得那老头是一个懦夫。”
“我觉得他不是懦夫,你这样说不太对。他们薛佛森家族里面是没有懦夫的,一个也没有。当然在格兰洁佛家族里同样也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有一次那老头单挑了三个格兰洁佛家的人,结果最后竟然赢了。他们都骑着马,可是他却跳下来躲在柴堆后面,让他的马在前面挡子弹,而我们的人骑在马上,围着攻击他,当然那老头也回击。最后他和他的马受了伤,一跛一跛地走回去,可是我们的人却要我们去接回来,其中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隔天也过世了。我告诉你,如果有一个人想要找懦夫打架,他绝对不会找薛佛森家的人,因为他们天生就不是那种人。”
下一个礼拜天,我们骑马到距这里有4英里路远的教堂去,大家都带着枪,贝克也不例外。他们把枪夹在膝盖中间,或者是靠在墙边,薛佛森家的人也是一样。讲道的内容千篇一律——都是无聊的东西。可是大家都觉得牧师讲得实在是太棒了,在回家的路上还兴致高昂地说着什么诚信美德、末世和宿命等等我听都听不懂的东西。对我来说,这个星期天算是我所度过的最痛苦的了。
午饭后一个小时,大家都在睡觉,有人睡在椅子上,有人睡在屋子里,真是无聊透了。贝克和他的狗躺在洒满阳光的草地上,睡得很沉。我跑进我们的房间,也想要小睡片刻。我看见了苏菲雅小姐站在她们房门口。她的房间就在我们隔壁。她带我到她的房里,轻轻关上门,问我喜不喜欢她,我说喜欢啊,然后她又问我愿不愿意为她做一些事情,可是千万不能告诉别人,我说好。她说她把她的圣经放在教堂的座位上,夹在两本书之间,忘了拿回来,不知道我肯不肯溜出去帮她拿回来,而且要我替她保守秘密。我回答说没有问题,于是便溜了出去。到了教堂,里面一个人也没有,除了一两只猪会因为教堂门没锁而闯进来之外。夏天的时候,猪喜欢在砖地上睡着,因为比较凉爽。如果你留心的话,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人都只有在非必要时才会去教堂,但猪可就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