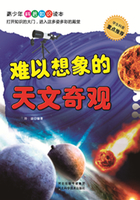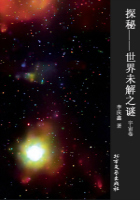过了半分钟,有人从窗里喊了一声:“别叫了!是谁啊?”
我回答:“是我。”
“你是谁?”
“乔治·杰克森,先生。”
“你要干吗?”
“先生,我没有要干吗,我只是要经过这儿,可是狗挡住了我的路。”
“这么晚了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啊?”
“先生,我没有鬼鬼祟祟的啊,我是从汽船上跌下来的。,’
“噢,真的吗?来人啊,把那里的火点起来。你说你的名字叫什么啊?”
“乔治·杰克森,先生。我只是个小孩而已。”
“喂,听好,如果你说的是实话的话,那就犯不着害怕——没有人会伤害你的。但是可别耍花样,站在那儿不要动。你们谁去把鲍伯和汤姆叫起来,顺便把枪拿来。乔治·杰克森,你旁边还有没有别人啊?”
“没有,先生,没有人跟我在一起。”
我听见房里有人走动的声音,灯火也亮了起来。那个人又喊:“把这盏灯拿走,贝西,你这老糊涂——你有没有头脑啊?把它放在前门的后面。鲍伯,如果你跟汤姆都准备好了的话,快各就各位。”
“都好了!”
“好,乔治·杰克森,你认识薛佛森一家人吗?”
“先生,我不认识,我从来都没听过他们。”
“好吧,也许是真的,也许不是。好,现在大家准备好。乔治·杰克森,你向前走过来,注意,不要急急忙忙地——要慢慢地走过来。如果你旁边有人,叫他往后退——他一露脸就会被射杀。好,慢慢走过来,慢慢地,自己把门打开——够你一个人进来就够了,听见没?”
我没有走得很快,因为就算我想也没办法。我一步一步地慢慢走,没发出半点儿声音,大概只听得见我的心跳声在怦怦地响着。那些狗儿也像人一样安静,紧跟在我的后头。当我跨上门前的木阶时,听见他们正开着锁,拿起门栓。我把我的手放在门上,慢慢地往前推,直到有人说:“好啦,够啦。把你的头伸进来。”我照做了,心里想着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把我的头砍下来。
地板上点了一根蜡烛,他们每个人全都盯着我看,我也望着他们,大约有l5分钟之久。三个壮汉拿着枪瞄准我,我吓得倒退一步。他们中年纪最大的那个人满头黑发,大约60岁,其他两个大概三十几岁吧——他们全都长得很不错——还有一个很慈祥的灰发老妇人,她后面站了两个年轻的女子,可是我看不太清楚她们的长相。
那个老年人说:
“嗯,我想应该没事了,进来吧!”
我一进门,那老人立刻把门锁了起来,放下门栓,告诉其他年轻人带着枪走进铺着新地毯的大客厅,聚在一个离前窗很远的角落——房子的两侧并没有窗户。他们拿着蜡烛,从头到脚仔细打量我,然后异口同声地说“他并不是薛佛森家的人嘛——不,他看起来一点都没有薛佛森家的样子。”然后那个老人希望我别介意被搜身,因为他并没有伤害我的意思——只是想要确定罢了,因此他并没有搜我的口袋,只是用手大概摸了一下,然后就说没事了。他叫我放轻松点,并且谈谈关于自己的事,然而这时那老妇人说:
“索尔,这可怜的小东西全身都湿透了,你不觉得他应该也饿坏了吗?”
“你说得对,瑞秋——我倒忘了。”
于是那个老妇人又接着说:
“贝西(这是女黑奴的名字),你去弄点东西给这可怜的孩子吃,要快一点,你们当中去一个人把贝克叫醒,然后跟他说——哦,你已经在这儿了。贝克,带这个小客人去把湿衣服换掉,再拿你干净的衣服给他穿。”
贝克看起来和我一样大,大约十三四岁左右吧,但是他长得比我高一点,只穿着一件衬衣,头发很乱。他边打哈欠边揉着眼睛走过来,手里还拖着一把枪。他说:“薛佛森家的人来了吗?”
他们回答说不过是虚惊一场。
“好。”他说,“如果他们来的话,我想我现在已经抓到一个了。”
他们都大笑,然后鲍伯说:
“像你动作这么慢啊,他们早就把我们都杀光啦,贝克。”
“好,大家不同意也没关系。哼,我每次都只能在后面守着,完全没有机会露脸。”
“别在意啊,贝克,我的好孩子。”那个老人说,“以后会让你露个够的。别生气嘛。去吧,现在照你妈所说的去做吧!”
于是我们一块儿上楼到他房间里,他给我一件他自己的粗布衫、外套和长裤。我赶忙把它们穿上。当我在穿衣服的时候,他问起我的名字,但我还没回话时,他就开始说着他前天在森林中抓到的蓝极鸟和小兔子的事。然后他又问我蜡烛熄灭的时候摩西在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当然也回答不出来。
“那猜猜看嘛!”他说。
“我要怎么猜啊?”我说,“我从来没听过。”
“但还是可以猜啊,很简单啦。”
“哪支蜡烛啊?”我问。
“啊?随便哪支。”
“我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
“它在黑暗里啊,它就是在那儿!”
“唉,如果你知道它在哪儿的话,那你问我干吗?”
“噢,拜托,这是猜谜而已嘛!喂,你要在这里留多久啊?你一定要住下来啊。我们可以每天打猎——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学校了。你养狗吗?我有一只狗——它会跳到河里去把你丢的木片叼回来。你喜欢每个礼拜天都穿得整整齐齐地去教堂做礼拜吗?我可是一点都不喜欢,可是妈妈偏偏要我这样做。这条旧裤子真讨人厌,我可不想穿,热死人了,但还是穿上的好。你好了吗?好吧——走啦!”
他们在楼下替我准备好了冷的玉米面包、腌牛肉、奶油和牛奶。自从我跳船之后,我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食物了。除了已经走开的黑人女佣和另外两个年轻女人之外,贝克和他的妈妈以及其他的人都抽着烟斗。他们一边吸烟一边聊天,而我则一边吃着一边回话。年轻的女人身边都围着毯子,头发披在背上。他们对我问东问西的,我告诉他们爸爸和我们全家人住在阿肯色州南端的一个小农场上,我姊姊玛莉安和人家私奔结婚去了,从此再也没听过她的消息,而比尔跑去找他们,后来也音讯全无,汤姆和摩特死了。全家就只剩下我跟爸爸了。后来因为发生了一些问题,爸爸变得一无所有。而爸爸死了之后,我拿了剩下的东西在河上航行,因为农场并不是属于我们的,后来我就从船上跌下去了,这就是我来到这里的原因。于是他们说只要我愿意把这里当做自己家的话,随便我要住多久都行。这时天已经快亮了,大家都去睡觉了,而我也和贝克一起上床去。当我早上醒来的时候,想起了昨晚的一切,竟然忘记我的名字叫什么了。我在那里躺了一个小时,想要把名字记起来。这时贝克醒了,于是我问:“贝克,你会拼字吗?”
“会。”他说。
“我打赌你一定不会拼我的名字。”我说。
“我打赌你会拼的话,我一定也会拼。”他说。
“好吧。”我说,“你拼拼看。”
“G—o—r—g—e J—a—x—o—n,没错吧?”他说。
“好,”我说,“你真得拼出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拼呢。这名字可不好拼——尤其对一个没读过书的人来说。”
我偷偷地把它记下来,因为也许有人会要我把它拼出来。除此之外,我想要把它记得更熟,到时候如果有人问起的话,我就能够毫不思索地把它拼出来,就好像是我的真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