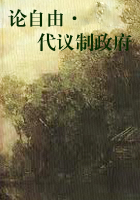君灏天呆了再呆,二十多年来第一次领会千古遗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
还有些佩服这丫的勇气可嘉,敢指着皇帝鼻子大骂她可谓是古今中外第一人了。
生气好笑之余真想抓来某无视他的丫头片子打她三十大板,叫她哭爹喊娘,再跪倒在他脚下哭求无视他的罪过;顺便再敲开她天马行空的脑袋瓜子看看那里面装了什么品种的拖鞋。
丝毫没有想过是她自己骂了阮天赐是奸臣,而他不过是顺嘴一提,给她提个醒。
阮七七用眼睛测量完白绫长度和房梁与地面间的距离,旁若无人认真的把平时玩的几块玉石放在白绫上绑成一个包,掂掂了份量,轻轻一笑。嗖一声,白绫包着玉石穿梁而进,不偏不倚从正梁穿梁而过。
踩在椅子上,把白绫打结,把头放进去还比划了比划。
完全没有生死一线间的危机感,也不知她是仗恃了什么,根本对身边的人不屑一顾。
看到这里,君灏天觉得他要再不懂这丫头是想干吗他就白活这二十几年了。
坐在窗前的桌上,双手环胸,面具下的狭长眼睛眯了眯,顿时觉得刚刚自己真是小瞧这丫头片子了,他收回打她三十大板的决定,决定要看完今天这一出戏,有趣的戏。
同时感叹: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狐狸的女儿点子多。
“你要寻死上吊?”君灏天这回学乖了,没有提及奸臣一话,想要先把小丫头拿下。
“切!姐又不是活腻了,大好河山美男如云还在等着姐陪!这不过是给奸臣老爹一个教训:姐的婚姻姐做主!由不得他卖女求荣!哼!”
本来,阮七七也就那么顺嘴一说,她压根忘记了刚才房内飘然而落的人,口口声声要为她申冤解救她的人,可这话说完了,解气了,她才发觉不对劲了。
“喂!面具男你怎么还在?对了,刚刚的话你要敢对别人说一字,姐叫你十天下不得床!”
狠辣的话一撂,阮七七仍没有去看身后已经快要发火的男人,也根本忘记她自己只不过是个披了十四岁身体的十岁孩子。
站在窗前目测着老爹正屋到她阁楼的距离,预测着轻功的话会用几个起落到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