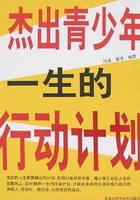钟离睿道:“那厮自幼父母双亡,无人管教,谁料想他成婚之后还是那般放从的性子。唉!”
钟离薇道:“将军今日更是怀疑臣妾对他心存不轨,这让臣妾情何以堪啊!”
钟离睿道:“那厮久经沙场,疑心是重了些,改日朕说说他便是。”
他这么一通插科打诨,钟离薇真的哭了,转而看向太后,泪眼婆娑地道:“太后,您要给臣妾做主啊。”
钟离睿一拍宝座,煞有其事地道:“给你做主,明日我便好好训诫他!这东西,反了他了!”
太后终于忍不住了,轻轻咳了一声,以眼色警告钟离睿立刻闭嘴。张嘴“那厮”闭嘴“这东西”,有哪个君王像他这么说话的?这也就是帝王家,她的儿子又是九五之尊,否则,她一天打他八通都不解气。
钟离睿本来是想从速打发掉钟离薇,此刻眼见无望,就对太后道:“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朕对此有心无力,就烦请母后规劝四郡主吧。”
太后点头,道:“也好,皇上去歇息吧。”
钟离睿想了想,摆手道:“朕还有事要请教母后,等等也无妨。”说完装模作样地低头翻阅奏折。
太后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笑而不语。
钟离薇早已看出钟离睿是有意偏袒寒烨昭,虽然不忿,却也不以为意。她当然晓得,夫妻间的事,任谁也不能把寒烨昭怎样,她此次进宫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得到作为主母应有的权利,从而能够在寒府放开手脚。
太后命人赐座上茶,温声道:“你有什么委屈,慢慢说给我听。”
钟离薇便从成婚那日开始讲起,细说了寒烨昭这些时日以来独断专行无视自己的种种行径,又把这一日的事情从头到尾讲述了一遍,末了,起身拜倒,凝噎道:“臣妾知道将军素来与家父不合,拜堂成亲那日就闹成了天大的笑话,因而也不敢奢望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只想着各尽其职,平静度日。可将军却连这点都不肯成全,使得臣妾在妾室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太后娘娘,若您也觉得臣妾配不上将军,就不如下旨命臣妾与将军和离。”
太后面色一沉,“这是什么话?皇上赐婚,就是要你们和离么?”继而语重心长地道,“烨昭十几岁便随军出征,这几年屡建奇功,你不是不晓得。沙场上的儿郎,心里装着的是天下苍生的安危,对于日常琐事,自然粗枝大叶,你该多担待些才是。”
钟离薇恭声道:“太后娘娘教诲的是,只是,将军的做派臣妾自问无计可施,请太后娘娘恕罪。”说着抹一把泪,“臣妾晓得,不该为家务事进宫,可,可臣妾也实在是万不得已啊太后娘娘。”
太后闻言话锋一转:“你对成婚那日耿耿于怀,原因不外乎是烨昭把你带去的下人撵出了府,今日哀家就给你个恩典,你自己做主挑选些得力之人。有了帮衬你的,诸事就不至于举步维艰了。回去见到烨昭,传哀家的话,让他把性子收敛些,既是成婚之人,就该有个一家之主的样子,日常诸事,你们要商量着来。”
“只是……太后娘娘。”钟离薇飞快地梭了一眼钟离睿,迟疑片刻才道,“将军一直十分看重慕容姨娘,臣妾不知该如何处理此事,对慕容姨娘轻也不是重也不是。”
太后就剜了钟离睿一眼,她这个儿子,连给大臣赏赐妾室都做得出,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钟离睿为之不悦,皱了皱眉道:“这话就不对了吧?朕可是听说,烨昭对那位……就是郡主你带进府、能歌善舞的那一房妾室也很看重,前两日不是还邀请友人一同观赏她的歌舞么?”
“还有这种事?”太后的言语瞬时转为犀利,“往日烨昭就行迹放荡,你是嫌他胡闹得还不够么?慕容氏虽然声名不济,想来倒也不会以丝竹之乐惰其心性。”
钟离薇不由得暗呼糟糕,忙不迭认错:“臣妾知罪,日后定当严加管教言行不检之人。”
“罢了。”太后已无兴致再谈,“今日就到此为止吧,你也不要总是埋怨烨昭,闲时也想想自己有无过失。”
“臣妾告退。”钟离薇行礼退出殿外,走出去很远,才发觉额头已经冒汗。本来应该是有希望得到允许打压慕容蝶舞的,却因了皇上的一句话就失了先机。这个戴姨娘,原本是指望她能帮到自己的,现在才发现,她是一块绊脚石,总在最关键的时候阻碍自己。
沈姨娘见她心神不定,试探着问道:“太后娘娘也不肯为您做主?”
钟离薇想了想,轻松笑道:“倒也不枉此行。先回王府,找几个牢靠的人带回寒府。他说让我回去,我怎么能让他失望呢?”
殿堂里的钟离睿正在献殷勤,道:“其实母后大可不必理会这些琐事,直接打发她回去便是。”
太后道:“烨昭没阻拦她进宫,就是要让我们母子给她个说法,见这一面,日后也就能清净些。”
钟离睿疑惑道:“这厮在搞什么名堂?”
“他能做什么?要么就让她放开手脚和他一较高下,把夫妻情分闹出来;要么就闹得水火不容,分道扬镳落个清净。”太后说到这儿,斜睇钟离睿一眼,“你就不会说些不掉身价的话么?也不知你出宫见的都是些什么人。”
钟离睿尴尬不已,“一时忘形,母后莫怪。”又道,“若如此,趁早写封休书不就结了?也省得宫里宫外都陪着他们胡闹。”
太后抚额叹息,“难为你整日把天家颜面挂在嘴边。既是你金口玉言赐的婚,烨昭又怎能随意休妻?万事总要走完过场才能落得清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