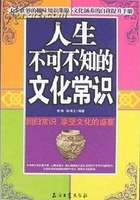过完年回来,又是一轮冲锋陷阵,方圆带着我们大宴宾客。去年请的那些人,有的已升职了,也有的依然在原地踏步,但不管对方升没升,方圆照样热情有加地示意我与阿兰倒酒夹菜,唱歌跳舞。所谓的交情,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培养建立起来的,我相信终有一天,方圆宴请的这些人,会成为某部门的龙头老大,我们好歹也算与他混了个脸熟。
只不过这个世界,向来是吃熟不吃生。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悲观,就算面前歌舞升平,我依然心情暗淡。
新的一年,就这样在我们的吃喝玩乐中拉开了帷幕。方圆不再叫我厉律师,开始叫我厉冰冰,我一直称他为方主任,没有因为他曾经光临过我家,就拉近了彼此的关系。因为我知道,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是一瞬间的感觉,一瞬间的脆弱。
当他不再脆弱时,他自然忘记了那种感觉。
两个月过后,方圆律师事务所接到了市司法局、市律师协会和市法律援助中心联合发出的新一年的法援案件的任务:十二件。我们所里四名执业律师,每人三件,每人比往年多了一件。
大家都知道法援的案件都是白忙活,在经济上没有任何收益,谁也不愿意接手,但由于每个所和每个执业律师都有法援任务,而且还关系到律师事务所的年审问题,所以很多律师都是带着完成任务的心态来接案。很多律师接法援的案件,都是走走过场,应付了事。
三月,法援中心发来一宗案件,我主动请缨,接了这件案子。方圆奇怪地看着我:“你不看清楚这是什么案件再接?”我公事公办地说:“挑肥拣瘦,不是一个好律师。”
他表情夸张地说:“只怕你看了案卷会吓得睡不着觉。”
我说:“那更好,不用睡觉,没日没夜地干活。”
他笑道:“你是一个好员工。”
我说:“你是一个好老板。”
这是一宗杀人案,妻子用菜刀在出租屋里杀死丈夫,然后带着三岁的女儿逃回老家,在途中路遇警察而心虚狂奔,被警察当场截住,交代出杀夫的事实。当警察半信半疑地与出租屋的辖区派出所联系时,凶案现场尚未有人发现,因为出租屋平时根本没有人来。
可以说,这宗案件似乎已没有再做法援的必要,杀人后潜逃,没有自首的环节;而且案发后妻子阿菊明确表示,想杀夫已谋划多时,根本不是误杀。
我一页页地翻看办案部门提供的案卷,现场血流满地的相片触目惊心。到底,心中涌动着多少仇恨,才能让一名妻子向朝夕相处的丈夫举起屠刀?
两天后,经有关部门批准,我成功办理了会见犯罪嫌疑人阿菊的手续。
当阿菊被带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例行公事地表明身份,“王阿菊,我叫厉冰冰,是法援中心给你指派的律师,你涉嫌杀害你丈夫一案由我担任辩护律师,你有什么想说的可以与我说,我会尽力为你辩护。”
也不知道她听清楚我的话没有,她只是呆呆地低垂着眼帘,看都不看我一眼。我提高声调:“王阿菊,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好半天,她才抬起头来:“我不需要律师,直接枪毙我吧。”
我吓了一跳,我见过想方设法减刑的,可没有见过只求早死的,原以为自己担任着天使的角色,对方却巴不得我是勾魂使者,实在有点扫兴。
我耐着性子安抚她:“你应不应该死,不是由你与我决定。再说,你这么坚决要寻死,有没有为家中的亲人考虑过?”
王阿菊抬起头来看着我,冷笑:“亲人?我让他们丢尽了脸,他们根本没当我是女儿,他们巴不得我早死。”
我直视她的眼睛:“你说亲人巴不得你早死,但你被拘留后,三岁的女儿一直由你母亲照顾。你说父母没当你是女儿?你就算不为父母着想,也得为女儿着想。”
她突然激动地站起来:“我女儿?她现在怎样了?她每天晚上都要喝一瓶奶才睡得着,现在她还有没有奶喝?”
我示意她别激动,坐下来。待她稍微平静,我才说:“你不是说只求早死吗?如果你一句话不说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你怎么向女儿和父母交代?全世界只知道你杀了丈夫,却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杀他。”
案卷中,称王阿菊与丈夫关系一直不好,时有争吵。王阿菊因常被丈夫殴打怀恨在心,于是一天深夜趁其熟睡,举刀朝其颈部猛砍,致其大动脉出血过多而死亡。
王阿菊用戴着手铐的双手狠狠地擦了一把眼睛,开始了她的回忆。
那时候的王阿菊,年轻而艳丽,在镇上的小工厂里打工,认识了邻村的男青年。可是男青年的家境很差,父母都是残疾人,如果跟他结婚,连彩礼都给不起。后来由母亲张罗,有人介绍了后来的丈夫阿木与她相亲。
虽然被迫与别人相亲,但王阿菊还是瞒着父母与男友来往,并不小心怀了孕。发现自己怀孕后,王阿菊悄悄告诉母亲。这个时候,她已经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也清楚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现实。
母亲悄悄带她到镇上的卫生院打胎,可是医生给她做了简单的检查后,却说她身体有隐疾,镇上没条件做流产手术,建议她到大医院做手术。但母亲觉得到大医院做手术得花好大一笔钱,就把她带回家了。
恰在这时,相亲后对她念念不忘的阿木再次找上门来,希望与她结婚。于是,在父母的软硬兼施下,她不得不隐瞒了自己已怀孕的事实,与阿木结婚。
婚后六个月,她就生下了女儿。公婆以为是自家的骨肉,对孙女疼爱有加,但阿木知道自己做了顶缸爸爸,怒不可遏,几乎每晚都追问女儿的生父是谁。
抱着好好过日子的心态,她很详细地交代了一切,表示与前男友已全无瓜葛,但丈夫不肯放过她,几乎每天晚上都向她追问与前男友间的细节,有时候边做爱边问,在她的诉说中达到兴奋的顶峰。
但兴奋过后,她必定遭受一次疯狂的殴打,理由是:“谁叫你这么骚,你不这么骚就不会给老子弄个野种回来。”
发展到后来,他一看到父母抱着女儿哄,便把满腔怒火泄向她:“你在外面搞的野种,却要我父母来带,老子不打你就是对不起父母。”
一年前,忍受不了他的殴打,她抱着女儿回了娘家,并决定与阿木离婚。但是父母坚决不许她离婚,说她有错在先,将来为阿木生下一儿半女,他自然不会再打她。等阿木再来接她回家时,她只好流着泪抱着女儿跟阿木回了家。
这次闹离婚事件,就此不了了之。
半年前,痛定思痛,两人带着女儿一起来到这个城市。在老乡的帮助下,他们找到了房子,阿木也顺利进了一家工厂,早出晚归地干活,每月可拿到两千多元,她就带着女儿在家煮饭。一家人似乎抛开了以前的阴影,连女儿都开始敢张着小手叫爸爸抱了。
然而,这种快乐而平淡的日子仅过了一个多月,有一天,阿木在外面喝了酒回来,估计是在上班时受了管理人员的气,回来便朝娘儿俩发火。她唯恐孩子受到伤害,把女儿紧紧地抱在胸前。不料这个动作刺激了他,他猛地冲过来,抓起孩子的手硬扯,眼里闪着凶狠的光:“你还护着这个死野种,总有一天老子弄死她。”吓得女儿哇哇大哭。
从此,他们又恢复了在家乡时的打骂。三岁的女儿已逐渐懂事,他却经常逼她当着女儿的面做苟且之事。有时候女儿看到他压在妈妈的身上,总是吓得跑过来推他,他却哈哈大笑。如果她稍作抗拒,他便劈头盖脸地朝她扇巴掌,有次把她的一颗牙齿都打掉了。
“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如果我不先杀死他,他总有一天会杀死我们母女俩。”王阿菊以这句话结束了她的故事。
我提着笔,叹息。卷宗上一张张满是血污的现场照片,终于有了合理的解释。犹如经历过一场浩劫,我浑身冷汗。
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如此卑微地活着。每个人都只看到他们走出家门后阳光的笑脸,却不知道一旦关上门,每个人都有可能是悲剧的主角。而我,充其量,只是演出了一场角色稍多的情感戏而已,远远未到悲剧的程度。
我朝王阿菊投去同情的目光:“就算你选择离婚,也比现在要好得多。”
她摇摇头:“如果我离婚带女儿回娘家,父母根本不会接纳我们,我带着女儿,连给她提供一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只有杀死阿木,才有女儿的活路,就算我父母不理她,国家也会照顾孤儿。”
我叹息。她思前想后,确实是蓄谋已久,她一心求早死,显然也是希望福利机构收养其女儿。
我说:“就算你真的一心想为女儿好,也不应该放弃主张自己权利的机会,你应该在法庭上把所有的事情说出来,好让亲人知道你的苦衷,也让法官准确地量罪定刑。”
她盯着我看:“杀了人可以不死?”
我纠正她的说法:“死不死不是由你我说了算,你应该从现在起积极配合律师,在法院审理此案时积极配合,一切让法官决定。”稍顿,我说,“我会与你家人联系,开庭时让你母亲带你女儿来见你。”
她双眼顿时放光:“真的可以这样?只要你帮我,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
我正色道:“你不是帮我,你是帮自己,帮你的女儿,帮你的亲人,你应该不想只见女儿最后一面吧?”
她点点头:“我希望有一天,可以看到女儿结婚,生孩子,我将来老了,可以为她带孩子。”
临走时,她一双被铐住的手向我不停地作揖,我只感觉悲伤无比,速速离开。
回到所里,已是傍晚。我叫了个快餐,速速吃完,然后继续看王阿菊的案卷。直到被房门敲击发出的响声惊动,才发现方圆站在门口。
“还在刻苦攻关?”他问我。
我说:“是,想理顺条理,为王阿菊写一份辩护词。”
方圆奇怪地问:“王阿菊是谁?为何我全无印象?”
我说:“就是那宗法援的案件。”
他恍然大悟道:“你今天做到这么晚,就是为了这件案子?”
我说:“是,我还打算明天与其家人联系,劝说其家人参加庭审,给她更多的信心。”
方圆奇怪地看着我问:“你是从法援中心出来的,难道你不知道,这类案件大家并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