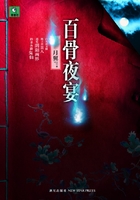我默默地看着局长的车顶,想起第一次来司法局的情景。
他是我的恩人,可惜此刻,他是另一个女人的仇人。而且,这个女人手握重兵。
一个手握重兵的女人若立志要你死,你唯一的选择,是非死不可。
我跑到局长办公室去,无论如何,我应该为他分忧。
推开门,我看到一张焦虑的脸。“局长……”我欲言又止。
他看出我的不安,问:“你知道了?”
我点头,说:“是。”
他叹气。在一个女下属面前,他现在确实不知道说什么。
我缓缓地说:“你可以劝劝她,看有没有回旋的余地。”
局长说:“我昨天深夜回来,她根本不让我进家门,楼下的垃圾箱里,扔满了我的衣服。打她电话,根本不听。”
我叹气,说:“这个时候,找第三方出来劝她,会比较好些。”
局长抬头看我:“你有办法?”
我说:“我有个朋友,是妇联主席。”
局长说:“你可以叫她出面劝说一下?”
我说:“好的。”胸中便陡然涌起一股使命感。我看到局长的眼中,有希望的光芒。
当我打开门欲走出门口的时候,局长在背后叫我。我回头看他。他说:“冰冰,不管此事成不成,我都要感谢你。”
我苦笑摇头,因为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彼时,最高人民法院刚通过并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对包二奶行为从重从严打击,我们省内各级妇联的信访部门据说门庭若市。
如果处理不好,局长将成为我市因包二奶而落马的第一人。
不是所有的第一名,都意味着鲜花和掌声,出头的鸟儿,注定会挨枪子。
本来,像这样的案例,根本无须娜亲力亲为,但为了帮助好朋友,她很乐意与我一起跑去找局长夫人。
傍晚时分,我与娜走进局长的家。妇联进户家访也是常事,电话联系的时候,局长夫人很爽快地对娜表示欢迎。
看到我,局长夫人稍有一点愕然。她认识我,每年的单位春节聚会,局长都会带家属出席,吃饭唱歌抽奖,那是相当热闹的场面。更何况,她的女儿曾跟着我实习数月,估计她对我已相当熟悉。
以往的见面,她对我很热情,比对司法局那些老牌美女还要热情,因为我的外貌,确实长得与世无争。
姿色平庸的女人,也是有优势的,或许她不易得到异性的青睐,但她会因为缺乏攻击力而更容易获得同性的好感。
看着她不解的目光,我连忙解释:“我与娜主席是好朋友,知道她来探望你,我也陪着来看看,看有什么帮得上忙的。”
娜也在一边帮腔,局长夫人的脸色缓和下来。她恢复正常,热情地招呼我们喝茶。
娜遵循妇联一贯的调解原则,劝和不劝分,希望局长夫人能再考虑,让局长浪子回头,继续过幸福的婚姻生活。这也是我的目的。可是局长夫人毫不犹豫:“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后,我不可能与他再在一起了。”
娜谆谆诱导:“你家局长也是一念之差,你就给他次机会吧,再说你们的孩子都大学毕业了。”
局长夫人深恶痛绝地说:“他绝不是一念之差,他是处心积虑,他能够在我眼皮底下养一个‘北妹’,以后说不定还会干出什么令人绝望的事。我与他在一起,当年也是受过很多苦才好不容易盼到今天的,我对这个人真的绝望了。”说到后来,她几度哽咽,泪水横流。
我心有不忍,抽出纸巾给她擦泪,好言相劝:“来之前,局长已向我表示与‘北妹’断绝来往,不会再做伤你心的事。”这是我的临时发挥,其实一个男人根本不会对属下这样说。
纵然悲泪长流,局长夫人仍然相当坚决:“他已破坏了我对感情的信任,他必须付出代价,我不但要离婚,还一定要让他坐牢。”
我默然。
一个对感情坚定执著的女性,是值得敬重的。我理解她的选择。
因为重婚罪是刑事自诉案件,一般来说,民不告,官不究,但因为局长夫人坚持要告局长,所以局长很不幸地成为我所在城市第一宗包二奶案的被告。
堂堂一个司法局长,竟然涉嫌重婚罪,这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
局长夫人向法庭递交了局长的存折为证据,上面打印有为“北妹”发廊交费的记录,还有小区发廊周围一些群众的证言,证实“北妹”曾经向人介绍局长是她“老公”。
你说这个“北妹”,叫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学人叫老公?这是我当时极为不解的一件事。后来,当我出来闯荡江湖后,有个男性朋友告诉我,桑拿房里出来的女子,都喜欢把恩客称为老公。
天,这个老公当得可真亏,花钱侮辱自己。建议男性朋友以后与失足妇女谈心时,除了做好安全措施外,还要看管好她们的嘴巴,不然,惹上官司可不是好玩的。
因为证据确凿,局长被判重婚罪,获刑两年,缓期两年执行。
也就是说,判了等于没判。可局长夫人还再走上访之路,誓要把局长拉下马。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古怪,有时候法律解决不了的问题,政府可以解决,但政府解决不了的问题,法律一定也解决不了。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找政府靠谱得多。
二十多年地往上爬,两个月足以把他拉下马。在局长夫人的努力上访下,局长很顺利地被开除公职。
如果说,之前局长还对家庭有点不舍之情,但从他被开除的那一刻起,他与夫人便成了仇敌。作为有过错方,离婚时局长可说是净身出户。
心灰意冷的局长什么也没要,就离开了司法局。
我记得,局长宽敞的办公室里,安放着他从各地搜集回来的石头和茶叶,他曾经对这些东西视若珍宝,有人出高价都坚决不肯转让。如今他全部不要,显然是绝望到了极点。
一个连心爱之物都放弃的人,必是心如死灰。
尽管司机再三请求开车送局长离开,但他坚决拒绝了。
看着局长缓缓离开司法局的身影,我黯然泪下。或许,这个结果是他没想过的,但自己种下的恶果,必须自己承受。
终于,我忍不住致电吴明,说晚上想见他。
他颇为为难:“我今晚有个饭局,未知几点才有空。”
我说:“那你吃饭后方便致电我吗?”
他说:“好,饭后我立即想办法脱身,出来找你。”
其实,我也没想做什么,只是想见一下他。
伤感的时候,我渴望有一个坚厚的胸膛,可供我依靠。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我的一时之兴,给这段感情画上了休止符。只能说,一切都是命。
晚上九时多,吴明致电我。约了来司法局门口等我。
我上了车,他回头看我:“找我这么急,有重要的事?”
我说:“也没有,只是想见一见你,与你说一会儿话。”
他说:“那随便找个地方散下步?”
我说:“不如到市政府的后花园去?那里的夜合,正是这个季节开花,很香很香。”
他迟疑了一下:“这样好吗?市政府很多人认得我。”
我说:“不要紧,晚上那里很静,没有什么人去的,我以前晚上常去那里散步。”
他爽快地说:“那听你的。”
到了市政府的后花园,我才发现,隔壁的迎宾馆被拆除后,这里正在建商贸广场,工人正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连夜施工。整个市政府的后花园,被建筑工地的灯光照得如同白昼。
尽管这里的夜合依然芬芳,却已非当年那幽静而令我沉迷的梦中故园了。
我有点扫兴,解释说:“以前这里不是这样的,还有,这里的花很香。”说着,我跳下车,跑到夜合旁边,摘了一朵花,放在他的鼻子上给他闻,“你说是不是很香。”
他装作陶醉的样子猛嗅:“果然好香啊。”边嗅边往我耳边嗅。我喜欢他痴缠的样子,情不自禁把头伏在他胸前。
兴致勃发的他,干脆跑去夜合丛中,摘了一大捧花给我:“你养在瓶子中,今晚一定可以睡个好觉。”
无论什么时候,他总知道我在想什么,举手之间便可以给我喜悦。我接过夜合花,默默地嗅它们的香味。
这是他最后一次送花给我,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很多事情,我们重视的往往是第一次,殊不知最应珍惜的应该是最后一次,因为开始可以策划,结束却毫无预兆。唯有珍惜每一次,才不会有此遗憾。
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谈情说爱,未免有点扫兴。我悻悻地对吴明说:“不如回去了,以后再来。”吴明点头。我们两人一前一后地往他车子停放的地方走去。
走近车辆停放处的时候,一辆小车驶近,刺眼的车灯令我不由自主地眯上眼睛,待我定睛再看,那车灯依然在照着我。我有点不快地上了车,吴明却在旁边说:“难道我遇上熟人了?”
我说:“不会,如果是熟人看到你与一个女人在一起,他会悄悄地熄火免得惊动你,大家都尴尬。”
吴明赞许地笑:“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人。”
我回他:“能让最聪明的女人喜欢的男人,想必也不简单。”
他大乐,驱车离开。
我没有想到的是,车上的人并非吴明的熟人,却是我的熟人。车子刚驶出市政府大门,我手机响了。打开一看,一个似曾相识的号码。接听,是林的声音。
他说:“你在哪里?”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你在哪里?”
我没好气地说:“你是谁?我在哪里关你什么事?”
他再说:“你告诉我,你在哪里?”
我大怒:“你以为你是谁?我在哪里关你什么事?”
恨恨地,我关掉了手机。他已有了别的女人,他凭什么追问我在哪里?每次都是他随便地离开我,再随便地找我,他凭什么?
一个女人爱你的时候,你是天,你是地,你是唯一的神话,可惜这个女人不再爱你时,你将失去特权,堕入凡尘成俗子。
吴明偏头看我:“是什么人让你如此生气?”
我犹自生气:“不认识的!”
他依然好脾气地笑:“不认识的人能让你如此生气?”
我沉默半晌,说:“是以前的男朋友。”
他说:“分手了还打电话,说明还关心你,你又何至于如此生气?”
我说:“如果还关心我,他当初就不会分手。”
吴明摇摇头:“不是这样的,男人与女人想法不一样。他找你不一定会有什么目的,或者只是突然忆起当年一些美好的细节,想与你说说话。对于曾经爱过的女人,男人都有放不下的情结。”
我不语。
他把手伸过来,握着我的手说:“可以好好说的话,没有必要恶声恶气说的。”
我任他握着,说:“是。”这道理谁不懂,只是怒火上头,恣意发泄而已。
心中漫过一股悲凉。他连我的前男友找我,都不以为意,反而鼓励我好好与他说话。虽然,他这样的做法很有风度,但是,我不喜欢这样的风度。
我宁愿他气急败坏地抢我的电话看,发疯地追问:“这个人是谁?为什么他会打电话给你,你是不是还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