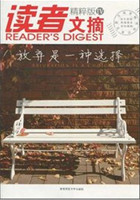夜深,贵宾陆续归来。有的微笑,有的深沉。我诚惶诚恐地站在电梯口,半弯着腰指引他们往各自的方向。
直到凌晨,整个迎宾楼的客房部都静下来了。值班的女服务员说要走开一下,让我坐在总台前守夜。我知道,她是要到值班室睡觉了。我说好。反正也就是一宿而已,明天搞完活动,嘉宾退房,我就离开这里了,一夜不睡没有什么关系!
拿过一张不知道谁扔在总台桌子上的旧报纸,我认认真真地看起来。不知过了多久,大厅的门被推开,两个人摇摇晃晃地走进来。
女的很漂亮,头发很漂亮,衣服很漂亮,鞋子袋子,从上到下,都很漂亮。男的瘦高,穿着西装,看得出平时是养尊处优之人。可是此刻,两人浑身酒气,女的老是像要跌倒的样子,男的欲要扶着她走,可是又自顾不暇。
我冲出来,扶着女的,问:“你们住哪间房?”
男的拿出钥匙牌,608。
我把女的扶进电梯,那女的突然忍不住,吐了一地,抱着那男的大哭。小小的电梯间,顿时脏臭异常。人类制造的垃圾,远比动物的排泄物要臭得多。我宁愿回家搬一天猪粪,也不要闻这腥臭的酒味。我强忍恶心,紧紧地扶着那女的。
扶着那女的进了房间,她突然大哭起来,披头散发,满身酒气。再美丽的女人,也经不起如此折腾。后来,当我正式踏进社交圈后,坚决不肯喝醉,只因为看过美丽的女人喝醉后会如此不堪。
我不忍马上离去,拿来热毛巾,帮那女的抹干净脸和头发,再用房间里的浴衣帮她换上,处理干净地板上的污秽物。后来又为他们泡了两杯茶,提醒他们喝了,我才离开。
处理完电梯间的污秽物,我听到厨房的开水炉已经响起来了。饭店的餐饮师傅们上班,开始准备嘉宾的早餐了。
当外面终于亮起来,声称“走开一会儿”的女服务员精神抖擞地回到了总台,朝着一夜未睡的我笑,问我困不困。在我笑着说不困时,我看见昨晚的醉男走了过来,意气风发,与昨晚的颓废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我旁边的女服务员马上如弹簧般“弹”起来,恭恭敬敬地向他请安。而他对我们却视而不见,扬长而去。
下午,我百无聊赖地坐在总台前看报纸。当天有精彩的花车巡游,客人跑到外面看热闹了,他们要吃了晚饭后才回客房部。我盘算着当天晚上,拿了劳务费后到同学家过一夜,第二天再回村子去。
因为数理化学得不好,我高考的成绩不怎么理想,家里人正盘算着让我到外面打工,妈妈还打算求阿红介绍我到省城的鞋厂打工。
总之,我感觉自己将有崭新的开始了,虽然这样的开始在今天看来很可笑,但在当时的我以及我的父母看来,也算是“前途”。任何工作,都比在农村种田有前途得多。
晚饭时间将到时,有人走进大堂,用手轻轻地碰我:“你出来一下。”
我抬头一看,一个陌生男人,年轻,很有精神的样子。
走出门外,环视四下无人,他说:“昨晚的事,你不要乱说,不然没好下场。”
昨晚的事?他还说:“××书记不会亏待你的。”我“哦”了一声,想起那个醉男。
陌生男人接着说:“××书记问你有什么困难,他可以帮你。”我脱口而出:“我想到迎宾馆上班。”
陌生男人笑了一下:“就这样?”我慌忙说:“是的是的,我真的很想在这里工作。”
于是,当天晚上,我没有离开迎宾馆,反而搬进了迎宾馆的女工宿舍。后来在迎宾馆当服务员的几年间,不断有人说我“后台硬”,我从来不解释,也不辩驳。
越是沉默,别人便以为你后台够硬,越以为你有故事。
有时候,沉默也是一种武器,沉默得越久,越有力量。所以我在迎宾馆的几年间,没人敢欺负我,就算是迎宾馆里最牛的餐饮部长,也对我谦和有礼。
就算是父母,问我如何得到这份工作时,我都是含糊地说是同学介绍的。我怕老实巴交的父母在向邻居炫耀时,不小心说出来。任何有可能影响自己的话,都不要轻易张开嘴巴。很奇怪,我似乎很小就懂得这个道理,而有很多人,活到老都不懂得管好自己的嘴巴。
其实在当时,我根本不认识××书记,也不认识那个喝醉了的美丽女人。直到后来,我成为迎宾馆的女服务员后,才从当地的电视新闻上得知,那女的是电视台的主持人,男的是市委副书记。
当然,我们习惯把副书记也称为书记。其实,书记完全可以叫迎宾馆的人立即叫我走,因为我本身就是临时工,但他却派人把我办成了迎宾馆的正式工。
你知道迎宾馆的正式工意味着什么吗?迎宾馆是政府开办的,正式的员工是有国家事业单位编制的职工,每月工资八百多元,逢年过节有礼品。而没有编制的服务员,一个月工资仅为四百多元,逢年过节的礼品也只是正式员工的一半。
我从一个临聘人员突然变成有编制的职工,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当天晚上,当客房部的部长带着我到女工宿舍选床位时,我的嘴巴一直忍不住笑,完全无法控制自己的表情。
那是我人生中最开心的一刻。后来,当我拥有更多的东西时,都再没有那样的惊喜过。人,得到的越多,越难体会到满足和快乐。
这是一九九三年的事了。
后来,那位副书记当上了书记,后来又因种种原因成为阶下囚。很多年以后,当我与一位资深法官谈论起他的这宗案件时,感触良多,忍不住第一次与别人说起这件往事。
就算他是大贪官,就算他是大罪人,但在当年,他确实拯救了我,给了我一根绳子,让我有机会从农村的深井中爬了出来。
有时候我想,如果当天晚上我没有出手帮书记,若无其事地装作看不见,结果会是怎样?
又,如果我没有得到书记的格外关照而留在迎宾馆,而是在父母的张罗下最终到省城的鞋厂打工了,我会是今天的我吗?
或许,我会在鞋厂里认识一个打工仔,然后跟着他回到他天南或地北的家,安心务农,也未必不比现在开心。反正人这一辈子,总免不了营营役役,不是在这里,就是在那里。
在迎宾馆我当了三年的服务员,三年之后,我成为司法局的一名职工。但这次,并没有人因为喝醉了酒而关照我,而是我无意中努力的结果。
我说过,我长相不美,任何工作上得到的便利,与我的性别完全无关。后来,先后有不同的男人欣赏我,也只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而非姿色。
一个女人这样说,似乎是值得骄傲的,但在我看来,这是一件尴尬的事。我宁愿是因为我漂亮,男人才爱我宠我,我不介意去当花瓶。
若男人赞你聪明,你千万要提防。因为你聪明,所以你无须被照顾,相反,他们要麻烦你,他们要向你求助,让你为他解决麻烦。如果可以,女人一定要当花瓶。当了花瓶,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插花了,花枝招展地不务正业。
而我,因为当不了花瓶,只好像男人一样正襟危坐,与男人隔着桌子谈法律和国家大事,可在我心底,其实更希望能穿着修身长裙坐在他们的大腿上谈情说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