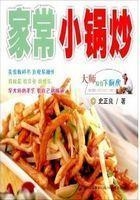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自作聪明的人,有自知之明的人,仅是少数。但凡自作聪明之人,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特别自信,特别偏执,你必须向他俯首称臣,他才可能给你机会。你若试图与之理论,在其看来简直死不足惜。
我不介意俯首称臣,哪一个造反成功的皇帝,不是从臣开始的?当过臣的人,可以很好地当皇帝,但有几个皇帝可以当臣的?
现在,我学会电脑了,办公室所有的资料,打印也罢,修改也罢,校对也罢,统统交给我,然后由我拿到电脑房,安排阿玉做。
猛然间,我俨然成了阿玉的上司。就连局长需要打印什么材料,也是直接叫我,把想法与我说,提都不提阿玉,也不到电脑房去了。
对一个机关单位来说,一把手不重视某个科室,说明这个科室已经没什么江湖地位了,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失去了竞争力。
过去,电脑房虽然没有什么级别,但好歹局长重视,无人敢轻视,现在局长连看都不看一眼,下面的人又都是跟红顶白之辈,阿玉的身份在单位突然一落千丈。比如,以前财务会计代发市政府的补贴,会直接送到电脑房请阿玉签收,现在只会打个电话到电脑房,通知她到财会室签领。
阿玉终于意识到,一切的改变,全因我入侵电脑房,但为时已晚。
所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能力牵制住徒弟,最好还是对她留一手的好,不然终有一天让她抢走地盘,自己反成孤家寡人。
某天,在每月例行一次的全局会议上,局长表扬了我。
局长是行伍出身,虽然没什么文化,听说才初中毕业,但回到地方后上过几年党校,现在的学历是大学本科,保养得白白胖胖,看上去还是挺有文化的。
在作总结讲话时,局长说:“司法局是一个重视人才、开发人才的地方,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进步。”然后,他环视全场,威严地说:“有些新来的同志,利用业余时间学会了电脑,让办公室的工作效率大为提高,这种积极的劲头是值得全局学习的,那些十几年没进步的同志应该引起反思!”
积极的同志,自然是指我了,不积极的同志,有可能是老赵,也有可能是老伍、老陆,阿玉也有可能,总之是泛指,个个均可对号入座。
在这种情况下,局长表扬我,显然是在捧杀我。凭什么你表现得这么先进,反衬出我们的落后?
会后,大家回到办公室,老赵大声说:“后生可畏啊!”
美姐说:“我们老了!”
黄黄说:“向冰冰学习。”
唯有李立,他鼓励地看我,“局长表扬冰冰,是我们办公室的好事。”
可是好事当前,其他的人竟然貌似心情都很不好啊!
就连阿玉,面对我也像结了一层冰。
我拿资料到电脑房,如果我不先叫她,她是不会理我的,如果我叫她,她会应一声,但再无二话,好像我欠了她五百块钱不肯还一样。
虽然没人骂我,但我感觉比让人打了一顿更难受。
这是我到司法局以来,最难过的一件事。
晚上我打电话给娜,哭诉此事。娜听了,笑道:“这也叫事?”
我气结:“这还不叫事?现在人人对我有看法,认为我只会在领导面前邀功,他们认为自己干了那么多活局长都不表扬,反而表扬我,他们生我的气……”
娜一字一句地说:“一把手说你好就好,其他的人你不用理会。”
我伤心,“可是他们不喜欢我。”
娜笑,“你伤心,他们就会喜欢你了?这个世界的人千千万万,你哪讨好得了这么多?”
我还是觉得不妥,娜懒得与我纠缠,没好气地说:“一把手说你好,你就好,别人,都是听一把手的。只要你对每个人客客气气,装作不知道他们不喜欢你,慢慢就会没事。”
娜又说:“过两天风平浪静,你想起现在的苦恼,会觉得现在的担心完全没有必要。如果我像你这么怕事,早回家种田了。”
想想也是,人家在市政府闹出那么大的桃色新闻,还搭上了主任一条命,现在还不是安然无恙地为市政府的接待事业贡献青春和智慧?
趁我无言以对,娜接着悄悄告诉我:“我可能过段时间到市妇联上班了,你千万不要与人说,等一切定了才可以公布。”
我心中又莫名其妙地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她连字都写不好,凭什么到妇联上班?突然,我觉得自己像个小人,人家刚才还在尽心尽力地帮我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现在我却忌妒人家的进步。
女人,你可否大方一点?这么多陌生人飞黄腾达你不介意,却忌妒好朋友的心想事成!
虽知众人不喜欢我,但我依然像平日一样,出入自如,该打招呼就打招呼,就算别人冷脸,我也笑脸相迎,恍若无事。
但凡需要打印资料的,我主动伸手帮人,其他科室的人受我几次帮,渐渐开始与我讲话,聊生活琐事。我似全然不知阿玉生我气,有时主动拿零食与她分享,有时帮她做些校对。反正也没什么血海深仇,于是,僵局慢慢化解。
想起数日前的愁眉深锁,我不禁佩服娜的定力。
我的积极主动,慢慢令李立对我产生好感。在过去,办公室的几尊大佛叫也叫不听,搬也搬不动,现在大佛们虽然不动,但好歹他多了一个帮手,总归是好事,因此他视我为同盟军。
我看见他的眼中,渐渐有了柔和的光,说话的语气,也越来越柔软。
而我,似乎,貌似,挺喜欢他的目光。
有时候,办公室没有其他人的时候,我们便聊些家乡的事。他老家的镇与我相邻,风土人情差不多,就连小时候过节时母亲做的点心,都是一样的。
一天,我偶然说:“我好想吃妈妈做的叶仔糍,又软又糯。”他说:“街上有人卖的。”我说:“我没有吃过街上卖的呢。”他若有所思地说:“哦。”话题到此为止。
次日早上,我到办公室时,拉开桌子的抽屉,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塑料袋,细看,里面装着温软的一团,翠绿可爱的菠萝蜜叶子,清晰可见。
正是叶仔糍。我回头看他,他正好看我,双目相接间,我脸如火烧。
一个男人,唯有欣赏一个女人,才会因为她无意间的一句话,刻意讨她欢心。
我也不问他,慢慢地吃起叶仔糍来。
我一口气吃了三个,尚余两个,放进袋子里,拉上抽屉。我慢慢地想心事,表面不动声色,心里波涛汹涌。
美姐回来,声势浩大地声称送孩子上学,来不及吃早餐,我拉开桌子,拿出余下的叶仔糍给她。她也不问,呼呼地吃起来。
整整一天,我与李立都没有再说一句话。我以为他会有话对我说,但没有,直到傍晚下班,他走出办公室,也没有拿目光与我对视。
我不说,不等于我没有期待。我心中隐隐有些失落。
当确信他真的已经走了,我才伏在桌上,浑身无力地想:人家不过是帮你买了一次早餐而已,你以为代表什么?
有一天,我的目光无意中掠过李立的脸,发现他也在看我,心中一动,说不清的感觉。
但那又如何呢,他有家庭,我也有林,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在对方不察觉的情况下,若有若无地瞟上一眼,多说一句,都是多余的。
除了工作上的事,我们不说其他的话题,也不再提故乡的事。我以为,这是彼此心照不宣。
某天,中午临下班时,李立从局长办公室出来,匆匆告诉我:“中午要准备一份材料给报社和电视台,报道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现在公职律师少,其他律师事务所也不积极参与,法援的官司质量和数量都上不去,局长对这个似乎不甚满意。”
我说:“想把数字做大?但每个律师办的案件数一对应的话,就会有漏洞。”虽然我知道政府部门的统计材料大部分是水分,但我们这里的公职律师才两人,夸得太大反而不妙,但数目太少说出来也有点难为情。
李立问:“那你有什么好办法?”我说:“我认为突出个案比较重要,通过归纳代表性的案件来总结,比较有说服力。这样也可以令人忽略所办案件的数量。”
李立说:“好主意,就这么办。”
时间太急,当天中午,我们干脆把所有的材料都拿进电脑房,两人边商量边确定,最终,我们将案件的类型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未成年人犯罪;第二种,妇女犯罪;第三种,农民犯罪。
因为就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来说,这三种人都是弱势群体,我们将其分类后,不管其类型有多少个个案,通过具体的案件便足以突显出法援工作的重要性。
两个多小时后,材料终于大功告成。我拍拍手,起身跑去启动打印机。
李立突然站起来,叫我:“冰冰……”我答:“嗯?”
他双手环抱我的肩,没有任何过渡。我大惊,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
他说:“我喜欢你,你知道吗?”我没有说话,感觉他的拥抱很紧很紧。他继续说:“我每天早上,想到一来可见到你,心里会很快乐。”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了。
一直就这样抱着,我竟然不抗拒,心中隐有欢喜。
半晌,我才说:“那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他委屈地说:“很久前,我给你买的叶仔糍,你给别人吃……”我哑然失笑:“我吃饱了才分给别人的。”他说:“我以为你讨厌我……”
我笑。他开心地抱着我。我欢喜无比,内心深处,却涌起一股酸酸的感觉,好像实现了期盼已久的心愿。
下午,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到法援中心来,局长与法援中心的主任带着他们在办公大厅里看了一圈,然后进了会议室接受采访。
第二天,本市的报纸上,用整版报道了法援中心的工作,有具体的案例,也有律师的具体操作过程。里面有八成是我的原创,而我的名字跟在记者的名字后面,前缀是通讯员。
局长拿着报纸,兴奋地跑进我们办公室,说:“冰冰,你这份材料写得确实不错。法援中心的人都说你很了解他们的工作,完全可以胜任律师的工作了。”
我受宠若惊,掩饰不住开心道:“是不是真的?”
局长说:“当然。明年我们局会有公务员的编制下来,到时我想办法把你的关系搞妥。”
我内心狂喜,忙说:“谢谢局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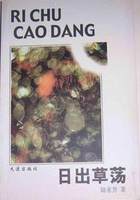









![相女驭夫策[步步倾心]](http://c.dushuhao.com/images/book/2020/03/31/19490880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