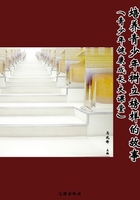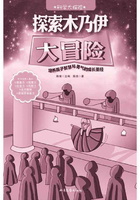他垂眸看着趴在地上的裴心悦,她长如云锦的青丝凌乱如麻,狼狈地贴覆在脸上,挡住她的面容,看不清她此时的模样,只是看到有鲜红的血液滴落在地板上,一滴,两滴,逐渐晕开,像泼染的红梅般娇艳。
“裴心悦,给我站起来。”贺流殇铁青着脸,整个面部线条都冷绷着。
裴心悦颤了一下肩头,然后双掌撑在地板上,掌心一片冰凉,她吃力地站了起来,只是微侧着身,不言也不语,柔顺垂下的青丝依旧挡住了她的脸。
他大步上前,站定在她的面前,而她轻敛着羽睫,视线落在了地面上,看着自己白粉两色的拖鞋鞋尖,鞋面上是一两只可爱的小兔子,她特别喜欢兔子有关的东西。
拖鞋是兔头,睡衣是兔子图案,喝水的杯子上也是,书签,钥匙扣……都有兔子的影子,她喜欢兔子所以也如兔子般柔弱,才这样任人欺凌吗?
他的手抚上她的发,把她两边脸侧的青丝拨到颈后,露出她的脸,鼻孔里流淌出的血水流过破裂的唇角,被打肿的左脸曝光在他怒火燃烧的瞳孔里,那清楚的五根红指印就像五根尖刺扎到了他的眼睛里,疼痛难忍。
他的手轻触上她的脸颊,她咬牙抿唇忍着剧痛没有叫出声来,只是别开了头,远离了他的指腹的碰触。
“刚才为什么不躲开?”在贺流殇的眼里她的坚强已经超越了他对她的定义,刚才他那一耳光是个男人也抗不住,何况是她这样娇滴滴的女人,而且她还很冷静很能忍的模样,不哭也不闹。
他真宁愿她又哭又闹,打他,骂他,也不想她这样憋着,仿佛天塌下来她也能承受的伟大模样。
她还是不说话,转身回到屋子里找了什么东西上,又出来默默走到门边。
“站住,你要去哪儿?”贺流殇见她不说话,把他当空气,心中的怒气更盛了,他一个箭步上前握住她放在门把上的手质问她。
“出去买药也不行吗?”她张口,嘴角的伤口撕裂得疼。
“你这模样还有脸见人!”他一把将她从门边拉开,自己的背抵着门板,盯着她现在丑死的模样嘲弄道。
“我早就没脸见人了,在把我的清白给你的时候,在我求你的时候,我就没有脸了,所以我还在乎这些做什么!”她轻笑了一下,可是眼潭里却惊不起一丝涟漪。
“裴心悦,你可真会作贱自己!”贺流殇狭长的眼眸紧到没有一丝光亮溶进去,仿佛死水一般暗黑,“既然你不要脸,我也不需要再给你脸了,以后就给我安分地待在流溪别院,哪儿也别想去。现在,给我好好待在这里,敢出去,我就打断你的腿。”
撂下这样的狠话,贺流殇抓起桌上的车钥匙就离开,还把门给反锁了起来。
他开着车出了流溪别院,整颗心都是沉闷烦躁的,抑郁难受。
到了附近的药店,他下车去买了只消肿化淤的药膏,并询问了详细被打伤的处理方法,这才离开。
上了车,他把药膏随手丢在了副驾驶座位上,看着那盒药,他的心里是说不出的矛盾。
他要的并不多,只是希望她能好好的和他在一起,每天都能是开心的,其它的事情都不要想。可是她却总是看不到他为之做出的努力,竟然还敢撕开他的伤口,在上面硬生生的撒盐。
没有人敢这么做,只有她,像疯了一般咬疼了他。
现在是他不要姚曼婷了,好不好?
贺流殇是越想越郁闷,牙关紧咬,发泄似的抬手便抬起手用力砸在了方向盘上。他买什么药,她敢这么说就应该承担后果,他何必操心,疼死她活该。
想到这里,他抓起药膏就扔出了车窗外,开车离开。
可是下一秒,他又无奈地折了回来,低咒一声,下了车去把那盒药给捡了起来,回了流溪别院。
打开门,他看到裴心悦已经整理好了自己,穿着睡衣坐在沙发上,正在拿冰袋小心的敷着破裂的唇角和发肿的脸,疼得她光洁的额头上都泛起了一层薄薄的香汗,黑眸像是水洗过一样明亮。
他走过去,把药膏扔在茶几上,然后拿过她手里的冰袋替她敷脸,虽然脸色还是阴沉的厉害,但是眼眸中的火气却小了不少。
“先前……为什么说那样的话?”他犹豫一下,还是问出了口,一边替她的脸做处理工作。
她没有回答,就连目光也被她垂下的羽睫给遮蔽住,双手揪在一起,不知道该说什么。
“以后不要再口不择言。”他自己接着说了下去,“这一次就当买个教训,以后不会这么好过。”
他的伤口岂是旁人能够揭开的,还是他重视的女人。
“你以为我现在过得很好吗?”裴心悦脸色一凝,不甘地捏着双手,“你表面上对我好,让我考虑,可是你转身就对别人说我是你地下情人,说我是卖的,不仅让我失去工作,还被别人羞辱到没有还口的地步。”
“难道别人说错了吗?”他不以为然,眸子阴沉。
裴心悦眼眶泛红,哑然地睁着水瞳,那些委屈的就这样哽在了喉咙里,噎得她好疼。
“难道我又有说错?”她也不甘示弱。
“我和姚曼婷之间你了解多少?”他冷瞥了她一眼,自以为聪明的女人,“不了解事情的原委,你就没有发言的资格,更不能胡言乱语。”
她依然说不出反驳的话来,她极力维护的那点自尊在他的眼里是那样的可笑。他就是要让她面对现实,认清自己的身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