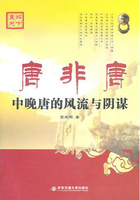风习习吹过,母亲去世已经六年了,看着石碑上同自己恍若相似的笑靥,止歌闭上眼,仿佛依旧可以清晰回忆出同母亲一起的场景。
“哇,妈妈,你看!那风筝飞得好高啊,小歌都看不见了,他都躲到云里面了!就这样‘咻’的一声不见了,跟小歌捉迷藏,哇!”
“小歌,我们都要像风筝一样,勇敢地向远处,向高处去飞,不要畏惧什么,只要迎着阳光,你看,就可以做到。”
“妈妈,我不飞远也不会飞高,我就在这陪你,你在哪,我就在哪。或者我带着妈妈一起飞着,那么美,那么高,妈妈,你说好不好?”
“好,妈妈和你一起,永远一起,陪着我的小歌。”
欢快的孩童声在脑海中回荡着,年少时,总可以那么开怀的笑着,笑的那样张扬,笑的那样无所顾忌。有母亲陪在身边,有快乐伴随左右。
妈妈,你还在我身边的,你在陪我一起飞对吗?你说好的,我们一起,我们永远一起,妈妈,只是,小歌好想你。我知道你希望我做快乐的孟止歌,你告诉我,我快乐的声音就连鸟儿的歌唱都要停止,故取名止歌。
四年了,四年了,我回来了,妈妈,你的样子还是那么美,那么年轻,依旧是笑着看着小歌。而我,也很好,原谅我四年时间才回到这里看望你,不是因为我忘记,而是我知道,你一直都陪着我呢。
妈妈,小歌现在很好,只是想你,我只是很想念您。我听您的话,不难过,要快乐,只是我终于站在您面前还是眼眶潮湿,妈妈,我多想你再像小时候那样抱着我,给我讲故事,教我做算术,做好饭等我回家,我多希望你再一次因为我成绩不好打我手心又抱着我落泪,因为我打工时不小心蹭破了手背而心疼不已,我多期盼下班回到家还有点亮的灯光,热热的饭菜,和你嘘寒问暖的关心——哪怕再一次也好。
只是妈妈,再没有人做这些,我只好一切自己来,您过世的这六年,每天上班前,我都要把家里的灯打开着,这样,晚上回到家,就不再感觉一室冷清。您过时的这六年,我自己一个人,努力地生活着,我把自己照顾的很好很好。您看,即使经过了那么多事,我依然可以微笑着,我已经学会如何坚强,如何不撒娇不依赖。妈妈,您看,小歌长大了,您很放心吧。
欧阳看着止歌悲伤的神色,张开手臂搂紧了她,拨了拨她被风吹乱的刘海,看着墓碑,“伯母,我是欧阳,您或许不认识我,我是止歌的男朋友,我同您保证,止歌,我会保护她,不让她受一点委屈,不让她难过伤心,您放心,今生,我会尽最大努力给她最大的幸福。因为止歌,让我看到了天堂的模样。”
低低的声音在耳畔响起,又仿佛从风的源头深深传来,却带着无比的坚定和沉稳,似是在许下一生的誓言。也或许,这就是欧阳,从来自信潇洒张扬,却总在最需要时给了止歌最安定的力量。同样,也正是因为止歌,欧阳知道,再没有一个人,只要看到她的笑就会不自觉轻扬嘴角,看到她皱眉,欲以身代。这种完全的喜悦和难过仅仅因为她,孟止歌,让他的感情变得那么直接又那么完整。
止歌已经平稳了悲伤的情绪,微笑着对欧阳说:“欧阳,谢谢你,我想单独和母亲呆一会,你先去车里等我吧,我一会就过去。”
见欧阳不肯移步,只好故作认真的举起左手:“老板,我发誓好不好,我不会难过,你在这里会妨碍我和妈妈说悄悄话的,员工也是有隐私的,过去等我,好不好?”然后板起脸,似有不满的抱怨,“妈妈,你看,欧阳不听话了,我不要他了好不好?”
欧阳无奈,只好揉了揉止歌的头发,然后转身回去车里。
透过车窗,欧阳远远望着那瘦弱的身影,白色的裙踞飞扬,发丝有一些凌乱,精致的脸上,明明是浓重的哀伤,却又试图掩藏,坚韧倔强。就是这样的孟止歌,走进了他的心里。从来,欧阳并不相信爱情,父母的商业联姻,三十几年的夫妻,却依然相敬如宾,没有吵架,亦没有太多关心,彼此维持着最简单的朋友关系,淡的察觉不到味道。欧阳曾想或许自己也会是这样,和一个陌生人结婚,然后继续开拓父辈的公司。爱一个人,和爱的人结婚,正因为自古难全,所以那些从来都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他从不敢奢望。直到遇见止歌,他忽然愿意为一个人付出一切,他忽然想安定下来,就是这种感觉,或许连他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何只是当初机场匆匆一瞥,那个人就稳稳地住进自己左胸第四根肋骨往里一寸的地方,为何只是一个擦肩而过,他就忽然想要拥抱她,带她走,给她自己拥有的一切。
年华似水,匆匆一瞥,难忘那天,你我之间。
总会有些人可以只用一瞬间便让你希望陪着她自此白头。
“妈妈,他对我很好,我们会在一起的,对吗?”止歌仰起头,清亮的眼睛却在下一刻迷茫无助,轻微的叹息声,被风打碎,散落的好远。
只是,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勇气,也不确定。总会不时想起他,四年了,为什么总感觉他的影子挥之不去,我以为我足够健忘,却为什么,总会——
何叙,他就像长在心口的毒,越是抑制,越会蔓延,深入骨髓,即使我假装视而不见,却又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那蚀骨的痛感。我们仅仅在一起一年半的时间,我已经花掉四年时间去忘怀。
可我知道,说忘记了,不过是在骗自己。
四年来,我用着各种各样的方式逼自己清醒一些,最后,选择让自己爱上另一个人来遗忘曾经,看着欧阳,我告诉自己,‘我孟止歌有多么幸福,他爱我,我也会尽力去爱上他,那个年少的一厢情愿,一往情深总会过去,现在我爱欧阳。’可是每每看到镜子,我都深深的闭上眼睛,怕那里面倒影的是何叙的脸。
看不到,就是不想念,不说出口,就是不爱了,更多时候,我只有依靠这种自欺欺人的方式才能好好地生活。
不停地工作麻木自己的痛感,可是依旧清晰的在深夜中辗转难眠。记得他衣橱中安宁送的那件衣服,他抽屉里珍藏的照片,甜蜜的和安宁拥吻的场景,病床前自己从未见过的细致耐心,以及失望透顶的严酷责备……一次又一次哭到窒息,那方自己曾经无限贪恋的胸膛终究还是为别人张开,他占据了整个生命一般,他走后,自己就空了。
妈妈,还记得我曾说过的那句话吗,我不会轻易爱一个人,只要爱上,就是深爱。不管我承不承认,他,都是那个人。
可是,什么是深爱呢,应该叫做成全吧!那么爱,终究要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竟然是放开他的手。
说的坦然,做的艰难。
我总以为,我已经平静,却原来平静的不过是一个假象,当我踏上这片土地,熟悉的感觉带来的是那张我熟悉的似乎从未远去的脸——何叙,明明四年没有再提起过这个名字,可为什么,丝毫没有任何陌生的感觉,就好像它一直在我生活中,或者说在我记忆最深邃的地方。好像一场盛大的圆舞,我以为我已经逃离,可睁开眼才发现,我不过是在画地为牢。
用力,缄默,却无可奈何,这正是我的可悲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