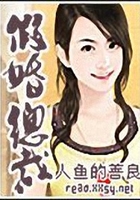这么想着,她站起身来,想回房间里去,风有些大了,沁凉入骨。
可就这么站起来,无意往阳台下扫视了一眼,她就怔住了。
空间的距离给人勇气,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当着面没办法说出来,可只要站得远了,以为对方看不到自己了,于是残忍的缠棉的话便能轻易的说出口,不会痛不会觉得肉麻,或是麻木或是甜蜜,不过是犹豫了那么一下子就能做到的事情。
连目光都能肆无忌惮起来。
她与顾方泽的家,位于本市最顶级的住宅区,是寸土寸金的市区里少有的能独门独户的三层小别墅。此时她正在二楼的阳台上,看着楼下不远处倚在静静停靠的白色宝马旁,那个有着瘦削英俊的侧脸的男人,脑子空白,一时不能言语。
很久以前,似乎也有这样一幕。是平安夜,很晚了,室友们都各自赴约还未回。那时她以为他还在美国,在宿舍里与他通电话时,他在电话那头声音很低但很清晰,“涟漪,我很想你。”
她觉得脸烫得厉害,躲在被窝里嘴角翘得老高,可嘴巴还要装模作样,“你骗人,美国那么多金发碧眼的大美人,谁知道你有没有把持不住偷吃!”
那头笑,有点得意有点邪气,“你下楼来看看不就知道了。”
她握着手机的手指顿了好几秒,随后倏地一丢手机,腾地从床上蹦起来,顾不上穿鞋,就这样推开门,打着赤脚噔噔的下楼。
那人也是如今日这般,倚在车旁,长身而立,嘴角噙着明亮的笑意。
她尖叫了一声,飞扑向他朝她展开的怀抱。心脏扑通扑通跳得飞快,像雀跃顽皮的小鹿,仿佛要跳出胸腔般一样,连天空绽放的烟花都仿若是为他们而设的,那样的欢喜,可惜从此再未有过。
如今时隔多年,他站在她家的楼下,倚在车边抽烟。他抽烟的样子还是没变,眉头微微皱着,大口大口的抽,然后优雅的吐出袅袅的烟圈,渐渐迷蒙了他的脸。
她站在阳台上看他。她知道他是为她而来。可她不明白,他为什么还要出现?
即便回来了,为什么偏偏要三番两次的出现在她面前?
明明当年……
心钝钝的疼得厉害,她抿紧了唇,握着拳头转身往回走。
李涟漪,什么都会过去的,只要放得下,什么都会过去的。
就在这时,她上衣口袋里放着的手机突然响起阵刺耳的铃声。房间越是静越是显得铃声尖锐,她的心紧了紧,恍然隐隐也知是谁打来的,但手却怎么也没办法动弹一下,任凭铃声一遍一遍的响着,直至安静。
可没隔几秒,手机又响了起来。
深吸了一口气,她仍是抵不住这催命般的铃声,拿出手机,看到了蓝莹莹的屏幕上陌生的电话号码,好似有点熟悉,却又不大想得起来,手指僵硬了一会儿,她按下接听键。
“你好,我是李涟漪,请问你是?”她能听到自己强自镇定的嗓音,很好,很完美,几乎没有破绽。
那头沉默着,许久,久到她的手指乃至身体都忍不住开始发抖,才传来熟悉的低哑的嗓音,“涟漪,我想见你一面。”
听到了声音,确定了猜测,她反倒是平静下来,仿佛是一直吊在半空中终于解脱,她吁了口气,抿唇缓道,“对不起,我没时间。”
那头很静,但她可以想象,他定是在抽烟,抽得很凶,或者是拧灭烟头,踩在脚下一点点的碾碎。他向来是如此,得不到的就毁掉,得到了厌弃了就丢掉。
曾经她无比迷恋他这点,觉得这样的男人和小说中描述的一样,霸道却可爱至极。可后来才知道,自己遇上了这样的他,分明是场自我毁灭的灾难。
她不想再见他。如果有可能,她希望此生都不再见到他,人来人往,擦肩而过也不要。
“有什么话你直说就好。”
电话里传来略重的呼吸声,默了几秒,他说,“涟漪,我与顾方泽,见过面了。”
李涟漪下楼时,福妈正好捧着洗净的衣服上楼,正巧撞上这正边奔下楼边穿外套的她,惊讶的叫住她,
“小涟漪,你这是要去哪里,急成这样?脸色这么难看。”其实何止难看,简直就是惨白!
李涟漪顿了下脚步,勉强扯出一抹笑,“福妈,我看上去……很不好吗?”
福妈是个有点干巴的女人,瘦瘦的,个子高,和福叔完全呈互补状态,听说年轻时也是个大美人,福叔还未转业时便嫁了过去,心甘情愿的做了军嫂,一熬就是这么多年,是个内心坚强,善良和气的妇人。
此时她正面露担忧地望着李涟漪,“是啊,是不是前些日子生得那场大病还没好干净,这可怎的是好,要不去医院看看?”
李涟漪摆摆手表示不用,随后就这样站在楼梯上,使劲用手揉了揉腮边僵硬的肌肉,眼睛弯起,嘴唇抿了抿,在嘴角处轻轻的形成梨涡陷下去,又看向福妈,“现在好点了吗?”
福妈一头雾水,这小涟漪是怎么回事?举止古怪得很。可看她的表情,笑得真好看,甜甜的,仿佛整个人都在发光似的,于是不由自主的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