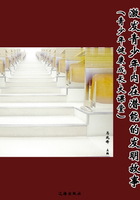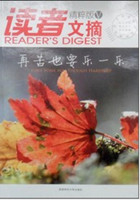第二天早上,弗莱迪早早就起来了。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弗莱迪打着冷战,急急忙忙地赶到马厩去察看那些老鼠囚犯。囚犯们被关在一个盒式畜栏里,紧挨着汉克的马厩,胡蜂雅各布和他的两个堂兄弟负责看守这些犯人。西蒙躺在一只旧粮袋上,睡得很沉。其他老鼠都醒了,他们滴溜溜转的黑眼珠子紧张地盯着弗莱迪,一言不发。
雅各布飞到弗莱迪的鼻子上,说:“一切顺利。刚抓住一只想逃跑的,他想从墙壁打洞逃走,不过我想他暂时不敢再这么干了。我扎了他一针,他就‘哎呀,哎呀’地叫了起来!”
“尽管他也是条硬汉子,”雅各布接着说,“但他还是害怕我把针扎进他厚厚的脑壳中。”雅各布将他的蜂针伸了出来,针尖对准弗莱迪的嘴巴尖,问道,“你介意不介意我在你这儿试一下?就一下,我绝不会伤着你。”
弗莱迪认为雅各布只是开个玩笑而已,但是这也很难说,因为胡蜂总是那么一副表情,就这副表情也很难看出来他们想干什么。“不要!”他说道,“走开!雅各布!”他忐忑不安地盯着胡蜂,一些老鼠咯咯地笑了起来。
雅各布飞起来,在老鼠们的头上嗡嗡地盘旋着。“不许笑!”他叫道,“如果你们知道好歹的话,就应该对强者表示应有的尊重。”
“噢,求求你了,雅各布先生。”一只老鼠回答说,“我们没有——我们不是在笑你,我们是在笑弗莱迪,他刚才看你都看对眼了。”
“什么?我不可能看他看对眼了。”弗莱迪说道。
“哦,对不起,先生。”这只老鼠尖着嗓子抗议道,“我想,你确实得对着眼才能看见他,因为他站在你的鼻尖上。”
“哦!”弗莱迪回答说,“那样的话,也许是这么回事。”他对那只老鼠皱起了眉头,问道,“是你昨天晚上咬的我吧?”
“嗯,先生……我……”
“回答‘是’还是‘不是’。”弗莱迪说着,摆出一副大侦探的神情。
“嗯,我……是的,是我咬的。但是后来你坐我身上了。”
“我明白,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扯平了,或许你是对的。不过——噢,早上好,金克斯。”弗莱迪看到猫儿推门进来,便向他打了个招呼。
“我只是顺便来看看那个该死的家伙是否像往常一样吃着丰盛的早餐。”金克斯回答说,他走过去坐到西蒙的旁边,问道,“这个老恶人今天早上怎么样?”
西蒙睁开一只眼看了看,随后又闭上了。
“不要管他,金克斯。”弗莱迪说,“他要是能好起来,也够倒霉的了。出来吧,我有些话想对你说。”
他们走出畜栏,来到谷仓院子里,查尔斯碰巧也从鸡舍走了过来,金克斯向他打招呼道:“喂,查尔斯,你这只好斗的老公鸡!昨晚你打的那场战斗确实激烈。我看到你了,你在那儿爪抓脚踹,把敌人打得缺胳膊断腿的。当时我还说:‘大家快看哪,那儿有只公鸡就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把敌人打得……’”
“嘿!快闭嘴!”查尔斯恼怒地反驳道,“你明明知道我昨晚不在那儿。我……那好,要是这个农场受到成群的凶狠的老鼠的袭击,你难道希望我抛弃家业,抛下亲爱的妻子和二十七个孩子,任由老鼠们对他们进行蹂躏吗?尽管我也想和你们在一起,和你们并肩战斗,但我的职责告诉我,我应当保护鸡舍。听着,朋友,在这长满美丽羽毛的胸膛下面跳动着一颗并不懦弱的心,它……”
“胡扯!”金克斯说道,“明明是你亲爱的妻子亨莉埃塔不让你出来,怕你漂亮的尾羽被老鼠咬断。老弟,不要再跟我们说什么并肩战斗,还有什么可以把心掏出来给我们看之类的鬼话!”
查尔斯垂下了头,弗莱迪替他感到难过。这只公鸡是个吹牛大王,而且还是个严重的“妻管严”,但他的确不是一个懦夫。他曾经在一次战斗中凭自己的实力打败过一只老鼠,并且,大约就在一年前,他还单枪匹马地冲进位于森特博罗的赫伯·加伯乐的办公室,将他赶出了办公室。“查尔斯,明天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块儿去坎皮奥先生家?”弗莱迪问道,“我们要处理一些有关他姑妈的事情,你或许可以帮上忙。”
查尔斯立刻来了精神,“我去!”他声音洪亮地回答道,“能为坎皮奥先生服务是我的荣幸。”
第二天一早,他们就出发了。天还在下雨。动物们并不像人类那样在意雨,不过弗莱迪还是撑开了比恩太太的那把深紫色的旧伞。“全身湿淋淋地走进坎皮奥先生家整洁的客厅不太好。”他说,“米纳瓦小姐会发脾气的。”
“她总爱发脾气。”查尔斯说。
“这就要看你的了。”弗莱迪说,“这也是我让你来的原因,你要说一些最好听的话来恭维她。”
他们赶到坎皮奥先生家时,浑身还是湿透了。班尼斯特给他们拿来浴巾,让他们在进入客厅前擦干身上的雨水。他们正在使劲地擦拭身上的雨水的时候,米纳瓦小姐出现了。
“老天爷!”她叫道,“看你们把垫子上弄得到处都是水!你们怎么选这么一个天气来?”
“米纳瓦小姐,”查尔斯回答道,“我们只是想尽快地再见到您,才不顾这么恶劣的天气,多么恶劣的天气也挡不住我们。”
“是吗?”米纳瓦小姐满腹狐疑地问道。
“小姐,您优雅的仪容,犹如灿烂的阳光、温柔的清风,将阴郁之气一扫而光。”公鸡接着说道,“在您迷人微笑的照耀下,阴云四散,红日升空,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亮的。”查尔斯一边说,一边深深地鞠了一躬。
一点儿也不假,一丝微笑浮现在米纳瓦小姐的脸上。它当然不会驱散阴云,也不会像查尔斯的赞美词中所说的那样美妙,但它毕竟是一个微笑。她说:“请到客厅来。”
坎皮奥先生打听到一些消息。狱长打电话告诉他说,安德森先生卧病在床,不过一两天就会好起来。“尽管这样,但我想他不会太好过的。”狱长说,“前面扎的都是豪猪的刚毛,屁股后面又满是小铅弹,看来他只能侧着身睡觉了。”
“嗯,听到这样的消息真是太好了!”弗莱迪说道,“不过,还不尽如人意。尽管我们打乱了他的计划,使他无法得到你和比恩先生的房子,但他还是得到了旅馆。”
“到阳台上来。”坎皮奥先生说,他们跟着他来到阳台上,“你们来听听。”坎皮奥先生说。
雨已经停了,湖面上隐隐约约传来一些微弱的榔头捶击声。
“是木匠,还有铅管工干活的声音。”坎皮奥先生说,“他已经开始找人维修旅馆了。狱长说了,艾哈准备康复后,就搬到旅馆去住。真是可耻,可我们又能怎么办?”
“我认为……”弗莱迪刚要说话,阳台的另一端响起一个声音,打断了他。“到这里来!”这个声音说道,弗莱迪循着声音看过去,发现是埃尔米拉小姐。她围着披肩,坐在轮椅里,神情黯然地凝视着灰色的湖面。
他走过去,查尔斯大摇大摆地跟在后面。不过,坎皮奥先生则走过屋子。
“背诗!”埃尔米拉小姐说。
“我还没来得及写其他悲伤的诗。”他回答说。
“沼泽那首就行。”埃尔米拉小姐说道。
“哦,您还想听那首诗?好吧。”他开始背诵起来,中间适当地加入一些哽咽与抽泣。
埃尔米拉小姐比以前笑得更加开心,但是查尔斯用一只爪子捂着眼睛,失声痛哭起来。“哦!天哪!哦,天哪!”他哽咽地说道,“哦,太悲惨了!我这颗凄惨的心啊!多么凄凉的一种美!多么杰出的一部绝望之作!”
弗莱迪觉得查尔斯做得太夸张了,他冲他直摇头。埃尔米拉小姐闭口不笑了,有些恼怒地看着查尔斯,“他总是这样吗?”她问道。
“他总是这样。”弗莱迪回答说,“他总是沉迷于悲哀,沉浸于伤痛,在痛苦中煎熬。他是我所认识的最痛苦的家伙。”
查尔斯还在不停地哭泣。
埃尔米拉小姐耸动着肩膀,不耐烦说道:“走开!”
“好啦!”弗莱迪说,“来吧,可怜的家伙。”他搀扶着哭个不停的查尔斯走进屋里。
公鸡一进屋就直起了身子,“那首诗真糟糕,弗莱迪。”他说,“如果我把一只爪子绑到后背,光靠另一只爪子写诗却不能写出一首更好的诗的话……”
“你真是太棒了!”弗莱迪不无讽刺地说道,“你大哭大叫,做得真是天衣无缝!她知道你是假装的。”
“恰恰相反!”查尔斯说,“她当时都快疯了,对不对?那是因为她遇到一个比她还悲伤的人。你根本就没有搞懂她,她并不想让其他人悲伤,她光想做这个房子里最悲伤的人。如果她待在这儿,大家总是不停地哄她高兴,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是因为她喜欢大家都哄着她。如果大家都成天号啕大哭的话,你看她还会不会在这儿待下去。”
“呸!”弗莱迪说,“说这些毫无意义。”
“嘿!那只是因为你根本没有想到!”查尔斯气愤地说道,“好啦,你爱怎么着就怎么着。不过,如果坎皮奥先生想让她离开这里的话,那么他最好让我来处理这件事。”
其实,弗莱迪心底已经认可查尔斯的想法可能管用。不过,他很清楚,如果他当面接受查尔斯的观点,查尔斯就会缩到一边,什么也不干。所以他一直不停地抨击查尔斯的观点,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使得他几近疯狂。最后,查尔斯说,这方法一定管用,要不他来做给大家看看。说完,他便踏着重重的脚步走出了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