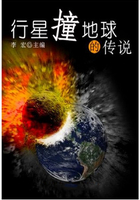显而易见,由于鸡窝的旋转门不大,只够供鸡儿们出出进进,所以绑架者肯定是只小动物。
“可能是黄鼠狼,”弗莱迪说,“几年前我们已经把这一带的老鼠消灭干净。”他打开手电筒,对门作了一番检查。剩下的三十三只鸡顿时拼命扇动翅膀,咯咯地乱叫。亨莉埃塔连忙进去安抚他们。
弗莱迪继续他的调查工作。他把门慢慢地转来转去,用手电筒和放大镜仔细察看四扇页门。然后,他又回头望着地面。他还尽量伸长脖子朝门里面看,里面的距离并不很大,只能把脑袋伸进去。“哼,”他说,“哈!”接着,他尖叫一声,响得半英里以外都听得见。
查尔斯和威利站在后面,望着那位大侦探开展工作。威利露出无限敬畏的神色——我是说,要是蛇能表达这种情感的话,他肯定会露出这种神色的。所以事实上,蛇还是蛇的那副样子。倒不是说,他知道弗莱迪在干什么,而是心里深感吃惊,弗莱迪竟然还会办点儿事。
查尔斯也全神贯注地望着,带有一点儿神气活现的样子,不时地点一点头,好像在说:“啊,就是这样,干得不错,这正是我会干的。”虽然公鸡跟王蛇一样不知道弗莱迪在干什么。他不可能知道,因为其实连弗莱迪自己也不知道。他只是在扮演大侦探。
威利听到弗莱迪尖叫一声,激动地说:“天哪,他准是发现了什么情况。”
“很可能是一条线索,”公鸡说,“弗莱迪这家伙倒挺能干——挺能干的。他是我的一位……”说到这儿,他没有说下去。他本来想说“他是我的一位很有前途的学生”,但是,他忽然想起威利已经认识弗莱迪很长时间了,听了他的吹牛是不会相信的。
然而,弗莱迪没有发现任何线索。当然了,要是你把头伸进一扇旋转门,而又没有完全伸进去,接着要是有人推着门想从另一边往外走,那么你的头就会被卡在中间,无法再缩回来,除非那个人不再推那扇门。现在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亨莉埃塔想往外走。她听见弗莱迪被卡在中间哇哇乱叫,更是拼命地推那扇门,想出来看看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喊得越响,她推得越起劲。要不是威利拿手电筒照着猪儿,因此母鸡透过玻璃能看见她把弗莱迪的脖子挤在门的边缘和门框之间,她很有可能会把他挤成重伤的。
弗莱迪终于脱了身,不得不躺下来喘口气。亨莉埃塔站在他的身边,用翅膀替他打扇,说:“真对不起,弗莱迪。可是,你干吗不叫我一声呢?”
“叫你一声!”他喊道,“人家都快憋死了,哪里还叫得出来。”
“胡说!”母鸡说,“你还大喊大叫呢,不可能憋得太厉害。快憋死的人连吱吱声都叫不出的。”
“大喊大叫!”弗莱迪光火地说,“我怎么可能大喊大叫,当时……哎呀,你看看我的脖子!”
弗莱迪的脖子上确实有几道痕迹,但亨莉埃塔用翅膀刷了刷,把痕迹刷掉了。“不过是门上的灰尘,”她说,“我想,伤得倒不厉害,只是吓了一大跳,弗莱迪。”
“算了!算了!”弗莱迪站了起来,“你就这么感谢我……”
乱哄哄的场面,加上弗莱迪的喊声,把有的动物都吵醒了。这时候,金克斯、威金斯太太以及两条狗罗伯特和乔治都过来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由于没有强盗的影子,也没有那两只失踪的鸡的影子,弗莱迪就请那两条狗到处嗅一嗅,看看能不能嗅到陌生人的气味。嗅着了就可以跟踪绑架者,让两只小鸡重新回到家人的怀抱——要是他们没有被吃掉的话。
四周没有见到有鸡毛,因此他们没有被当场吃掉,这一点可以肯定。那样的话,盗贼很有可能想把他们弄到个僻静的地方,这样鸡毛就不会被发现。于是,罗伯特和乔治满怀希望地到处嗅着。最后,乔治宣称,他认为自己闻到了一种怪味儿。他把别人叫过来,看看能不能查出点儿什么名堂。
金克斯说,他认为是一种很淡的软糖味。弗莱迪说,主要是旧毯子的味道,虽然里面夹杂着一点儿淡淡的煮卷心菜的味道。威利什么味儿也闻不出来。
“哎呀,我觉得,绑架者闻起来根本不是软糖味、毯子味和卷心菜味,”威金斯太太说,“我来闻闻看。”她使劲嗅了两下,但她是把气吹出来,而不是吸进去,结果扬起了一大团灰尘,弄得大家直打喷嚏。
“大家喷完了鼻息,”亨莉埃塔尖刻地说,“是不是该为我的孩子们想想办法了?”
“说得对,”弗莱迪说,“我们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乔治,你认为,你闻到的那个怪味到底是什么味儿?”
小棕狗说:“就在这儿,要是你想闻的话。这既不是软糖味,也不是卷心菜味。这肯定是老鼠味儿。”
“老鼠味儿!”弗莱迪不大相信。金克斯说:“呸,这儿已经有一年时间没有老鼠的踪影了。”
“好吧,”乔治说,“你爱怎么认为就怎么认为吧。”
“乔治说得对,”大牧羊狗罗伯特说,“我们是不是最好去跟踪那只老鼠?趁他也许还没有……”他朝亨莉埃塔瞥了一眼,没有说下去。
“趁他也许还没有把他们吃掉——你是想说!”母鸡直截了当地说,“哎呀,有话就直说,然后马上动手干,别一个通宵站在这儿说空话。”
于是,两条狗立即出发——嗅呀,嗅呀,嗅呀——他们顺着谷仓院子的边缘,穿过那片草场,朝着林子一路嗅过去,其他几只动物跟在后面。
要是盗贼确实是一只老鼠,弗莱迪要找回两只小鸡的希望就很渺茫。老鼠有时候偷小鸡,但很少把鸡搬到远处。这件事有好多令人费解的地方。一只老鼠怎样搬得动两只鸡呢?他干吗要挑小布罗伊勒呢?这只小鸡虽然是他妈妈的心肝宝贝,却是个皮包骨头的小东西。有三十五只鸡可供选择,他干吗不挑一只肥点儿的当晚餐呢?
羊肠小径越过鸭塘那里的小溪,然后向北进入树林。到了这儿,威金斯太太转过身来。“你们往前走吧,”她说,“上次我来这林子的时候,被树枝钩住了,结果扭伤一只脚,那还是大白天哩。我去找找那几只兔子,看看他们有没有发现什么动静。再过个把钟头天就亮了。”
弗莱迪也不大喜欢这黑黢黢的林子。他倒不是个胆小鬼。要是面临真正的危险,他会像任何人一样勇敢。或者说,几乎会像任何人一样勇敢。但是,他有着丰富的想象力。对这种人来说,脑海中的危险远比现实中的危险要可怕得多。他知道,他只要走进林子里,便会开始自己吓自己。他会想象每簇丛林后面都有幽灵伸出粗糙的爪子抓住他,树干周围都有一张张可怕的假脸窥视他。一想到这种情景,他就会耷拉着尾巴。
然而,大侦探怎么能畏缩不前呢?于是,当他看到两条狗进了树林深处,在黑暗里东闻闻西嗅嗅,金克斯和威利跟他们在一起,时刻准备发起突然袭击,查尔斯在亨莉埃塔的催促下也跟在后面时,他叹了口气,接着往前走。
“肯定是老鼠,”罗伯特轻轻说,“这儿的树叶是湿的,容易把味儿留下来。”
比恩先生的这片林子不算很密。虽然在黑暗里看不大清楚,弗莱迪却没有跌跌撞撞,还是跟得上脚步。然而,他的想象力却活跃起来了。他朦朦胧胧间看见右方不远处有一片黑压压的丛林,一只长着角的大猩猩咧开嘴巴在可怕地朝着他笑。他还隐约听到一种很有规律的声音——一种笨重的啪嗒啪嗒的脚步声,毫不留情地跟在他的后面!随时都会有一只干巴巴的大爪子搭在他的肩上,把他往回拉——原来是一根树枝。有一回,前面的动物一松手,树枝弹了回来,啪的一下打在他的鼻子上。他吓得不由得发出一阵尖叫声。
别的动物停下了脚步。“喂,我们应当保持安静,”罗伯特用责备的口气说,“出了什么事儿?”
“没事儿……哦……没事儿,”弗莱迪结结巴巴地说,“只是……哎呀,只是有一样东西……突然朝我弹了回来。”他心里想,那东西就是突然弹回来的嘛。接着,他又听见那种很有规律的声音,最后发现原来是自己的心跳声。
“我们快要走出树林,踏上后面的路了,”乔治说,“所以现在光线好像亮一点儿了。”
他们快要走到一座跨越溪流的小桥上时,查尔斯说:“嘿,我清楚地记得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他摆出一副装腔作势的样子,“你们肯定还记得,我的朋友们,有一天我在这儿遇到了一只大老鼠,在一场公平而又公开的决斗中打败了他。那天,我为自由打了一仗,这个消息传遍了整个文明世界。查尔斯——已经在传说和故事中赫赫有名……”
“嘘,小声点儿!”弗莱迪轻轻地说,“路那边有什么东西,看上去像是一辆汽车。我们顺着水渠爬过去看个究竟吧。”
果真是一辆汽车。他们爬近一点儿,听见了发动机嘎嘎一响,发动了。接着,那辆汽车没有打开头灯就开足马力,朝城里疾驶而去。
两条狗在停车位置的周围嗅来嗅去。亨莉埃塔挖苦地说:“我觉得我们是来找老鼠的。干吗对汽车这么在意?开汽车逃跑的又不会是老鼠!”
“没错,”罗伯特说,“但是,老鼠到过汽车旁边。这倒很有意思——这一带都是他们的味道。这儿还有一种怪味儿。不是老鼠的味儿。这味儿不大一样。”
“真有意思,我也闻到了,”弗莱迪说,“这种味道好像以前闻到过。哎呀,老鼠去哪儿……”
“喂!”乔治喊了一声。他已站在那座石墙跟前。“我看,老鼠钻进这墙里去了。”说着,他在墙脚边拼命挖起来。那里有个老的旱獭洞。
别的动物都跟着过去。但是,乔治挖起来的石块和泥土不停地从他们的耳边飞过,所以他们又不得不散开了。“别着急!”弗莱迪说,“你这么挖是挖不出来的,你得挖个大洞才逮得住他,但这样这老墙就会塌下来压在你的身上。”
“没错。”罗伯特说。他朝洞里嗅了嗅:“老鼠肯定在这洞里,我们只要坐在这儿等他出来就行。而这是你的活儿了,金克斯。”
“我来试一试。”威利说。他把头伸进去,接着又缩回来,叮嘱了几句:“好吧,我来试一试。不过,要是这洞大一点儿就好了。听着,要是我卡在里面,你们就得把我拉出来。我摆动两下尾巴,你们就动手拉。”说完他又钻进了洞里,但刚进去五英尺,就不动了。
在漫长的一分钟时间里,什么动静也没有。威利还有十英尺长的身子露在旱獭洞外面。然后,突然,它动了一下,接着却又不动了,再接着开始拼命扭动起来,尾巴也啪啪甩了两下。“他给卡住了!”弗莱迪说,“快往外拉。”
大家冲上前去,然后停住了,互相看了一眼。当然,蛇的身上是没有地方抓得住的。
“天哪,”金克斯说,“那怎么办呢?什么地方也抓不住,怎么往外拉呀?除非我把爪子刺进他的肉里。弗莱迪,你能不能用爪子抓住他的尾巴,而又不刺痛他?”
“我想不出办法,”猪儿说,“我们抓不住他,那只好让他缠住一些东西。但愿他听得见我们的话,这种办法也许行得通。”他走过去,从路边的篱笆上拆下一根木杆,横放在威利的身上。蛇儿好像理解了他们的意思,马上在上面缠了两圈。“好了,”弗莱迪说,“快来,抓住这杆子。不,抓住这一边,然后用力往外拉。”大家拉呀拉,终于像拔瓶塞那样把蛇拉到了外面。接着,他们放掉杆子,匆匆奔到蛇的前端,去看是怎么回事。
威利说不出话,他嘴里衔着一只样子很难看的大老鼠。
“哎呀,天哪,”弗莱迪说,“原来是我们的老朋友西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