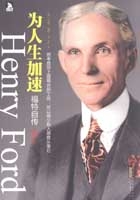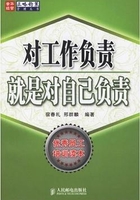1 早期译本中仓央嘉措诗歌的篇目数量
事实上,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客观地说,只是在民间流传了寥寥几首。比如“东山明月”、“不负如来不负卿”、“第一最好不相见”等,这几首诗可以说尽人皆知;但是,若让一位自称喜爱仓央嘉措诗歌的人再列举出几首来,估计是很难说得上来的。
那么,仓央嘉措到底写过哪些诗,流传到今天的有多少首呢?
很遗憾,就连这个简单的问题,都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
这是因为,直到20世纪初期,这些诗歌的传播经历了二百年之久,但却没有刊印本,一直是以手抄本和口口相传的形式流传的。很显然,以这种形式流传,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增删的可能性很大。
到了20世纪,尤其是于道泉先生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后,诗歌的数量问题有了基本的答案。对诗歌数量做了详细统计的是我国藏族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佟锦华(1928~1989年)先生,他在《藏族文学研究》一书中曾提到:
“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于道泉教授1930年的藏、汉、英对照本62节66首;解放后,西藏自治区文化局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本74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本124首;还有一本440多首的藏文手抄本,另有人说有1000多首,但没见过本子。”
由以上的几组数字看来,就连佟锦华先生,也无法确定诗歌数量。而这个数量,是随着出版者的版本不同而变化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了解一下仓央嘉措诗歌的出版版本。
近些年,仓央嘉措诗歌汉译本出版过多种,但大部分是根据以前的汉文译本重译的,也可以叫做“润色本”,而最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版本,就是于道泉先生1930年的译本,是汉译本中最早的,他翻译了62节计66首,这个数字也应该视为仓央嘉措情歌流传到20世纪初时的大概数量。
因此,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于道泉先生翻译诗歌的前前后后,最主要的,是他在哪里得到这62节藏文的原本。
2于道泉本62节的真实来历
于道泉(1901~1992年),我国著名的藏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他精通梵文、藏文、蒙文。1926年,他受聘请为京师图书馆做满、蒙、藏文书的采访和编目工作。当时,他结识了两位藏族朋友,一位是西藏驻京僧官降巴曲汪,一位是藏文翻译官楚称丹增,这两人在雍和宫北大门居住。因为于道泉对藏文很有兴趣,于是两人将雍和宫的一间房子借给他住,平时教他研读藏文。
就是在这个时期,有一位西藏友人从拉萨来到北京,他随身带了一本梵式的小册子《仓央嘉措》,内容就是所谓的“仓央嘉措情歌”。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小册子的原文,是诗句237句,两句为一段,并不分节。
由于正在研读藏文,而且,于道泉本人对诗歌也很感兴趣,于是,在藏族朋友的帮助之下,他将这237句翻译为汉语,并依照诗句的意思,给它分为了54节。
此后,于道泉又从另一位朋友那里得到一本印度人达斯(Das)所著的《西藏文法初步》,见其附录中也有仓央嘉措情歌。于道泉经过与“拉萨本”小册子的对照,发现两本不完全一致,“达斯本”是242句55节,其中,“拉萨本”的第11、23、24、26、27、45,这六节“达斯本”里没有,而在“达斯本”54节后多出7节。将这多出的7节翻译之后,就形成了于道泉译本中的第55节到第61节。
那么,于道泉译本的第62节又是从何得来呢?这是根据一位西藏朋友口述后的补遗。
这就是于道泉译本62节数量的来历。
从这儿可以看出,第一,拉萨本、达斯本和藏人口述(一首)是于译本的渊源;第二,62节这个数量是于道泉人为划分出来的,“拉萨本”原本实际上是不分节、连着念的,但因为于道泉的整理比较符合诗意,因此出现了仓央嘉措诗歌的数目。
而后世人在于道泉译本的基础上,重译、润色的版本,也都遵照了这个数目。但我们必须清楚的是,“拉萨本”本身是没有数目的。
于道泉先生译后,曾将文稿交给许地山先生润色修改,但终不满意,于是就放在一边了。
到了1927年,陈寅恪先生推荐于道泉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这个时候,于道泉又将文稿润色后,向傅斯年先生提出申请出版,这就形成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版本的《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它在1930年由“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的形式正式出版,这也就是第一本仓央嘉措诗歌汉文本。
在出版诗稿的同时,于道泉先生还撰写了一些补充性质的文字,大致有《自序》、《译者小引》、《附录》等,其中讲述了仓央嘉措生平、翻译诗稿的缘起和若干需要解释的问题。
于道泉先生的译法,简单来说是“逐字逐句”的“直译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诗歌的原意。但是因为要照顾到文字的原汁原味,所以,于译本在现今看来,读起来有如嚼蜡,有的诗作丝毫没有诗意,而且有很多粗陋之处。对这个问题,于道泉先生也承认,“翻译时乃只求达意,文词的简洁与典雅非我才力所能兼顾”。
不过,这个版本虽然读起来不好看,价值与意义却是非凡,第一,如果没有藏文原本,或者不会藏语,也可以使很多学者研究仓央嘉措诗歌,这是个比较客观的汉文资料;第二,这个译本对后世影响极大,它开创了仓央嘉措情歌翻译及研究之先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就是汉译仓央加措情歌的蓝本。
3神秘版本译出来60首
由于道泉先生的“蓝本”而来,后来人的版本便层出不穷了。需要强调的是,后来版本中大多数是从于道泉本“重译”而来,由此,于道泉先生所定62节,便顺理成章地延续下来了。
这样说来,如果有人说翻译家、学者普遍公认仓央嘉措的诗有70首左右,并以大多数学者译作的数量为证,那么,这就是个非常偏颇的结论。因为于道泉的分节是自定的,而“大多数”译者是从他的版本重译。实际上,这就像是孙悟空的猴毛变成小孙悟空,小孙悟空再多也不证明孙悟空有成千上万,只是他的化身罢了。
那么,有没有不是从于道泉译本重译过来的汉译本呢?
如果这个版本也是60~70首,而且它又与于道泉得到的藏文小册子毫无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初步认定,仓央嘉措的诗歌流传下来的大概就是这个数字。
这样的版本有一个,就是刘希武先生译本。
刘希武(1901年~1956年),四川人,1939年元旦,他赴当时的西康省教育厅任秘书,到职第四日,拜访了著名学者、翻译家黄静渊先生。因为刘希武平素好作诗文,是当时颇有名气的诗人,所以,他们说到了藏族文学。
刘希武先生提到,“康藏开化已久,其文艺必多可观”,并请黄先生推荐书目。黄先生便拿出一本书,对他说,“试译之,此西藏文艺之一斑也。”
这本书就是当时另一种版本的仓央嘉措诗集,它是藏、英两文的版本。刘希武先生带回家后,将它翻译为60首的汉文古体诗。
对于自己的翻译,刘希武先生说:“夫余之所译,盖根据拉萨本,并参证时贤英译及汉译语体散文,其于藏文原意有无出入,余不可得而知,然余固求其逼真者矣。”
这就是说,第一,刘希武先生译作的“蓝本”,不是于道泉的“拉萨本”小册子,而是另有一本,并且不是汉文本。从他所述来看,他不懂藏文,是依照英文翻译而来,这说明,当时仓央嘉措诗歌已有英文版,但这英文版从何版本而来,今日已无法追溯了;第二,他在翻译的过程中,参考了“汉译语体散文”,此处是不是指于道泉译本,不得而知,但从他的自序和诗歌排列顺序看来,与于道泉《译者小引》相似,多半是受到他的影响的。
从这两点看来,我们无法推断出这个藏英两文版本是分节还是不分节,或者到底有多少首;而刘希武译作出现的“60首”,是蓝本原有60首,还是受到于道泉译本的影响人为地分节为60首,这些问题都无法解答。
而这个版本到底是何物,是由哪家书社出版、出版年代如何、英文为何人所译,这个版本是否依然流行于世,就更无法考证了。
从刘希武译本的内容看来,它与于道泉所据的“拉萨本”小册子和“达斯本”都有不同。这个不同点有二:
第一,于道泉译本中有六首诗,刘希武本没有,这六首诗都是佛教内容的。这样,就说不清楚刘希武所据的藏英两文本原本没有,还是刘希武选择性的不译。如果原本没有,那么有两种可能,一是英文译者认为佛教内容与“情歌”路数不符,因此早早地剔除了,其二是这六首是混入于道泉看到的“拉萨本”小册子的。至于这六首是不是仓央嘉措原作,根本无法得知。
第二,刘希武译本的文字内容,显然过于“艳”,所用词句“情欲”成分过重,与于道泉译本的民歌风味大不相同。这有可能是英译本的文字风格所致,但更有可能的是出于刘希武的主观倾向,他对仓央嘉措的认识是“酣醉于文艺而视尊位如敝屣,其与南唐李煜何以异?”并认为他的诗“其事奇、其词丽、其意哀、其旨远”。
因此,刘希武译本不但文辞华丽、内容缠绵,而且少了几首佛教诗,造成了刘希武译本与于道泉译本的明显差异。
4无法认定的仓央嘉措原笔
除了刘希武依据的这个我们不得而知的神秘译本外,包括影响力极大的曾缄译本等,几乎都是依照于道泉译本而来。于道泉先生将早期诗作汉译本定为62节,因此后来者几乎都是按照这个体例重译,虽有增删,但大致数目以于道泉译本为准。
但是,于道泉这原始译本的62节,是否就是准确数目呢?事实上连他自己也解释不清,他在《译者小引》中曾明确地说:“下面这六十二节歌,据西藏的朋友说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是否是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几节是他所作,我们现在都无从考证。”
目前学界无法确定这60~70首诗歌中,哪些是仓央嘉措的原笔,又有哪些一定是伪作。不过,对这些伪作的来源,学界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有可能有些诗歌是仓央嘉措对当时民歌的记录,而非原创;第二,在后世流传过程中,有可能掺杂进一些内容相似、风格相近的民歌;第三,有些内容、诗意过于庸俗的作品,有可能是当年仓央嘉措的政敌伪造的,目的是以此证明他“不守清规”。
显然,第一种“伪作”,辨别起来比较困难,但并非无痕迹可寻。因为即使内容上看起来“相似”,但笔法、思想的矛盾之处,却无论如何也难避免的,这样的矛盾很难让人相信它们出于一人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