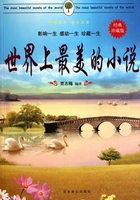【2】
光头们长出头发以后,给发生送来了很多锦旗,记者来采访发生,发生裹在自己的头发里浑身哆嗦。
“发生,你治好了这么多人,什么感觉?”记者问。
“疼……”发生哆嗦着说。
“我问的是你心理上有什么感觉?”记者启发道。
“怕……”发生上下两排牙齿互相敲打着,发出“咯咯咯咯”的声音。
记者不再问她了,转而问发生的爸爸:“您对自己的女儿这种行为有什么感觉?”
“我感到很骄傲。”发生的爸爸满面红光,说了很多,最后一挥手,“我们希望,全天下的人从此都不再为秃头而烦恼。”
他说这话的时候,发生的头发又一次竖得笔直,记者们咔嚓咔嚓拍下了这难得的场面。
发生现在变成最抢手的姑娘了,很多人来发生家提亲,但发生爸爸和妈妈都没答应,发生躲在门后看着那些挺不错的小伙子来了又走了,每当这个时候,她的呻吟声就停下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没听到发生的惨叫,那一定是有人来提亲了。
“我想快点出嫁。”发生有一天从她住在二楼的窗户探出头来对我说。我吃了一惊,她从来没主动跟我说过话。
“为什么?”我问。
她的头发从窗口垂了下来,在没有风的空气中卷曲成各种形状,我后退了一步。
“不知道。”她说。
发生的爸爸为了实现他在记者面前许下的豪言壮语,到电视上登了广告,还专门租了辆大客车专门往村里拉光头,车身上写着“生发专用车”,每次一拉就是满满一车,下来的全是光头,一片明晃晃的,让人眼前一亮。
发生的叫声更惨了,但我们也很快习惯了这更惨的叫声。
发生忙着被人剪头发,她爸爸和妈妈也怕别人偷剪她的头发,总是不放她出来,把她关在房里,每天吃核桃芝麻之类的东西,说是能养头发。
“我们帮帮发生吧。”春生说,这时她已经出嫁了。
我们不知道怎么帮她,再说都有自己的烦心事,顾不上她。春生说,如果发生没有了头发,就能出来玩了,也能嫁人了。
我始终没想明白嫁人和头发之间的关系,但春生年纪大,她这么说了,当然有道理。
【3】
当夜,我们几个从小一起玩大的人,偷偷跑到发生的窗户底下,小声叫着她的名字。她一边惨叫一边探出头来,乌黑的头发覆盖了整面墙壁,好像一大团水渍。
我们拽着发生的头发爬了上去,各自掏出剪刀,发生一看见剪刀,就猛然跳起来躲到床底下,我们怎么拽也拽不出来。
“疼!”她说。
“剪光了就不会疼了。”我说,“忍一忍。”
发生听了这话,就钻出来了。我们用一团布塞住发生的嘴,免得她叫得太厉害,被她爸爸听出不对劲来。
一人一把剪刀剪开了,发生的汗水流了一地,头发也没剪光。
我们继续剪,春生在旁边把剪下来的头发装到麻袋里,装满一袋就朝下扔,她爸爸妈妈在下边接着。
后来,发生不流汗了,开始从每个毛孔里流出血来。
“她要死了。”我赶紧松开她的嘴。
“别停。”发生呻吟着说,“剪!”
“你流血了。”我说。
“没事,剪!只要没头发了,死都愿意。”她说。
我不敢多看她流血的脸,又剪了几刀,最后她完全变成了血人,头发也没减少。我扔下剪刀,从窗口爬出去。大家都跟着我走了,我们没想杀人。
只有春生还在不停地剪着。
这晚发生死了,谁都不知道她怎么死的,我们也没说,春生家把发生的头发拿去卖了,也赚了一栋房子。春生给我们一人买了个随身听,我没要。
发生死了以后,按规矩本来是要火化的,但是她的头发还在继续长,比活着的时候还长得更快,发生爸把这事跟村长一说,大家一致同意让发生土葬。
【4】
追悼会的时候,全村人都去了,发生被白被单蒙住,放在灵堂后,用块白布帘子遮着。追悼会进行到一半,白布帘子慢慢地朝外鼓了出来,仿佛有很多人在帘子后朝外挤,鼓鼓囊囊地不成形状。大家吓得跑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要跑时,有个人看到了帘子底下伸出来的东西。那东西黑糊糊的,水一样遍地流着,一眼就看出来是头发。
发现是头发之后,大家也不再害怕了,索性揭开帘子,掀开了白被单。发生脸上的血已经被擦干净了,全身都被疯长的头发包住了。只这么一会儿的工夫,头发已经铺满了灵堂的地面和四壁,到处漆黑一片。发生爸爸说不用怕,吩咐一人拿着把剪刀,大家咔嚓咔嚓开剪,头发纷纷落地。不过这次发生没有再发出惨叫了。
头发总是剪不完,忙了一整晚,第二天就草草埋了。加厚的棺材,平常的铁锨凿上去都留不下一个印,发生刚躺进去没一会儿,还没起灵,棺材就被头发撑爆了,头发像蛇一般蜿蜒生长着。送葬的队伍前所未有地长,不是为了纪念发生,而是必须得有这么多人跟在后边,才能把头发及时剪断。前边的人抬着发生的遗体,匆忙上了山,挖了个深坑埋了。
发生的头发很快从地里冒了出来,黑油油的,渐渐覆盖了漫山遍野。人们找到了一条发财的好路,成群结队地上山割头发,然后拿去卖给村外秃头的人。发生的爸爸有些不高兴,但也没办法,发生已经死了,头发就不再只归他们一家所有。
我的衣服鞋子和零食,都是发生的头发换来的。
头发越长越多,渐渐地将其他的植物都挤死了,最后全村只剩下了头发,一走进村口,就看到一片漆黑在地面上飘拂。
春天的时候,那些头发上长了些白花,变成蒲公英般的絮,风一吹就四处飘。
起初,我们不知道这些白花是什么东西,随它们飘,反正眼睛看惯了黑色,来点白色也是不错的。
后来,这白花越来越多,到处都铺满了白花,连我们吃饭的碗里,喝水的杯里,都满是这种白花,每次喝水之前,都要先吹开。
过了一阵,很多人开始觉得身体发痒,痒得钻心,去医院看了皮肤科,什么毛病也没发现。
“痒死了。”春生说。她不断用指甲抠着自己的身体,我在她身上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她自己抠出来的血印子。
春生抠着抠着,忽然从嘴里喷出一把黑色的东西来。
那些东西虽然湿答答的粘在一起,还是能看出来是人的头发。她伸手连忙去拽,刚扯了一把,就捂住肚子叫疼。
接着,更多的头发涌了出来。
从她的眼睛里长出了头发。
从她的鼻孔里长出了头发。
从她的耳朵里长出了头发。
从她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里,都长出了头发。
春生变成了一个黑色的发球,完全看不到一点别的颜色,她在地上打滚嚎叫着,我远远跑开了。
一路上,很多这样黑色的发球发出凄惨的叫声。
我想跑回家,却认不出我自己的家在哪里。地上的头发把所有的房子都包了起来,有人从头发中伸出手来,向我求救,我也不敢去拉他。
我跑出村子后回头看看,已经看不见村子了,只望见一只巨大的黑茧一样的东西,把村子和村子里的人,把活着的春生和死了的发生,一起包了起来。
和我一起跑出来的还有几十个人,我们后来都只联系过一次。
每过一阵子,就会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我们中的一个人身体开始发痒,到医院里透视,发现他的内脏和血管里长出了细细的茸毛。
那些茸毛都长成了漆黑的头发,把他们团团包裹起来。
他们都是火化的。
最近,我也觉得身体开始发痒了。
但我已经没有打电话的必要,全部的人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我只能对着镜子说:“你也开始长头发了。”
镜子里的我,瞳孔中有些漆黑的东西在飘拂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