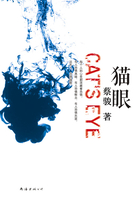次日。见面,玩笑,吃大餐。下午五点,来到半岛KTV。“唉,人生就是过把瘾嘛!”章子腾拿起了桌上的啤酒瓶,“我也来疯狂一回。”“要不,把白丽叫来?”艾利亚有意调侃章子腾。“不要叫她。我不想提这个人。”章子腾露出厌恶的样子,“说白了,她就是风骚。”听了章子腾的话,原先狂欢着的众人都没了言语,觉得非常尴尬,温度骤降了许多。突然,他又笑逐颜开,“来来来,大家唱歌唱歌,许诺你也去唱一首吧!”他的笑容很灿烂,那一瞬间我又觉得他很可怕了。一旁沉默着的张仲良,一直在衣兜里摸索着什么,老半天才摸索出来一张皱巴巴的纸。他小心翼翼地将其摊开,昏暗的灯光下,深情地注视着。过了一会儿,他很严肃地对我说,“许诺,我写了一首诗,帮我看看吧。”我为张仲良这种突然的真诚而感觉受宠若惊,正准备接过来,章子腾一把抢过了这张纸,嬉皮笑脸地念起来:“爱到当时已惘然……看不出来张仲良还写情诗呀!”“你有病啊!”张仲良愤怒地将纸张抢了回来,似乎章子腾戏谑的举动伤害了他最引以为豪的东西,“看不懂不要看!”他说着,一面将纸张递给了我。我认真地读了起来:爱到当时已惘然匆匆年华老,苒苒物华休。
梦醒霜天,问佳人何在?空自叹。八百里人生辗转,千年梦孤灯自守。望河山,锦绣万里俱滔滔。坐断山河情未果,爱到当时已惘然。读罢,我很想说点什么,但又无从开口。张仲良殷切地看着我。我只好硬着头皮说:“第二句,好像是柳永的词。而且,你没有真情实感啊。”他重复那句永恒不变的话:“你们都不理解我!”我们很一致地笑了起来。张仲良对人对事总怀着一股执著的抗拒。他的内心充满了不安全感,好像自己身陷泥沼而且周遭充满了诡诈。他的愤怒是我迄今为止见过的最为可爱的愤怒。只是这种愤怒随着时间的流逝越发孤独无告,形貌日渐消瘦。唱了五六个小时的歌,嗓子干涩冒烟。从KTV里出来,大家商量着何去何从。“我和张仲良打的回家。”王励励将手搭在了张仲良的肩膀上,“你说呢?”张仲良将王励励的手一甩:“车费一人一半!”“知道了,张仲良同学,你有够庸俗。”王励励露出无奈的神情,咧嘴笑道。“那我和艾利亚一起走。”宁小宇说,“那就这样了,回学校见!”大家三三两两地走了后,留下我和章子腾。“要不,我们来个二人约会?”章子腾开玩笑说。“不。”我毫无幽默感,“为什么是你呀。
”“难不成你还想那人是李松?”章子腾又开始拿我开涮了,“知道,今天他没来,你觉得失望极了。”“就算吧,随你怎么想。我一开始就没指望他会来。”在KTV门口站了一会儿,夜幕之下,是流线型的暗蓝深灰的建筑,冷色的灯光点缀其间。我们木然地看着这一方风景,章子腾说,“其实我常常觉得很失落。”“失落?”听他这么说,我莫名感动,像坚冰消融,锋刃泛出柔光。“留在这里上天府一中让我很失落。”章子腾说,“我可以出国,但我妈希望我留在他们身边。”“留在他们身边?”“你知道,”章子腾说,“即使我不考中考,他们也有能力把我送进天府一中。”话到这里,他似乎担心我不理解,强调道:“把我送进天府一中实在轻而易举。”“我相信。”我冷冷地说。心里也冷了。原来这才是他想说的。他并不想吐露衷肠,所谓失落不过是曲折的铺陈。我觉得好笑,你直说不就行了。想着,更觉得小路真实。一个不优秀的人,把仅有的平凡的真诚,全部奉献给了朋友。“再见。”我再也难以掩饰对章子腾的鄙夷,向路边停靠着的一辆的士走去。坐在车上,干冷的空气从车窗外不断地吹进来。我突然很想哭。拿出手机,打算给小路发一条短信。
我想告诉他我今天到了哪里,做了什么,什么又让我觉得很好笑。想着想着,却无从说起了。内心深处最细微的感受有时是无法传达的。即使可以表达,听者也未必理解。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小路。然而,我与小路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了。我们不可能永远像儿时那样嬉笑打闹,我们总会长大,各自面对不同的生活。从谈天说地一直到寥落短信,从寥落短信又到礼节问候。相隔遥远终会让我们失去共同的语言。那时,他说南,我说北,我们再友好地一起谈南北,徒劳坚持,悲哀而无味。接下来的一天,是我坐在书桌前,昏头昏脑地应付一张又一张的题卷。我骤然明白,那灯红酒绿已是昨日之灯,渐渐离我远去。回到学校,忙不迭地准备期末考试。这日子黑得透明。可不管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即使你心里蓄积满了暗沉,也总有人是活在明朗里的。模拟考排名出来了,李松已经是连续三次获得年级第一。鲁老盛赞不已,说,即使从全省的标准衡量,李松也是顶尖学生了。考天府一中实在是轻而易举,稍加巩固,进实验班也是稳当的。那时,李松就可以和各个学校的精英学生展开巅峰之争……她说得好不激昂,可过于富有感情的话往往带有太多的个人色彩。
所以我们大都赞叹几声表示羡慕,之后各忙各的事情,并不与鲁老附和。我们总是无法与她合拍。一年前,刚到这所学校时,我还满怀赤诚地琢磨,她对我们到底有什么要求。而今我终于懂得,她对我们的期望,那感觉好比万人列队,铿锵前行,气势恢弘却惨无个性。她说:我们追求卓越。而卓越只是一个符号,一类人,一种印象。理想中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向前。我们也在其中,昂首阔步,头上长空万里,内心却不禁愕然,只想问:Where are we?这种想法虽然超脱,但再次滑坡的成绩让我困顿重重。我诚惶诚恐地四处求教,到底该怎样提高成绩。“介绍学习经验?”王励励说,“说白了,就是夸大自己的苦难史。”我真是不该向他询问。无论什么时候和他对话,总感觉自身渺小到就快凄凉飘散。想来,章子腾和张仲良也一定好不到哪里去。最后,我不得不求教李松:“一直想知道,你这么努力学习,这种持久坚持的信念是从哪里来的呢?”“很多东西不用说,生活自然会告诉你。”李松放下了手中的笔,认真地回答,“比如放长假,我考了第一,却要背着沉重的物品赶车回家。而那些不努力考得不好的人却可以坐名车,吹空调,听着音乐悠然离开。
”“这是动力吗?”“应该说是一种震动。比如,看到芋头那种不学无术一无所知的人享受奢侈……”“不能这么说。芋头不见得这么糟糕。”我打断了他。“在我看来他就是这样。”李松说,“还有什么比成绩更能说明一切?”我很想辩驳,可是迈克鲁斯已经站在讲台上了。李松转了过去。“从中我明白,只有成绩可以改变处境。”我隐约听到他这么说。然后,他又有点叹息似的,“这也与我从小的生活有很大关系。”漫长的英语课。好不容易捱到下课铃响,迈克鲁斯卷起书走人,我迫不及待地追问李松:“能说得具体一些吗?”“具体一些啊……”他作出愁眉紧锁的沉思状。样子宛若面对一道数学难题。不过,如果他对待所有事都像在解数学题,那他的生活就太艰巨了。“那得从我爸讲起。”思考良久,李松就吐出了这么一句话来。片刻,他说:“我爸其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只可惜没有机会,没人帮他,要不然,他早成为声名远播的化学教育专家了。”“你爸教化学?”“他以前当过化学老师,带高中毕业班,只教了他们一年,那个班就拿了地区第一。”他很自豪,“不过后来我爸还是觉得没意思,当老师太累,也没什么钱。有人因为欣赏他,请他去北京发展。
真的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啊,只可惜我妈太不成事了,我爸最终没去成。”“你妈不让你爸去?”“不是不让,而是脱离了我爸的话,我们简直没法生活。我妈这么大的人了,根本不会照顾我,那时我又小,我爸工作忙的那阵,我严重营养不良。后来我爸对她失望了,决定亲自照顾我。我爸真的很辛苦,每天上完班就来接我,然后带着我去买菜,回家又忙着做饭。”李松补充道,“虽然我爸是那么的尽责,但我妈却真是一个糟透了的人。她不做饭,不工作,却成天在家里抱怨命运不济。”“懒是最重要的问题吗?”我问。他没有理会,自顾自地说,“在我小学毕业考试前的那天晚上,我和我爸在阳台上睡了一夜。最后他们离婚了。”“因为这些原因?”“是必然原因。”李松的语气非常严肃。“那你……受了一些影响?”我小心地斟酌着字句。“受了太大的影响。还有什么比经历更能改变一个人?我之所以沉闷木然,和经历是分不开的。”晚自习,我花了一节课的时间给李松写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字句我一直记得,并且今后也不大可能忘记。大体是说,希望他更阳光,更开朗,即使性格沉闷犹如榆木,也一定要开花。我希望他开花。也许是觉得像他这么优秀的人,不该拥有让人遗憾的性格。
也许是想要在字里行间表露某种心迹,但时光流逝,如今回想,这种初衷终于难辨其貌。但不管怎样,我最后终于是鼓起勇气,把写好的信交给了李松。他拿到信,有些惊讶,但并不急于打开。他翻前翻后地看了看信封,只是问:“我应该以怎样的心情对待这封信?”他的问话让我很吃惊。“当成一个同学友好的建议……当成白痴火星文也没关系。”李松没有说话。拇指摩挲了几下信封,点点头说:“我会好好看的。”只可惜,还没有等到回信,期末考试就来了。艾利亚坐在我后面。“你模拟考的数学是多少分?”数学考试前,她试探性地问。我没有回答,只是淡淡地笑。艾利亚看了,不再追问,显得惊疑甚至是敬佩了。少顷,她目光炯炯,“一定是130分以上吧?强人啊!太崇拜你了!”我又淡淡地笑。淡淡。
这是优生被问及成绩时脸上永远不变的神色。最近我频繁剽窃这种表情,只因为内心空洞一无所知,又不想让别人看出我肤浅尴尬,索性似笑非笑,倒让人觉出一种深邃。就为了被误会为优生的几秒钟的虚荣,整场考试,包括交卷的时候,我都不好意思回头。更重要的是,我的头重得抬不起来了。我完全考砸了。十五分的压轴题只着四字,曰:由题可知。四分一道的B卷填空题处处天窗。至于A卷,想必也是漏洞百出。回到教室,径自走到座位,周遭闹闹嚷嚷,我感觉自己又被一切边缘化了。热闹欢喜是他们的,而我脱离语言,脱离空气,脱离所有兀自难过着。不远处,白丽正叙述着自己是如何巧妙地逃过监考老师的眼睛,全盘照抄了王励励的答案。“英语语文就不谈了。数学,即使有那么些没看清,”她说,“上一百三十分还是没问题的。”周围感叹连连。
惊羡于白丽的魅力,能让王励励折服,也惊羡慕于她在所有事务前过人的应对技巧。甚至,连送衣服那件事,在哭过以后,她都不留痕迹地掩盖了。“如果没有一点家底,我是不会胡吹的。”她这样对所有人说。那种坚定的目光,那种令人信服的力量,是我所从未见过,也从未想象过的。记得鲁老说,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一个人不能光是努力,也要懂得方针。方针不仅是方法。更多是一种富于灵气的发现。白丽的脑袋是如此灵光,因此常让我有落后于时代的恐慌。前面,另一个人也趴着,趴在灯光的阴影里。苍白失落,寂寞无声。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她回头看了看我。我也看了看她。这一瞬间,我们又站在一起了。我和苏明理,又是朋友了。这种分分合合的友谊已经消褪尽了所有感动的气息,只是奇怪空虚,如此理解的两个人,为什么总在同一个世界上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