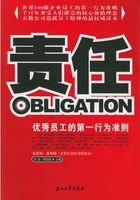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可能两次同时踏进同一条河流,因为水会流动,当踏进第二次时,已经不是同一条河流了。
但是她宋菀菀,二度重创在同一个人手里。
不知从何时开始,她的生活便进入了一个怪圈,绕不出,躲不掉,只能按照既定的轨迹前进。无论逃到哪里,最终都只会回到相同的原点。
那个原点,名为“苏翊”。
回到家关上房门,一头倒在床上,她用被单蒙住头,迷迷糊糊的睡了过去。这一觉睡得并不好,梦里群魔乱舞,张牙舞爪要向她扑来,她在延绵扭曲的空间里不停奔跑,不停奔跑,而路的尽头,却是一张巨大的、狞笑着的脸……
她是被外面嗡嗡的交谈声弄醒的。
缓缓睁开眼,房间里光线昏沉,很安静,窗外的天空深海般的墨蓝,夜空深处已是华灯初上之景。
她意识模糊的从床上爬起来,用脚摸索着拖鞋,外面的谈话声越来越清晰,有男有女,不时传出阵阵笑声,今天是老爸的生日,家里好像来了不少亲戚。
她恍恍惚惚的,打开房门……
一个身形挺拔的男人迎面走来,考究精致的衬衫西裤穿在他身上,真的足已用玉树临风、衣冠楚楚去形容,就是有一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给人精英的感觉。他注视着她的眼神,沉静不惊,温温淡淡,隐约带着笑。
“你醒了?出来吧,刚好要开饭了。”他缓步走近她。
菀菀怔怔地看着他,一股寒意毫无预兆的从脚底开始往上窜,沿着脊柱,一点一滴往上攀升。
她努力抑制住体内的寒冷,想往上扯动嘴角挤出个笑容,却怎样也做不到。无奈,她只好略低下头,一言不发的从他身边走过去。
没走几步,倏地,手臂上一紧,一股力道迫使她止住步伐,她扭过头看向身后的苏翊,不偏不倚的对上两道炯亮的目光。
他神情严肃地审视着她的脸,沉声道:“你怎么了。”这并非疑问句。
他的手掌心太暖太热,与她此时淋漓到极致的冰寒格格不入,她几乎是下意识就想挣脱他的钳制,这时母亲大人的叫喊声从大厅那侧传来:“苏翊,菀菀还没有起来吗?快点叫醒她,差不多开饭了!”
菀菀顺势抽回手臂,垂下眼帘,低头匆匆地说:“去吃饭吧。”别过脸,抬腿径直走向大厅,不再去看他的表情。
大厅里,偌大的桌子上坐满了人,有一半是特地前来道贺的亲戚,见到菀菀,不免又是一番寒暄,问完工作又问感情,场面十分热络。她强笑着,一一应对。
丰盛的菜肴全部上桌后,大家纷纷举箸开动,餐桌上以寿星宋爸爸为中心,不断有人举杯向他敬酒贺寿,一时间,推杯换盏,觥筹交错,敬酒与撞杯的声音不绝于耳。
菀菀坐在苏翊身边,安静地端着碗吃饭,像是被这派热闹喧哗的景象隔绝出来的个体。忽然像是有所感应,她扬眸看向身旁的男人,正正对上他投射而来的目光,她立即躲闪开来。然后,不知是不是她的错觉,周遭的气压,蓦然低沉了几分。
饭桌上各人酒酣耳热,高谈阔论。菀菀愣愣地注视着摆在她面前的装有白酒的小酒杯,忽地放下手中的筷子,举起酒杯起身对父亲大人说:“爸,今天是你的寿辰,作为女儿我敬你一杯,祝你身体健康,心想事成!”
“哈哈,好,干!”宋爸爸今晚红光满面,显然心情极佳,他举起酒杯与女儿碰了一下杯,便二话不说仰脖而干。
菀菀垂眼看着杯内清澈透明的液体,闭眼,仰头一饮而尽。她没有喝过白酒,一口气咽下去后,那辛辣刺激的口感令她感到不适,似是有一团烈火,顺着喉咙直烧进胃里,火辣辣翻腾。她嘴里辣得难受,但是身体迅速热了起来,心底的寒意,似乎也祛除了些。
于是,她又斟了一杯白酒,视线投向宋启寒,举起酒杯说:“哥,为了咱们宋家第一个小孙儿,我敬你一杯!祝你和嫂子生活和和美美,生个健康聪明又可爱的小宝宝!”说完,又是一饮而尽。
宋启寒端着酒杯与妻子对看一眼,仰头,干了一杯。
第二杯烧酒下肚,一道热流窜向四肢八骸,菀菀感到烫热无比,全身上下火烧一样难受。酒意上涌,白皙的脸颊腾起两团红晕,唇色亦是娇艳绝伦,眼神却开始有些飘悠。
“好了,菀菀,不要喝太多了,米酒后劲很足你喝不惯,你以茶代酒吧。”宋妈妈察觉到女儿已有几分醉态,不由的出言提醒。
“我、我没事的,这点酒,喝不倒我。”菀菀执拗的回道,又往杯里倒满白酒,站起来的时候,忽然有一秒钟的目眩,她晃悠了两下稳住身体,然后扬举酒杯向着对面一个中年男人说道:“叔叔,这一杯菀菀敬你,祝你生意兴隆,合家安康!”仰起头一干而尽,末了又举起一杯对中年男人身边的妇人说:“婶婶,菀菀祝你心想事成,祝愿堂弟能考上第一志愿!”不待众人反应,她举起小酒杯,迅速吞了下去。
连续猛灌了几杯白酒,她的头好像塞了块石头变得又重又沉,身体却热得快要飘起来,飘飘然的不受自己控制。依稀中母亲大人好像板起脸说了什么,但是浓浓白雾源源不绝的笼罩她的意识,她对周围环境的感知力越来越弱……一阵天旋地转,眼前的人影从一个变成两个,越来越多,重重叠叠……
在她快要倒下的时候,一股坚实沉稳的力量从后面托住了她,她茫茫然看过去。
男人的脸色很难看,他盯着她,语气是从未有过的严厉:“你别闹了。”
醉意朦胧,他的声音竟像是从天边飘来,他的五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难过的情绪,就这么一下子涌上了菀菀的心头。
不是类似于高三那年发现被欺骗时的难过,而是一种,更为深沉的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