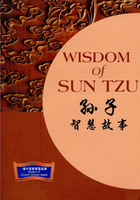第72章 夜半鬼抽风
果然是山珍野味。
“好地方就是好地方,菜色就惹人爱。可这是什么地方?”万全策开心地道。
尉迟风对他笑了笑,“这里叫耿马,位于云南的西南部,西邻缅甸。有汉、傣、佤、拉祜、彝族、布郎、景颇、傈僳、德昂、回、白等民族。谁有本事,可以找个少数民族姑娘,以后就可以天天山珍野味了。”
“呵呵,像我虎头虎脑的,让人家看上的机会挺少。”万全策笑道。
“我尖腮猴脸,绝不是人家的白马王子。”郭超常实话实说“是啊,我们都黑不溜秋的,野人一个,想让人家看上眼都很难。”蔡如柏风趣地说,“倒是老大、老二他们,一个个白脸王子,会被少数民族姑娘追死。”
尉迟风笑笑,“那倒不一定,情人眼里出王子。何况这里是浪漫之乡。知道这里为什么叫耿马吗?”耿马“的”耿“系傣语,意为”地方“、”地域“。”马“为汉语。即”有马的地方“或”跟着马找到的地方“。而”耿马“的傣语直译为”勐相耿坎“,意为跟随白马寻觅到的黄金宝石之地。有意思吧?”
“嗯嗯,不错,是不错。白马溜溜的地方哦。”众人都道。
“酒来了,这酒更不错。”胖厨师抱来一瓮酒,手一举一托,白花花的酒便哗哗而出,落入各人面前的碗里。眨眼功夫,十四碗酒便斟定,且滴不漏。
这一手仙摇酒瓮之功,就令人大开眼界。
范庭兰就禁不住道,“好俊的功夫。”
“嘿嘿,见笑见笑。”胖厨师说罢,也入了席。
尉迟风便对大家介绍道,“我们这位大厨姓郑,名得泉,芳龄二十有五。谁不嫌他胖,都可以沾一下他的油光。”
“这恐怕得让给农峻了。瞧他瘦的像竹杆,风吹就倒似的。”范庭兰望着刘农峻笑道。
刘农峻一脸遗憾地答,“可惜我是油泡都不肥的人。郑厨即使有意,我也无福消受啊。”
众人开心地笑。
尉迟风端了酒碗,站了起身,“各位,我们终于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如果说有点损伤的话,那也是被蚊叮蚂蝗咬,痛痛痒痒就过去了。为这顺利,我先敬大家一碗酒。”
说吧,一气喝下。
尉迟风开了场,接下来,自然就热闹了。酒过三巡,就打开了酒仗。
这酒仗打到深夜方散。
谁都好像没醉,有的只是七八成酒意的样子。
龚破夭心里却清楚得很,彭壁生和赵卓宾说去上茅房,实则是借机呕出胃里的酒水。方法很简单,用食指伸入嘴里,直顶喉咙头,就会一阵反胃,什么东西都会倾吐而出。这种方法简单是简单,却容易伤身体。但在酒席上,谁都愿伤身体,而不愿伤感情,更不愿伤自己的威严。
这是酒场的游戏规则,只要你不是当场醉倒,现场直播,还能坚持着喝下去,就不算你醉。哪怕到最后,你只能抿一抿酒碗,或者借着酒意,将碗中的酒晃出三分之一,也不会有人跟你计较。这是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这酒场上,从来就没有常胜将军,说不定哪天就会轮到你。
因此,借上茅房去吐的,或出门去透透夜风的,大家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心知肚明就算了。
彭壁生和赵卓宾吐了回来,赵卓宾是静静地端坐着,不敢再主动出击。彭壁生倒好,端起酒碗又挑起了战争。
他这是空肚喝酒,是酒家的大忌。
范庭兰用脚踢他也不顶用,他冲着尉迟风就嚷,“为了你让我有机会以步代车,这碗酒怎么说也得敬你。”
嘿,他还清醒,没忘记自己是汽车团的人。
尉迟风自然不能推,只能站起来应战。
一碗喝下,彭壁生又继续点将,“农峻兄,我最看不惯的是你瘦得像竹,飘动如云,生来就好像不用坐我开的车一样。但凭你这么不给面子,就得罚你一碗。”
“唉,壁生,你以为我想瘦的?是老天喜欢肥瘦皆宜,才让我当代表的嘛。咱也别挑肥拣瘦,为咱这肥瘦有缘相聚,这酒就喝了。”刘农峻知道彭壁生爽快,自己也没半点犹豫。
这么一路挑战下来,彭壁生竟也喝了七八碗。
大家方知,他彭壁生的胃,是可以持续发展的胃,生态平衡得比较好。
尽管都喝得脸红的脸红,脸青的脸青,有的眼皮已经降下帷幕,有的已经声高八度,但都保持着军人的坐姿,不让自己的身子东歪西倒。
席散,范庭兰欲扶彭壁生,彭壁生推开他的手,“老范,你以为我彭壁生这么差的?虽不敢说海量,溪量是有的吧?”
溪水长流。难怪他吐了还能继续战斗。
坐着,大家都可以保持良好的坐姿,双脚踏地,要撑起身子,迈出坚定的军人步伐,那就不可能了。
走没几步,谁的脚飘,谁的脚浮,一眼就看得出来。
飘的、摇的、晃的,就有如浪上的帆。
但帆不会倒。
坚持到这个时候,谁都会继续坚持下去,回到自己可爱的窝。
进了房里,离开了别人的视线,彭壁生衣服也没脱,蹬掉鞋子,就爬上床,仰天八叉地一躺,拉开被子盖到自己身上。
龚破夭和范庭兰相视一笑。
也就笑一笑的功夫,如雷的呼噜声,就从彭壁生鼻头、嘴巴爆发而出。
“他也入睡得太快了吧?”范庭兰不由道。
“呵,有福之人,说睡就睡的。”龚破夭笑说。
范庭兰却笑不起来,“他这如雷贯耳,叫我们怎么睡?”
“没事,就当听春雷吧。”龚破夭边说,边扫视着房子。
“想找什么?”范庭兰不由问。
“蚊帐。”
“没有,我早检查过了。”范庭兰道,已经做好了喂山蚊的样子似的。
“嗯,那你先睡,我出去一下。”龚破夭丢下这话,人已飘出了房外。
脱了衣服,范庭兰也爬上了床,盖上了被子。
说是怕彭壁生的呼噜声,那是正常的情况下说的。这十多天的长途跋涉,本就累得不行,加上酒意一涌,没两分钟,范庭兰的眼皮就开始打架。想睁开一下,都感到沉如千斤之石,无力再睁。不消三分钟,他也睡着了。
龚破夭出门,并非去找尉迟风。
没有蚊帐,他觉得这不是尉迟风的大意,而是故意安排。
既然是故意安排,他相信尉迟风自然有理。
出了门,龚破夭就抽了抽鼻子,夜风很凉,在凉凉的夜风里,他寻觅到一缕野艾的气息。
气息从溪上方传来。
身子飘了过去,龚破夭拔了一大把野艾。野艾已半干。
带着艾草回到房间,龚破夭看了一眼床上的彭壁生和范庭兰,差点没叫出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