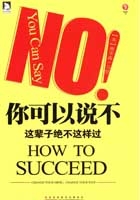整个上午,我们没有联系。我没有想过要打电话给他,但吃午饭之前还是忍不住特别注意了一下手机,偶尔离开座位也总是记得随身带着。到了下午,天气又变得阴沉,四点钟的时候下了一阵小雪,从办公室的窗户看出去,往来的行人和车辆很快把刚刚积起来的一点薄雪弄脏,街道显得潮湿抑郁。也正是那个钟点,Lyle打电话过来,打了招呼,聊了聊天气,又说了些关于Caresse的事情。我在他似乎要切入正题之前打断他,虽然我也不能确定,究竟有没有“正题”,又或者是什么样的“正题”。
不管怎么样,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今晚你不要来了。”
他没有立刻回答,我有点多余地解释:“是因为工作上的事情,晚上我还要写点东西。还有我们两个作息习惯不一样,我十一点钟要睡觉。”
他在电话那头笑了一下,说他能理解。我们互相说了声拜拜,挂断电话之前,他突然叫住我,说:“我拿走了你那里一样东西,那个水晶球,今天早上Caresse要玩儿,我可能把发条弄坏了,我会找人修理。”
“那个……坏了很久了。”
“不管怎么说,我会找人修理。”最后,他这么说。
晚上回到家里,又是我一个人了。前一天推来转去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客厅茶几上,上面没有贴新的留言。在门口换鞋子的时候远远地看了一眼,碰都没碰一下。第二天早晨吃早饭的时候,我站在厨房的案台那里又看到它,突然想“干脆签了算了”,找了一圈没找到笔,赶着出门,于是又一次作罢。
在那之后,我们时不时地通一次电话,问一句:“Caresse今天说什么了?”这是那段时间打电话必讲的话,就好像说“你好”一样。因为小孩子正在学说话,也因为我们都需要掩护吧。
圣诞节假期前的一个晚上,既不是节日也不是周末,下班之后,我跟一帮同事去吃泰国菜,散得很早,还不到九点钟。在节日气氛和难得的兴奋心情的驱使下,我站在第二大道和东第六街的路口给他打了个电话。拨号码之前犹豫了一下,不知道是打手机呢还是打家里的电话,最后还是打了座机。没什么原因,或者说原因很复杂,因为我明知道那个钟点,他很可能不在家的。但结果却跟我明知道的不一样,就是他接的电话,听到我的声音,第一句话就说:“Caresse刚刚睡着了。”
“我正好在附近,本来想过去看看她的。”我回答,其实一点都不近,而且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打这个电话。
还是老习惯,先来聊一下孩子。不过,跟老习惯不同的是,他告诉我他一会儿还要出门,问我:“一起喝点东西好不好?”我答应了。
于是没有来由的,我们又开始约会了。单纯的约会,就像刚刚认识的男女朋友一样。有的时候他来接我,有时我自己到约好的地方去。下午两点钟的咖啡,九点钟的晚餐,或者深夜的鸡尾酒,然后他送我回家。牵手、亲吻,海阔天空地聊天。我们常常聊起Caresse,刚刚还在调情,下一秒钟就可能在说那个小丫头今天又干了什么淘气的事情。奇怪的是,一点都不扫兴,这样的对话似乎把普通的男女之事变成一些别的东西,即不是单纯的罗曼史,又不太家庭。似乎,世界如此之大,几十亿男男女女,而我跟他,仅仅因为一个粉红脸蛋儿的小女孩儿,有了挥斩不断的联系。
一月中旬的一天,我跟Lyle约在公园大道和二十街那边的一间酒吧,刚刚坐下来,就有一伙人过来跟他打招呼,其中的一个叫Kelly Sandler的女人在旁边站定跟他讲了很长时间话,从游艇派对,说到曼哈顿港口的驳船位,说来说去无非是那几句,却就是一幅不打算走的样子。
我对她说:“不如坐下来说吧。”
女人作出夸张的表情,问:“你不介意吧?”
“当然不。”我回答,笑着看了Lyle一眼,他也正好在看我,咬了一下嘴唇,一个转瞬即逝的自嘲的笑容。
我在旁边听他们说,每次他想结束掉谈话,我就想出点话题来留住这个Kelly Sandler。我不看他,但感觉得到他的目光越来越久地落在我身上。快到午夜的时候,他伸手过来握住我放在台面上的手,对Kelly说:“我们恐怕要走了,”转头又跟我说,“这两天Caresse半夜里总是会醒一次。我哄她睡觉的,她醒过来总会找我。”
Kelly有点意外地看着我们,而我继续恶作剧,跟她解释:“我往巴特利公园方向,他去上东城,你住在哪里?和我合乘一辆出租车,或者坐他的车走。”
一点也不意外,Kelly欣欣然地跟Lyle说:“不介意的话,可不可以麻烦你送我到东五十七街的四季酒店?”
三个人走出酒吧,我在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Lyle抢先走过来,给了出租车司机一张钞票,对他说:“对不起,不需要用车了。”然后抓住我的胳膊,让我也坐上他的车子。三个人坐定,他对司机说先到“四季”。我说不要,先送我好不好?先到巴特利公园。他笑了一下,说好的,先到巴特利公园,先送你回去。
车厢里光线幽暗,我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从他的声音里面也听不出来他的心思。片刻之后,我在家门口下车,隔着车窗跟他们说拜拜。我一个人上楼,没有卸妆也没换衣服,在抽水马桶的盖板上面坐了很久。我根本不知道自己算是赢了,还是玩过了火。悸动、心跳、试探、细微的眼神和短暂的笑容,那些早已过去的感觉又一次回来,却又跟从前的不同。没有难过,没有苦涩,没有患得患失,所有的不确定让我每分钟心跳一百二十次,却依然感觉良好。
好像过了很久,又像是一转眼的功夫,门铃响了。我跑过去直接按了开门键,因为我知道那只可能是他。我打开房门看着电梯数字的变换,等他上来。电梯门打开,他走进我的房间。没有讲话,抱住我,吻我。
那天晚上,我们又在一起了。
不知道是凌晨几点钟,应该是夜里最黑最冷的时候,他闭着眼睛说:“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没有分歧。”
“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其实不喜欢开着灯。”
他伸手关掉床头灯,在黑暗里抱住我,冬天的夜晚,这样的拥抱总显得比实际上更温暖更不可缺少。
我忍不住开玩笑,只为了破坏气氛。亲了一下他的手背,说:“你要干什么,我不管,但是答应我,不要为其他女人做同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
“把手放在她的头和床头板之间。”话没说完就笑得把头埋进被子里。
他没有跟着笑,把我拉出来,没来由地对我说: “e,我不是那种喜欢退回到某个时间,重新来过的人。不过,这件事不一样,因为你不一样。我希望我们可以再试一次。我需要你。”
黑暗里,我看不到他的眼神或是表情,只感觉得到眼泪从自己的眼角沁出来,听到自己满不在乎地回答:“有一天,你老了,当你觉得需要一个人,真的需要,二十四小时的需要,百分之一百的要,你可以给我打个电话,如果运气好我刚好空窗,我会查一下Agenda,找个时间,跟你出去。”
很久他没有讲话,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睡着了,背过身很轻说了一句:“我需要时间,我需要想一下。”
仅仅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被闹钟吵醒。我起来穿衣服,让他继续睡,喜欢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但他坚持要陪我走到公司,一路上帮我拿着手袋。那天,我刚好拿了一个没有拉链封口的托特包,路上很多人,而他就那样随随便便的垂着手拎着,我每隔一会儿就要朝他手里看一眼,生怕到公司之后发现钱包或是电话被偷了。我在公司楼下的咖啡馆请他吃早饭,因为那是一个难得的晴天,我们就站在门口,冬天早晨的冷风里面,一杯咖啡,一只pain au chacolat。喝咖啡的时候,我偷偷地抬头看他,他的打扮一如既往的简单、干净,仿佛不着痕迹般地给人留下那么点儿特别的印象。一个同事正好经过,跑过来跟我打招呼。向她介绍Lyle的时候,我只说了他的名字,突然发现没办法告诉别人,我们现在,究竟算是什么?因为我自己也一无所知。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我没有力气把他赶走,因为我还爱他,只是没有从前那么爱了。就像现在,我一样努力工作,但再也不会像从前那样投入了。
就是那一周的周末,他送Caresse到我这里来。我在厨房里洗水果,他拿了一本图画书指着上面的苹果蛋糕洋娃娃,问Caresse这个要不要,那个又是什么。我端着一盘草莓走到他们身边,他抬头看着我,嘴里却是问Caresse的问题:“妈咪生个弟弟给你玩好不好?”
那可能只是句玩笑话,我却条件反射似的回答:“我刚刚跟老板说过,我的五年计划里没有生孩子。”说完笑了一下,想表现得满不在乎,却更像是尴尬。
Caresse又一次帮我解了围。一般情况下,她对“给你个什么什么好不好?”这样句式的问题,一律是点头的,不知道为什么对“弟弟”这个玩意儿却不买账,一个劲儿摇头,说一连串“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我知道父子间的那种感情对Lyle来说意味着很多东西,他应该是真的想要一个儿子。不过,我听到那个问题的时候,胃都要抽筋了,我不后悔生Caresse,也想念胎儿在肚子里踢打翻身的感觉,但是,在那段怀孕到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片断,对我来说像噩梦一样不愿意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