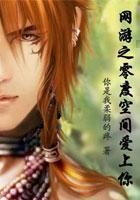第二天下班回家,Caresse已经送回来了。那个礼拜剩下的几天,我们都没有联系。直到周末他过来接孩子,我们在巴特利公园的游戏场上匆匆见了一面。Nick也在,等我送走了Caresse一起去健身。三个人互相打了招呼,其他几乎什么也没说。不过,只要有Caresse在场,气氛总不会太尴尬。我禁不住觉得两个成年人老是拿小孩子当掩护,蛮好笑的。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我很想跟他说些什么,甚至有点后悔把Nick也一起叫来了。但如果真的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恐怕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
Lyle带着Caresse告别走了,我坐Nick的车子去健身房,在车上说起两个礼拜之后的公司派对,地点在公司附近一个名叫“Balloon”的夜店里。Nick告诉我那是很“潮”的地方,平常要进去得排很长的队,进了大门还要等位子。看他蛮感兴趣的样子,我问他要不要一起去,我可以带一个人。
“你没有约会?”他问我。
我摇摇头回答:“没有。”
“你这样不行啊。”他开始语重心长,“不带小孩的时候应该多出去出去,不要只跟我去健身房,减肥也不要减过头了,变成Keira Knightley那样没胸没屁股的就不好了。”
我说你那么多废话干吗,要去去,不去拉倒。他答应去了。
又过了一个礼拜,Lyle把Caresse送回我这里,走之前跟她说拜拜的时候,随口提起下周要出去度假,新西兰的什么地方,因为Sandra想去。他走之后,我关上门,对着门板说了句“Bon voyage”。随便吧,随便到哪里去。那个地方名字怪怪的,我几乎立刻就忘了。而我和他之间也再不会有什么了。
新的一个礼拜开始,天气阴晴不定,冬天的味道渐渐浓了。第一个工作日的晨会上,照例是经济学家、行业研究员挨着个儿地发言,有人提到新西兰,能源、食品、旅游……我走神了,手里拿着水笔在记事本上乱画,坐我旁边的同事以为我在想跟他差不多的事情,侧过头轻声对我感叹:“看这里的破天气,帕里格里格岛现在华氏八十度,晴朗无云,沙滩白的晃眼,风速每小时二十公里,冲浪的好地方……”我对他做了个尴尬的笑脸,他耸耸肩,低头继续看他的手机。帕里格里格,就是这个名字,我又想起来了,也可能根本就没忘记。
星期三,Nick到华尔街附近办事,约我一起吃了午饭。吃完饭,我拉他陪我去买星期五派对上穿的衣服,两个人一路逛到布罗德路。我在沿街一家店里看上一条深灰色的裙子,穿上非常合身,午饭多吃一口都有可能拉不上拉链。店员在一旁很夸张的对Nick说,你女朋友的身材很好啊,换了旁人,我都不敢把这条裙子拿出来给她试啊,巴拉巴拉一堆生意经。
Nick也夸张地回答说,这不是我女朋友啊,我没有那样的荣幸啊。我只是她的健身教练加血拼顾问啦。
等店员走开了,我对着穿衣镜跟他说:“不如我们开始约会吧,我是说真的约会,星期五晚上就算是第一次。”
“第一次跟第二次两年多以前都已经约过了,要约也得从第三次开始,谈谈身体谈谈渴望,我送你回家,说不定还想跟你上去,到你卧室里坐一下……”他还是贫嘴。
“我说认真的。”我打断他。
安静了很久之后,他开口说:“我想我们应该再等一等。”
“是你催我开始约会的,还等什么?”
“A closure.”
“已经结束了。”
“我愿意相信你,不过这种事情旁边的人总是比当事人看得更清楚。”
“你还喜欢我吗?”
“喜欢。”
“喜欢我什么?”
“有点驼背,笑起来挺可爱的。”
“驼背也算优点?”
“算吧,我蛮喜欢的。”
“那周末的晚会你还当不当我的plus one?”
“当然当啦,这不就是朋友通常做的事情嘛,我不会让你落单的。”他看着我回答,然后又让我转过去让他看看后面,仔细端详之后关照我,“你这条裙子里面一定要穿thong的。”
我脸红了。
结账离开那家铺子的时候,他替我开门,同时轻声对我说对不起,他没答应跟我约会,因为他这个人“认真起来还蛮认真的” 。
我心无杂念地工作,一直到周五。因为逢到周末,晚上又有活动,整个下午办公室里都有些人心涣散的味道,老板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离下班还有半小时,已经有人翘班走了。我照样还是六点三十分左右离开公司,回家正好可以跟Caresse一起吃饭。看她拿着小勺子把西兰花、虾仁、蛋黄还有米饭舀起来,送进嘴里,笨笨的,却又那么认真,就是我一天当中遇到的最最动人最最有趣的事情了。
差不多八点钟,Nick过来接我。我还穿着运动衫裤坐在Caresse的小床边上给她讲睡前必听的故事——《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小孩子很奇怪的,有些东西不知道怎么的,机缘巧合印进她脑子里,就再也忘不了了。我给她讲过《白雪公主》、《小红帽》、《冰雪皇后》等等,全都及不过Lyle那个磕磕巴巴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
Nick站在卧室门边上看了我们一会儿,静静的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Caresse很敏感,总觉得房间里多了个人,一会儿朝那里看看,一会儿又对他笑一下。直到我挥手把他赶走,让他到客厅里等我,小姑娘方才安静下来听故事。等故事讲到阿里巴巴发了财,她也已经闭上眼睛,渐渐睡熟了。我用最快的速度换了衣服,化了妆,跟Nick出发。Claudia留下来看孩子,我答应她十一点之前肯定回来。老实说,我已经懒得出去了,巴不得洗完澡坐在床上看书或者干脆关灯睡觉。但Nick已经来了,而且,他的话还是有些道理的,我应该开始自己的生活,除了女儿,除了工作,除了Lyle之外的生活。毕竟有人早就走远了,远到南半球去了。
走出我住的那栋楼,我就发觉自己忘记带粉盒和手机了,开始觉得麻烦没有回去拿,等车子开出一段路又开始担心,家里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Claudia又找不到我。等到了Balloon,走了几步路,脚上新鞋怎么穿怎么别扭,每一步都像是踮着脚尖在走路。合规部的老板,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老远看到我跑过来跟我打招呼,因为夜店里很吵,他凑得很近,口水都喷我脸上了……事情林林总总,总之是一切都不顺意。我莫名其妙,自己怎么又会退回到这个样子,在他身边时的样子。
公司的派对总是那个样子,有人只为出风头玩得很疯,有人公开了办公室里的暗恋,也有一些只是想见一下高层,除此之外的那一些就是走一下过场而已,表示自己还算合群,多少还有那么一点团队精神。我恐怕就是那最后一种。两杯Martini,两小块蛋糕,跟所有认识的人打了招呼,尚不到十点钟。我借Nick的手机打家里的电话,Claudia说她在餐厅看电视,小孩睡得很好,没什么事情。没什么理由让我提早告辞了,于是只好照原定计划混到十点半再走人。
临走去跟老板说拜拜,他老人家最后还不忘记用带着法国味儿的英文损我两句:“这么早走?你还不到三十岁吧,打起精神来啊,e,漂亮的青蛙烫死了可惜啊。”他总喜欢说那个老掉了牙的,关于温水里的青蛙的比喻。
我跟Nick说,他要是愿意多待一会儿,我就自己回去。其实心里很清楚,他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他总会说:“你是女的,外面天那么黑,无论如何我得送你回去。”等等等等。或者就像今晚这样,摇摇头,默不做声地伸手搭着我肩膀,陪我离开。出了Balloon,我们走了一段路到他停车的地方。路上吹到冷风,上车之后,头疼了一路。我头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聊天开玩笑的情绪。直到车子开到我家楼下,挡风玻璃印上了细细的雨丝,他轻声骂了一句:“Damn,下雨了。”然后对我说,“我不送你上去了,替我亲一下宝宝。”
我跟他道别,下车低头跑进去,雨滴落在身上感觉冰冷。乘电梯到家门口,开门进去,客厅里没人,Claudia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在餐厅看电视,安安静静的,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角落里的一盏小灯还开着。听见我开门的声音,卧室里有人走出来,转过那条短短的走廊,在我眼前站定,离我不过五米的距离,对我说:“嘿。”是Lyle。
我觉得又累头又痛,愣了一下,或者可以说愣了很久,直到脱掉高跟鞋,放下手包,把钥匙扔进门口桌子上的小碗里,才终于开口问他:“你怎么在这里?Claudia呢?”
“我让她回去了。”他回答,“我想看看Caresse,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没关系。”他很客气,我也很客气,“你看到她了,我昨天抱她称体重,有十二公斤了。我就快抱不动她了。”
我又拿出小孩子的事情来做掩护,他也很配合地附和,然后走过来,指指茶几上的一个瓶子说:“这个是给你的。”
我拿起来看了看,澳洲产的红葡萄酒,应该是旅行纪念品。“新西兰好玩吗?”放下酒瓶,我问他。
“我不太清楚。”他回答,“十几个小时的飞机,美居酒店45,然后又是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基本就是这样。”
“你?美居?”我撇撇嘴,笑了一下。很难把他跟那种实惠型的酒店联系在一起。
他没理会我的表情,朝门口走过去,像是要走了,快到门边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问:“你穿的是thong吗?”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又问了一遍。
我禁不住笑了一下,回答:“对,眼光真好。”这方面他总是很在行的。
“今晚是在跟什么人约会吗?”他站在原地问我。
“为什么这么问?”我反问。
他没说话,笑了一下。我穿不惯thong的,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只有在床上才穿,最长不超过半小时。他还记得的。
“裙子太贴身,所以才穿的。今晚是公司聚会。”我解释,话说出口才想起来根本没必要跟他解释。
“很漂亮。”
“谢谢。”
有那么一会儿工夫,两个人都不再讲话。他没说再见,也没有伸手去开门,突然开口说:“我在飞机起飞之前跟Sandra分手了。”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点也不意外,听他继续说完那个句子,“后来才发觉自己做了件大蠢事,因为有托运的行李,我没办法下飞机,十几个小时一直飞到奥克兰,最早一个返程的直飞航班是第二天上午,让给她了,我在机场旁边的‘美居’又待了一天,然后转了三次机回来。”
一段不长不短的沉默之后,我叹了口气评价:“这是你活该。”
他耸耸肩,回答:“随你怎么说吧,酒是我在布里斯班转机的时候买的,在那里等了四个小时。”
“我不喜欢喝酒的,你可能忘了。”
“我没忘,只是不知道买什么好。而且,我想你可能变了,事实上,这一年里面,你的确变了许多。”
“变好了,还是坏了?”
“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面对你,我从来没有什么判断力。”
“如果你不介意,我拿去送给我老板好了,”我打断他,不让他说下去,突然很想说说笑话,好让气氛正常点,“喝得越多,老得越快,我的健身教练说的。”
“我一向觉得运动做得越多,死得越快。他还说过什么?你的健身教练。”
我又想出来一句:“有腹肌的女人才有好的爱情。我想他指的其实是‘做爱’。”说完就笑了。
他没笑,走回我身边,好像没听懂我说的笑话,问我:“你有吗?”
“有什么?腹肌还是爱情?”
他低下头,嘴唇几乎贴在我的嘴上,说:“两样都是。”
可能只是为了验证健身教练的话是不是正确,可能是因为那条裙子,或者是裙子下面少到不能再少的内衣,也可能只是因为他身上勾起回忆的味道,我吻了他。
亲吻的间隙,他贴着我的嘴唇说:“你可能不能原谅发生过的事情,但是,你可以原谅我,请原谅我,原谅我,你一定要原谅我……”
恳求或者命令,不管究竟是什么,反正是起作用了。在他说出那个句子之后,一切失去控制。那个十二月的深夜,离婚三个月之后,我们在客厅的沙发上做爱。为了不吵醒Caresse,两个人都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几乎不像真的发生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