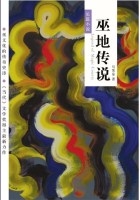不过,我还是不够美国化,完全没想到他说Double Date是当真的。一个多礼拜之后,星期五的傍晚,他打电话过来说,周末他来领Caresse的时候,会把他的约会对象一起带来。
“那一起吃晚饭吧。”我还没下班,用办公室里通常的那种口气大方干脆地发出邀请。
“好的,你也带上你的约会对象。”
我曾经以为这种情形之下,一定得找个英俊体面自信满满、在前夫面前不落下风、决不露怯的男人,才过得去。但真的到了这个份儿上,倒变得极其坦然。我告诉他:“我没什么特别的交往对象。就我一个人。吃意大利菜好吗?Caresse可以吃面条,我来定位子。”
定下约会之后,我在心里盘算了几次,该怎么打扮自己,怎么跟他的新女友聊天,想不出个头绪,最后决定一切随意。星期天早上,我还是平常周末的打扮,深灰色开衫加牛仔裤,头发随随便便梳了个马尾。下午三点多,门铃响了,我在门禁系统的监视器里第一次看到他的新女友,站在他身后。门开了之后,他开门,退到一边,让她先进来,这种细节他从来不会出错,得体而动人。匆匆一眼看起来,她非常美,深色头发长到锁骨处,带一点卷,向里弯成一个优美的弧度。我突然有点后悔没化妆,没吹头发,也没换件好看点的衣服。
开了门见到了真人,倒没有第一印象那么惊艳。她不过分年轻,也不老,三十岁左右,最好的年纪。身材很好,至少有五尺十寸高,还穿着高跟鞋,而我脚上只有双圆点图案的袜子,没穿鞋,看起来比她矮了一大截。
Caresse一听到门铃声就很激动的站在门口等着看有谁会进来,开门看到爸爸高兴得直跺脚。
“e,这是Sandra。”Lyle对我说,转头又告诉Sandra我的名字。
两个女人握手。Sandra蹲下来拉拉Caresse的小手,给了她一只米棕色的泰迪熊。
Caresse喜欢小熊,似乎也蛮喜欢爸爸的新女友,一开始就没什么戒备,很听话地让说“你好”就说“你好”,让握手就握手。过了一会儿还拿了自己的照相簿去给她看,小手搭在她的膝盖上面,一点也不陌生的样子。
我笑着对Sandra说:“Caresse喜欢年轻漂亮的姑娘。除了你,只有这里十一楼一个十三岁的女孩子,她第一次见到就很喜欢。”话说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吹捧得有点过头了,特别是那句“十三岁”。Lyle看了我一眼,没有笑,却足以让我知道他在嘲笑我,我满不在乎地看回去,Sandra听了倒很高兴,尽管穿了丝袜连衣裙不很方便,还是跪在地上陪Caresse玩。Caresse给她一块磁性板,她想画只兔子上去,描来描去的画的却像只老鼠。很普通嘛,我暗地里又刻薄起来,莫名其妙的有点得意。
晚饭之前,我们带着Caresse到附近的游戏场去玩。Lyle抱着她去玩滑梯,我和Sandra站在边上聊了几句,她说英语的时候,有些词会带一种特别的转音,有点怪却很好听。她对我说,她其实是德国人,在第三十二街上的一家出版公司工作。还告诉我,她觉得Lyle很好。的确,好爸爸,跟前妻和平共处光明磊落的。但没过多久,她又开玩笑似的问我:“有没有女人跟他相处得足够久,直到弄清楚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的?”
“就我所知,没有。”我也开玩笑似的回答,发觉她其实也不像看起来那么普通。没有人真的那么普通。
Lyle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陪Caresse玩,他个子高,可以一下把她抱到最高最陡的那个滑梯上去。小姑娘兴奋地尖叫,我却吓得要死,赶紧跑过去接着,等Caresse平平安安回到地上,才又有闲心嘲笑人了,轻声问Lyle:“你是不是迷上绿卡婚姻了?”
他无所谓的回答:“这句话绝对要告诉Cheryl-Ann,她肯定会喜欢这种说法,事实上,这句话听起来,简直就像从她嘴里说出来的一样。”
我撇撇嘴说:“听起来好像是在骂我嘛。”
他笑了一下,一把抱起Caresse,又把她放到最高的那个滑梯上。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不出声地对自己说,这样的事情早晚都会发生,不管是女朋友还是滑梯,我最好还是不要瞎操心了。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Sandra:“你们怎么认识的?”
“哦,”她摸了一下头发,有点不好意思,“真的很偶然,我们是在纽黑文那间医院里遇到的。我去耶鲁见一个作者谈书稿的事情,到了之后才听说他摔了一跤,断了腓骨。说起来真的是很奇怪的事情,如果那个教授没有误了交稿日期,如果他没有摔断腿,我跟Lyle就不可能遇见。”
“医院?你也是去探望病人?”我问Lyle。
他摇头,Sandra替他答了:“他前一天刚做完一个小手术,穿着病号服,在走廊里乱转。我走错了楼层,撞到他一下,他扶着栏杆几乎直不起身子,我以为自己要犯过失杀人罪了,说了无数句对不起,把送他回病房,给他找来护士……”
“……我正好在找那个护士,她没收了我的手机。有监护设备的房间不能打电话,我没守规矩。”Lyle接下去说,好像那是个爱情故事接力。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我看着Lyle,问他。
他也看着我,却没有讲话,回答我的又是Sandra:“九月四号下午,我记得很清楚,到今天为止,我们刚好认识四十天。”
九月四号,那天上午我给他打了个电话,那是我们离婚之前最后一次讲话。如果Sandra惊讶地看着我问:“你不知道他动过手术?!我不能想象自己的反应”
甜点上来之前,Sandra去了化妆间,只有我们三个坐在位子上,我终于开口问他:“你生病了?”
他点头,然后很平静地解释:“切除胆固醇息肉,很小很简单的腹腔镜手术,整个过程不到一小时,两天之后就出院了,完全没有危险,我母亲那方面有家族史,她和Gerard都做过类似的手术。我只是终于下决心尽早去做了而已。”
“为什么没告诉我?”
“原因很多。”
我在心里帮他回答:他不想在那个时候再有什么事情发生,改变原来的计划,他想离婚,我也想,就那么简单,猜也猜得到。于是,我没等他解释,又换了一个问题:“你还有什么会遗传的病没告诉我的?这是你的私事,但是关系到Caresse。”
“没了,你呢?”
“我爷爷奶奶七十岁以后都有高血压,我爸也有这趋势。我右眼有一点点近视,大约五十度。但不戴眼镜也能看得清楚。”
“所以,你也不是那么完美。”
“我有说过我完美吗?”
“那要看你怎么看了。”他说,“你是我遇到过的最会批评人的人,很有效率,喜欢下结论,通常这样的人都觉得自己很完美。”
我想说,想吵架是怎么着?话没出口,Sandra回来了,坐到他身边,在他嘴上亲了一下,看看我们问道:“我错过什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