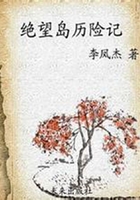大约三天反复的高烧之后,Caresse慢慢好起来了。退了烧,她立刻又精神起来,红疹开始出现在头颈和胸口,迅速蔓延到背、屁股、胳膊以及腿上,像细细的沙粒撒在皮肤上面,似乎并不很痒,只是看起来有些滑稽。又过了两天,疹子就差不多退干净了。回过头来看,短短几天里的事情对我来说好像有一年那么长。原本以为是场灾难,却也不过就是小朋友当中最常见的流行病。许多年之后,可能有一天,我也会不以为然地对Caresse说:不要紧的,不过就是玫瑰疹而已。
住院的那几天,我延长了休假在病房照顾她。她烧退之后,就回到公园大道的那个家里去了,那个礼拜她归Lyle带。不管她在哪里,我还是每天去看她。多数是下班之后,有时还加上午休的一小时。但不管是几点钟,我总会碰到Lyle,可能他也因为Caresse的病修改了自己的日程表吧。他既没说我不该来,也没表示欢迎,表现的就好像理所应当,我们两个就应该在那里,一切只为了那个小朋友高兴。
又一个周末来临,交接小孩的时候,我们又匆匆见了一面。那个时候,我们刚刚开始实行一种新的交接办法。因为Caresse慢慢懂事了,为了让“交接”显得自然一点,每到那个时候,我们总是约在公园、游戏场、餐馆或是售卖玩具的商店里,就好像妈妈带宝宝去玩,玩累了爸爸带宝宝回家,这个样子。有个专家告诉我们,很多有小孩的离婚家庭都是这样做的。虽然在这个离婚家庭,更多的时候,是妈妈和保姆在交接。
那个下午天气不好,我们约在麦迪逊大街的一间玩具店里。出租车只能停在街对面,下车穿过马路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了。贴满动物图案的橱窗玻璃后面,Lyle就站在那里,Caresse两只胳膊抱着他的一条腿,抬头看着他,好像咿咿呀呀地在跟他讲话,脑袋晃啊晃的,口水都蹭在他裤子上了。他笑起来,用手里的一条纱手帕帮她擦掉。
我推门进去,他看到我,低头对Caresse说:“看,妈咪来了。”
Caresse朝我挥手,冲过来要我抱,我抱起她,问Lyle:“她刚才在跟你说什么?学会什么新词了没有?”
“她说,今晚我们跟妈咪一起吃饭好不好?”他回答,在我开口之前又补充,“我们三个。”
Caresse肯定说不出这样一句话,是他编的。我也只当是句玩笑话,随口说:“恐怕不行,我还有事情要做,”不字脱口而出,理由却还没编好,晚上我要带Caresse,不能用加班、剪头发或是看电影做借口,“我是说,我跟别人约了吃晚饭。”
“好的,没事。”他看看我答道。
给Caresse买了一套四只森林小伙伴之后,我们从店里出来,拦下一辆出租车,告别分手。坐上车,Lyle把手里那个装宝宝用品的大包交给我。那是一个黑色的四十五公分宽的大手袋,曾经是我的overnight bag,在我们结婚之前要是去他那里过夜,我总是带着这个香奈儿的羊皮大口袋。那个尺寸,我拿着像个旅行袋,他拿似乎更合适一点……我一路胡思乱想,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那么多以前的事情。也不能确定,哪些事情是他故意要我记起来,哪些是我自己想要去回忆的。
接下去的那个晚上是Caresse病好之后第一次在我那里过夜。人家说,小孩子生一次病就会变得任性一点,绝对是真的。而且,直到那个时候,我才逐渐意识到自己在Caresse生病的那段日子里开了个坏头——既然我可以跑去Lyle那里看小孩,他也开始时不时地不请自来,按响我的门铃。
周二晚上,他穿着礼服出现在门口,跟我说他正好在附近,带了蛋糕给Caresse。那天晚上,他抱着她在客厅里跳舞,在玩具钢琴上弹琴给她听,直到九点钟她上床睡觉了才走。我送他到门口,暗示了一下,他这样突然来了,我觉得不方便。
我说:“我没记错的话,今天是星期二,你来接Caresse要等到星期六。秀父爱也不急在今天。”
他回答的倒很坦然:“我突然想到那天在飞机场,说老实话,由他来做此类爸爸该做的事情,我不是很舒服。”这个“他”指的应该就是Nick。
“你说折纸飞机?”我笑了,“从来没人规定过飞机只能由爸爸来折,我们只是朋友,而且他做的飞机的确飞得比较远。”
“随你怎么说吧。”他说完就走了。
到了星期五,我下班回家,打开家门又听到他说话的声音。进门就看到他坐在厨房的小餐桌边上,Caresse坐在他腿上,他正手把手地教她切一块粉红色的鹅肝。小姑娘看起来极其投入,盯着面前的盘子,脸涨得通红。我那里根本没有餐刀,叉子也只有吃水果用的,全套家什都是他带过来的。
“今天有人告诉我,幼儿园的入学考试要考吃饭的,那人批评我是极其不负责任的父亲。”他向我解释,理由听起来有些荒谬。
“可能是有那样的考试,不过肯定是用勺子的。即使是用刀叉,也不会切鹅肝。”
“要学就学得地道一点,不是吗?而且鹅肝很软,比较好切。”
我不跟他废话了,问他:“你自己进来的?”
“Caresse开的门。”他回答。
那个时候,Caresse刚过十四个月,身高约八十四厘米,开门的按钮距离地板至少一米五。其实不用问,也知道是保姆开的门。
我转过头去看了一眼Claudia,她在客厅叠衣服,一脸无辜。她是保守的华侨圈子里的女人。在她看来,一男一女能心平气和的坐在一起,男的不喝酒不赌博不吸毒不打女人,每月给家用,而且又有个小孩子在那里,还有什么好多说的?
Claudia照例在我到家之后走了,Lyle却没有告辞的意思,反而让我也坐下来吃他带来的晚餐,Caresse从他腿上跳下来,抓着我的手把我拉到平常坐的那个位子上去。我搞不懂这算是什么,他突然冒出来,我们三个坐在一起,在餐桌边上,像一个家庭似的。
不过,他没有让这种胡思乱想持续很久,开口对我说:“有机会我们应该经常在一起聚一聚。”
我点头:“这我没意见。”
“实际上,e,我遇到一个人。”他继续说下去,“我想我们可以来个双重约会,你也带上你的约会对象。”
我愣了一下,回答:“好的,我的确应该看看你约会的女人,毕竟她,或者她们,免不了会接触到Caresse。”
“不要这么刻薄。”
“我是实话实说,从前总是你把我拖上法庭,我想偶尔我也可以这么来一次。如果她不够好,Caresse去你那里的时间要重新排过。”
他笑起来,我也忍不住翘起嘴角,也许曾经的爱人就是这样变成朋友的,有点惆怅却不沉重。